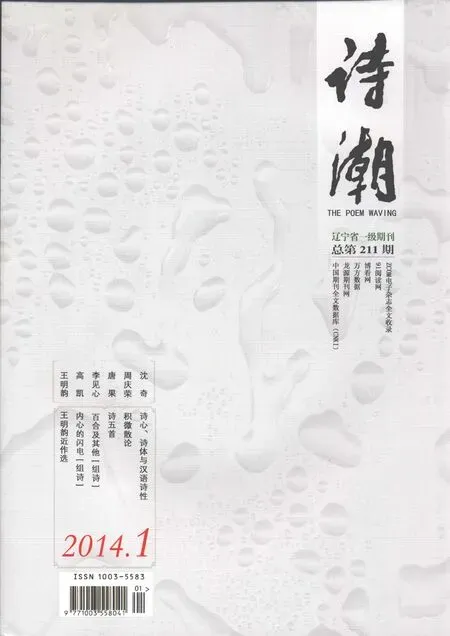詩心、詩體與漢語詩性
——對新詩及當代詩歌的幾點反思
沈奇
詩心、詩體與漢語詩性
——對新詩及當代詩歌的幾點反思
沈奇
進入新世紀后,有關新詩與當代詩歌的問題討論又熱了起來,連同主動與被動,我也說了不少:說“先鋒寫作”與“常態寫作”的問題,說“口語”與“敘事”的問題,說“體制外寫作”與“寫作的有效性”問題,說“動態詩學”與“詩歌標準”的問題,說“自由之輕”與“角色之祟”的問題,說“詩歌生態”與“網絡詩歌”的問題,等等,以至于想要應邀或自在地對之再說些什么,都不知該怎么說了。
尷尬的是,回頭一看,你自以為還算說到點接近問題要害的話,到了還是“說歸說,行歸行”,只顧埋頭趕路以圖“與時俱進”的當代詩歌之旅,很少能真正靜下來瞻前顧后調整“內息”的,這似乎已成為百年新詩的一個“老傳統”,或曰“痼疾”。是以有關詩歌理論與批評的話語,多以兀自空轉,說了也白說。
這實在只是一個積累問題而非解決問題的時代。
談論新詩,無論是反思“五四”白話詩之新,還是慮及當代詩歌進程中各種的什么“新”,總會常常先想到兩句話:一是“身不由己”;二是“枉道以從勢”(孟子語)。
在現代漢語語法中,“新詩”是個偏正詞,主詞是“詩”,為“新”所偏正,以區別于“舊體詩”。以“舊”指代可謂漢語文化傳統之基因“指紋”的“古典詩歌”,是“五四”新文化的一大“發明”。顯然,從命名上便可看出,這一大“發明”的明里暗里,都是社會學層面的理,與真正意義上的“詩”之“道”沒多大關系。其發生學上的要旨在“新”而不在“詩”,所謂“借道而行”。
“身不由己”。在新詩這里,“新”是“大勢所趨”,詩之“道”是一直被“新”所“偏正”而裹挾運行的。包括以20世紀70年代崛起的“朦朧詩”為發端而延伸至今的現代主義新詩潮(第三代詩歌、90年代詩歌、新世紀詩歌等),也都大體以此為軌跡,少有跳脫時代潮流而自在自若者。對此,我曾在20世紀90年代初連續撰文發表,提出警惕“造勢之風”與消解“運動情結”、反顧詩歌本體和詩學本體的問題,到了也只是自己給自己提個醒而已。
如今回頭看,這個“唯新是問”而“與時俱進”的“勢”實在太大了,我們僅僅從新詩百年的不斷重新命名,和所謂代際標出與流派紛爭之繁多與混亂,就可知道“勢”的推力之大和影響之烈,以致每每將“見賢思齊”變成“見先思齊”,導致“詩心”浮躁,難得水深流靜。太多“運動性”的投入,太多“角色化”的出演,缺乏將詩歌寫作作為本真生命的自然呼吸進而成為一種私人宗教的主體人格,也就必然生成太多因“時過”而“境遷”后,便失去其閱讀效應的詩人及其詩歌作品,唯以不斷更新的“量”的繁盛而高調行世。
進入新世紀這十余年間,因意識形態張力的降解和網絡平臺的迅速擴展,當代詩人們發現似乎不再需要以“運動”來助推其“新”,可以稍得自在地返回個我的“創造”與“標出”了,實際“造勢”與“爭鋒”依然不減。這里面有諸如人格缺陷及集體無意識等積習所致,也有新詩與生俱來的基因問題所使然:門檻低,無標準,“挺住意味著一切”。加之身處“數字時代”和“娛樂至死”的文化語境下,大多數詩人愈發成了“時人”與“潮人”,活在當下與形勢的熱熱鬧鬧中,沉溺于“一個‘扁平’的世界里眾聲喧沸”(韓少功語)。所謂“詩之道”到底為何,大概少有思考的。
想到二十年前讀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書之《現代主義》一書,其中有格雷厄姆·霍夫(Craham hoff)題為《現代主義抒情詩》文中的一段話:詩歌最充分的表現不是在宏偉的,而是在優雅的、狹窄的形式之中;不是在公開的言談,而是在內心的交流之中;或許根本就不在交流之中。”①新近讀陳丹青筆錄編纂的《木心講述:文學回憶錄》,特別感慨其中一句話:“詩人不宜多知世事。”②我理解現代中國的“世事”,總不離“時勢”所然,“多知世事”,難免就會為“時勢”所裹挾。復又想起耿耿在心的錢鐘書先生那
句話:“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
這樣的詩人,這樣的素心人,現在哪里去找?
木心還有一句妙語,說“植物是上帝的語言”。③轉喻來說詩之道,可謂“詩是植物的語言”:自然生長,不假外求;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言——居原抱樸,守住愛心,守住純正,以及從容的啟示,而以大自在之詩心,通存在之深呼吸。
何以得“大自在”?先得脫“勢”以從“道”:去機心,棄虛榮,潛行修遠,卓然獨成。
這是說“詩心”之道,還得往下說“詩體”之道。
先說文體的意義。
《文藝爭鳴》2012年第11期,在頭條“視點”欄目刊發當代學者孫郁先生題為《文體家的小說與小說家的文體》大文,開篇劈頭就直言指認:“當代小說家稱得上文體家的不多。小說家們也不屑于談及于此,大約認為是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進而指出:“在文風粗鄙的時代,不談文體的批評界,好像是一種習慣。其實也可以證明,我們的時代的書寫,多是那些不敬畏文字的人完成的。”隨即以木心為例證,引申及結語:“我們今天的作家不敢談文體,實在是沒有這樣的實力。或說沒有這樣的資本。”④讀此文頗感共鳴不久,便讀到《木心講述:文學回憶錄》,其中有一段新解孔子“不學詩,無以言”的話,認為其意思是“不學《詩經》,不會講話。他懂得文采的重要。”其后又說:“我認為,有時候文字語言高于意義。”⑤兩位振聾發聵之言,實在又是反顧常識之思。
我們每個人都活在“故事”中,何以還要有“講故事”的小說?大概要的是小說的那種“說法”;小說之所以成為小說而不僅僅是講故事的特殊文體的“說法”。好的小說,故事、人物、情節、寓意之外,那語言也必是好的。在承載敘事、演繹情節、塑造人物的同時,作為其“介質”的語言本身,也有其獨到的審美品質。亦即“敘事”與“被敘事”一樣,成為其藝術審美的有機組成部分。同理,我們每個人多少都有過“詩意年華”的體驗,何以要有“詩”的存在?大概要的是詩的那種獨特表意的“調調”;詩之所以成為詩這一特殊文體的“調調”。詩的審美本質接近音樂,是對包含在詩性語言形式中的思想、精神、情感、意緒諸“內容”的一種“演奏”;好的詩歌不在于其演奏的“內容”為何,而在其“演奏”的獨特風格與方式讓我們為之傾倒而洗心明道。詩緣情,文以載道,關鍵不在要“緣”的那個情和要“載”的那個道,而是那種詩與文的“緣”法和“載”法。是以我們有了老子、莊子、孔子、孟子等先哲們,還得有屈子、李白、杜甫、蘇東坡等詩人文豪們。這里的邏輯前提是這世界本是說不明白的,說不明白才有意思,才有新的“說”來不斷活泛這個世界的靈魂。“文章千古事”,是“說法”亦即表意方式而不是說的什么,才是生生不息、在在感人的千古不廢之事。
這便是文體的基本意義之所在。
具體到詩歌,“體”的意義就更顯其要了。“抒情詩人之所以運用語言的每一種特性,就是因為他既沒有情節,也沒有虛構的人物,往往也沒有使詩歌得以繼續的理性的論述。致力于字句的準備和完成,不得不取代一切。”⑥以“語言的特性”及“字句”為“體”要,遂成為詩歌發生學層面的關鍵。
這還是西方學者說的話,是身處有語言而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文字“基底”的拼音語系中的學者說的話。而漢語文學自古便離不開文字,離開字詞思維,就沒有了根本意義上的文學思維。按照饒宗頤先生的說法:“中國文學完全建造在文字上面。這一點,是中國在世界上最特別的地方。”⑦也就是說,漢語是包括發聲的“言”和書寫的“文”原道共融、和諧而生的詩性話語,文字是其根本、其靈魂。故漢語詩學向來就有“情生文”與“文生文”兩說。
新詩以胡適“詩體的大解放”為發端,且以“白話”繼而以“現代漢語”為“基底”,以“啟蒙”繼而以“時代精神”之宣傳布道為“激點”,“作詩如作文”,“作詩如說話”,只重“情生文”,無視“文生文”,一路走來,“與時俱進”,直至當代詩歌之“口語”與“敘事”的濫觴、“散文化”及“跨文體”的倡行,除了無限自由的分行,再無其他詩體屬性可言。失去漢語詩性修為與文采美感追求能力的當代詩人們,遂二返西方現代“翻譯詩歌”的借鑒,拿來小說、戲劇、散文及隨筆的情節、人物、戲劇性、理性論述等“他者”元素,來“開疆拓土”以求新的“新”。而問題的邏輯悖論是,如此拿“他者”彩頭充門面的事,是否到了只能是更加“降解”了自身的本質屬性,導致詩體邊界的更加模糊?
現實的狀況是:大體而言,當代漢語詩歌真的就只剩下假以“詩形”而自由“說話”與“作文”的“范”了。
由此可以看出,當代詩歌以無限可能之自由分行為唯一文體屬性,其根由源自失卻漢語字思維、詞思維之詩性基因的傳承與再造,過于信任或單純依賴現代漢語之“通用語言機制”而放任不拘,從而越來越遠離了漢語詩歌的本味。同時,這樣的文體屬性和語言機制,看似自由,其實反而是不自由——寫來寫去,分(行)來分(行)去,只是一點點“同一性差異”;從分行等外在形式層面看去似乎千姿百態、千差萬別,其實內在語感、語態、語序及理路與品質并無多大差異——隨便翻覽當下任何一本詩刊、詩選集以及網絡詩歌,都會發現一個基本現象:無數的詩人所作的無數詩作,都像是同一首詩的復制,或同一
首詩的局部或分延,結果難免“彼此淹沒”。所謂“人各為容,庸音雜體”。而“獨觀謂為警策,眾睹終淪平鈍”。(鐘嶸:《詩品》《詩品序》)
因而我一直認為,若還認同詩歌確有其作為“文體”存在的“元質”前提的話,那么漢語新詩至今為止只能算是一種“弱詩歌”。這個“弱”的根由,在于新詩一直是喝“翻譯詩歌的奶”長大的,且單一憑靠現代漢語的“規矩”所長成,故無論比之西方現代詩還是比之中國古典詩,打根上就難以“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且總難擺脫“洋門出洋腔”的被動與尷尬。
一個民族的文化根性,來自這個民族最初的語言;他們是怎樣“命名”這個世界的,這個世界便怎樣“命名”了他們。而詩的存在,就是不斷重返并再度重鑄這最初的語言、命名性的語言。當代中國人,包括年輕人,之所以還有那么多傾心于古典詩詞者,實在是由衷地傾心于那種留存于漢語文化深處的“味道”,傾心于這個民族共有的情感原點和表意方式。這樣說不是要重新回到古典的之乎者也合轍押韻,而是說要有古典的素養作“底背”,才能“現代漢語”出不失漢語基因與風采的漢語之現代。
故,今天的漢語詩人們,要想真正有所作為,恐怕首先得考慮一下,如何在現代漢語的明晰性、確定性、可量化性之理性運思,與古典漢語的歧義性、隱喻性、不可量化性之詩意運思,亦即“翻譯體”與“漢語味”之間,尋求“同源基因”的存在可能,以此另創一條生存之道,拓展新的格局和生長點。
對此,我給出的答案,依然是這些年我總在那講的四句套話:內化現代,外師古典,融會中西,再造傳統。
回頭還得再說文體的另一重意義——以“雅氣”化“戾氣”的意義。
當代詩人于堅給詩下過一個別有意味的定義,說詩是“為世界文身”。在漢語世界里,“文”同“紋”,“文,畫也”。(《說文解字》)“集眾彩以成錦繡,集眾字以成辭意,如文繡然”。(《釋名》)可見“為世界文身”的功能不在改造世界,而在美化、雅化世界。
雅,在現代漢語中是形容詞,在古代則是名詞,意為“正”,正以“禮”,正以“道”,正以丘壑內營,真宰在胸,脫去塵濁,與物為春。現代之“正”,則正之有教養的公民;正之本真自我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文生于野而正于廟堂,故常常要“禮失求諸野”。至于后來將“雅”與“禮”搞成“雅馴”與“理法”,存天理滅人欲,并不等于今天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完全棄“雅”與“禮”而不顧。連當今的西方也知道,在上帝虛位、哲學終結之后,藝術與美的存在,已成為現代人類最后的“獲救之舌”。
新詩“移洋開新”,本意在思想啟蒙,前期多求時代之“真理”,當代多求日常之“真切”,唯以“情生文”為要,一直疏于對詩體之“文”、詩語之“雅”的“商量培養”。其實要說真,人世間最大的真無過于一個“死”字,人人明白的真,卻依然人人都“偽”美著活下去——可見“真”不如“美”,雖是哄人的東西,卻是實實在在陪著人“偽”活一世的東西。故許多真理都與時俱“退”、與時俱寂滅了,唯詩、唯藝術,萬古不滅。由此轉而想到:一人,一族,一國,一時要發憤圖強,必是于斯時斯地先堵了一口氣,進而再賭了一口氣起而行之的。如此,生志氣,生意氣,生豪氣,也必不可免隨之生出些“戾氣”來。此一“戾氣”,可謂百年中國之時代“暗傷”與國族“隱疾”,發展到今天,無須諱言,從廟堂到民間,教養的問題已上升到第一義的問題——此一要害問題解決不好,必然是誰也過不好,也必然難得長久之好。而“戾氣”何以降解?唯有以“雅氣”化之。而這“雅氣”,從古至今,漢語文化中,總是要詩文來負一點責任的。
眾所周知,古今漢字文化圈,連一片茶葉,也可以由“藥用”而“食用”而“心用”,終而達至“茶道”之境,洗心度人,功莫大焉。反觀烈烈新詩,卻由最初的“藥用”(啟蒙)到后來的“時用”(反映“時代精神”),便一直停留在與“時”俱進的“勢”的層面,難以達至“雅化”之“道”的境界,顯然,其內在語言機制是大有問題可究的。
人是語言的存在物,尤其是現代人。語境可以改變心境,已成不爭之常理。漢語古典詩學將過于貼近現實的詩文及藝術皆歸之于“俗”,其本意或許就在這里。長期以來,我們一直過于看重了新詩的思想與精神作用,疏于其作為一種語言藝術而潤化人心、施予教化的作用,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是個重要的缺失。
注:
①格雷厄姆·霍夫(Craham hoff):《現代主義抒情詩》,轉引自馬爾科姆·布雷特伯里(M·Bradbury)、詹姆斯·麥克法蘭(James Mcfarlame)編《現代主義》,胡家巒等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頁;②木心:《木心講述:文學回憶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頁;③同上,第324頁;④《文藝爭鳴》2012年第11期卷首頁;⑤木心:《木心講述:文學回憶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頁、775頁;⑥蘇珊·朗格(Susanne·K·Langer)《情感與形式》,劉大基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00頁;⑦《文學與神明·饒宗頤訪談錄》,施議對編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