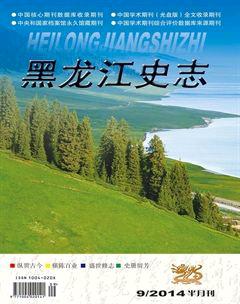張太雷對中共三大的貢獻
楊琳
[摘 要]張太雷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重要創建人,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宣傳家。由于其思想成長歷程與所有的革命實踐活動幾乎都與共產國際有著密切的關系,讓他更容易理解共產國際對中國的策略,能在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代表之間出現矛盾時,起很好的調節和潤滑作用,從而推動中國革命的發展。
[關鍵詞]張太雷;中共三大;馬林;陳獨秀
張太雷(1898-1927),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重要創建人,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宣傳家。張太雷作為中共最早的國際使者,曾在1921年3月遠赴蘇聯參加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工作,籌建了遠東書記處中國科。此外,他還參加了共產國際三大和青年共產國際二大等重要國際會議。回國后,張太雷先后擔任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鮑羅廷的助手和翻譯,為促進中共三大的順利召開和國共兩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作出了突出貢獻。
綜觀張太雷的經歷,不難發現他的思想成長歷程與所有的革命實踐活動幾乎都與共產國際有著密切的關系。他赴蘇工作的獨特經歷,使他具備了不輸于母語的外語水平和對蘇聯風土人情透徹的理解力,讓他更容易理解共產國際對中國的策略,能在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代表之間出現矛盾時,起很好的調節和潤滑作用。同時,他作為中共中央領導人兼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的雙重身份,他的想法和活動都深受影響。因此,本文的研究是放在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背景下,張太雷對中共三大作出的巨大貢獻,旨在突出張太雷面臨東西方各種矛盾和黨內意見分歧沖突時,如何解決矛盾及推動中國革命的發展。
(一)協調馬、陳二人的關系
辛亥革命失敗后,孫中山清醒地認識到他領導的國民黨,既沒有忠實可靠的武裝支持,又缺乏明確的綱領,黨內許多成員腐化墮落、斗志消沉。對此,孫中山憂心如焚,一籌莫展。為了改變這種困局,他將目光開始轉向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1920年秋天,共產國際派魏金斯基來到上海會見了孫中山,這是共產國際與孫中山的第一次接觸。1921年10月,共產國際鑒于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繼魏金斯基后,又派馬林來到中國,從事國共兩黨建立聯合戰線的活動。剛回國的張太雷即被任命為馬林的助手和翻譯。張太雷上任后的首要任務,便是協調馬陳二人間的關系。
馬林和陳獨秀的關系從第一見面就很不和諧。1921年9月中旬,陳獨秀辭去廣東教育委員的職務,回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局書記。他抵滬后不久,就從李達、張國燾處了解到,馬林要求中央每周匯報工作一次,并安排時任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的張國燾擬定該部門的工作計劃和預算,明確表態由共產國際來負擔中共的工作經費和工作人員的薪水,而中共中央的義務是定期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和經費支出情況。這種做法使陳獨秀立即產生反感。此后的接觸會談,讓馬、陳兩人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尤其是在中共與第三國際的關系問題上,發生了很大的爭執,會談停頓了,關系僵持了”[1]。馬林按照第三國際的體制,認為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共的方針、計劃都應在第三國際的統一領導下進行。而陳獨秀則表示中國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特別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國際的經濟支援,暫時保持中蘇兩黨的兄弟關系。[2]
張太雷成為當時調節兩人關系的關鍵。只因在馬、陳日益激烈的矛盾面前,連“張國燾當時被認為是接近馬林的人,但是他也沒有主意,不敢作聲,因此,奔走于陳獨秀與馬林之間和傳遞信件的只有張太雷同志一人。”[3]在中共與第三國際關系的問題上,張太雷是站在馬林這邊的。他早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建中國科時,就堅決執行“每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并成為它的支部”[4]的規定,為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取得合法地位架起了橋梁。對此,張太雷對陳獨秀做了大量的工作。據包慧僧回憶:“有一天……我到中央書記辦公的地方談工作,進去時,正遇見張太雷同志同陳獨秀談中共與第三國際的關系問題。張太雷同志勸陳獨秀說:共產主義運動,全世界是一個整體,都應該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活動,中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話還沒有完,陳獨秀發起火來,說:中國的革命要根據中國的歷史條件和經歷條件來推動。我們一無所有,犯不著戴人家的現成帽子,你的話同馬林的話是一樣的,我聽不進去,……陳獨秀站起來拿著帽子要走,張太雷同志請他坐下來繼續談下去,但是,陳獨秀還是很不高興地走了。”[5]在陳獨秀那碰壁之后,張太雷對他身邊的同事進行勸說,試圖用朋友圈的影響力,讓陳獨秀改變態度。
張太雷與馬林全力營救被捕的陳獨秀,成為改變馬、陳二人關系的轉折點。1921年10月初,張太雷出使日本歸來時,正值陳獨秀、包惠僧、楊明齋等遭法租界巡捕房拘捕,被指控編輯《新青年》等過激書刊有害租界安全。張太雷立即與馬林等密切配合,四方奔走,全力營救。馬林請當時上海著名的法國律師巴和出庭為陳獨秀辯護,還動用共產國際的活動經費打通會審公堂各個關節。同時,張太雷、李達等聯絡社會力量積極營救。由于營救得力,陳獨秀被罰100元了案。幾天后,在張太雷的陪同下,馬、陳再次進行了會晤。這次會談,氣氛相當和諧,彼此能推心置腹。他們“從此經常見面,毫無隔閡的商討各項問題。……并且具體規定了接受國際補助經費的辦法;此后中國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變成了經常性質了”[3]。包慧僧曾贊嘆:“這一次糾紛的解決,張太雷同志起了很好的作用。”[6]
(二)與國民黨上層積極接觸掃除國共合作障礙
自1921年起,張太雷陪同馬林到桂林與孫中山進行會談,以后又在上海、廣州、莫斯科、武漢等地工作,工作的重點都是國共合作的政策。但兩黨合作存在著眾多阻礙。
首先,孫中山本人對國共合作并無確定的信念,同時國民黨內部意見都存在很大分歧,其中國民黨右派對兩黨合作則存在更多猜忌。
其次,當時的國民黨是中國的第一大黨,它的歷史和影響在國內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孫中山為首的黨內人士均以革命正統自居,對于其他政黨,總以高人一等的態度看待。
針對以上情況,張太雷利用與國民黨上層人士接觸的機會,向孫中山及左派人士做了不少解釋的工作,“當時國際代表站在客卿地位,有時不便直言無隱,太雷便從旁加以協助,盡力宣傳十月革命后蘇聯國力日臻強盛,實為世界革命陣營唯一可靠的盟邦。同時也說明中國共產黨革命政策的實質與工農新興力量抬頭,也是史無前例極堪信賴的新因素。這些因勢利導的進言,具有一定的說服力。”(1)
(三)消除共產黨內關于國共合作的分歧
經過多方考察和與國民黨領導人的多次會談,馬林為中國革命制定了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方案。但是,以黨內合作的形勢的方案一經提出就遭到了中共黨內大多數人的反對。
首先發難的是陳獨秀。他于1922年4月6口致信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魏金斯基,明確反對馬林關于全體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的提議,并陳述了包括兩黨宗旨不同;孫逸仙派向來對于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等(2)六條反對理由。陳公博甚至公開直接反對國共合作,他認為“國民黨的主義和共產黨的主義究竟不同,今日縱合,終久必分,與其將來分裂,倒不如各行其是”,他還認為國共合作“只是一種旁門左道,而非正當革命的辦法”(3)。對于這些反對聲音,張太雷做了大量工作。他通過寫文章、做演講、授課、談話等多種形式大力宣傳國共合作的必要性,反復強調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這兩個強大的兇惡敵人,就必須建立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反對共同的敵人。針對黨內同志“對國民黨的印象不好,認為他們多是一些官僚政客,特別是不愿意當‘跨黨的黨員”(4)這些心里包袱,張太雷指出,兩黨合作中“我們要加入國民黨,一定要保持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一定要保持無產階級的黨性”(5)。陽翰笙回憶道:“太雷同志這些真知灼見的主張,給我們以深刻的教育。”(6)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杭州西湖會議召開。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熹、高君宇、張太雷和馬林出席此次會議,討論共產國際關于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問題。馬林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并堅決主張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國共統一戰線。李大釗同意馬林的意見。張國熹堅決反對。陳獨秀開始不同意,后表示服從共產國際決議,但要以取消加入國民黨時打手模和宣誓服從孫中山的做法,以及根據民主原則改組國民黨為條件。最終,經過馬林的說服,李大釗、張太雷的疏通,會議原則上接受了加入國民黨的主張。會后不久,張太雷和李大釗等少數共產黨員,在孫中山的親自主持下,率先以個人名義正式加入國民黨,成為參加國民黨的第一批中共黨員,做了很好的表率。
在此基礎上,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了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此次大會是旨在正式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張太雷出席大會,并參與大會的籌備工作,參加黨章的起草工作。與會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近40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出席了會議。會上,討論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問題成為中心議題。張太雷“在會上發言很激烈,主張國共合作”(7)。他仔細分析了孫中山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民主主義立場,以及把國民黨改造成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可能性,積極主張采取幫助國民黨進行改組,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針。他還在代表中展開活動,進一步宣傳和解釋國共合作及其偉大意義,以加深代表們對這一方針的理解。在張太雷和其他持正確意見同志的努力下,最終,中共三大正式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孫中山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的策略方針,從而為實現國共兩黨的首次合作奠定了基礎,開創了國民革命的新局面。
參考文獻:
[1]包慧僧:《回憶張太雷》,《回憶張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頁。
[2]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集1917-1925》第2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北京圖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430頁。
[3]包慧僧:《回憶張太雷》,《回憶張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頁。
[4]轉引自葉孟魁、趙曉春:《中共創建時期的張太雷與陳獨秀》,《江蘇工業學院學報》,2007年6月第8卷第2期。
[5]包慧僧:《回憶張太雷》,《回憶張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頁。
注釋:
(1)羅章龍:《憶太雷同志》,《回憶張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頁。
(2)參見《“二大”和“三大”》,中國共產黨第二、三次代表大會資料選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頁。
(3)陳公博:《我與共產黨》,《“二大”和“三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571頁。
(4)陽翰笙:《憶我的良師益友張太雷同志》,《回憶張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頁。
(5)陽翰笙:《憶我的良師益友張太雷同志》,《回憶張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頁。
(6)陽翰笙:《憶我的良師益友張太雷同志》,《回憶張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頁。
(7)徐梅坤:《回憶中共三大》,《“二大”和“三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