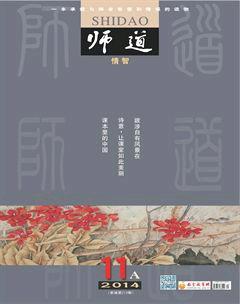“弟子中國”之隱憂
呂偉超
生活,有時,不過是聲音的匯集。每天,我們進入,或是逃離。
單位身處鬧市,車水馬龍,頗為嘈雜。邊上是一個公園,清晨,我去公園散步,須先快速跑過公園的廣場——廣場舞的歌聲和鼓點,和制造它們的大媽們,如色塊斑斕的沖擊波,已經(jīng)把周邊的房價,打壓得抬不起頭來了——因此,跑的時候,我必須盡可能地,低著頭。有時我跑到公園東首的寺廟邊,聽梵音繚繞,有時跑到公園西面的小學(xué)旁,聽書聲瑯瑯。某天,見小學(xué)生齊集操場,雙手別在背后,高昂著頭,用力背書:“弟子規(guī),圣人訓(xùn)。首孝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余力,則學(xué)文……”聲音一如他們的隊伍,整齊劃一,鏗鏘有力。“步從容,立端正;揖深圓,拜恭敬。勿踐閾,勿跛倚;勿箕踞,勿搖髀……” 小學(xué)生齊聲誦讀《弟子規(guī)》,童音清越,足以消弭廣場舞歌聲之凌亂。可是,小學(xué)生那恭敬的身姿,沉穩(wěn)的腔調(diào),與大媽們夸張的動作、放肆的音調(diào),恰成鮮明對比。少年老成,老來天真,公園的空氣里,不時激蕩起兩種時代的“最強音”。
曾幾何時起,在一些中小學(xué)校,誦讀《弟子規(guī)》成為時髦。晨間頌,午后讀,日暮省;老師念,學(xué)生背,家長跟著讀。嚴肅的,正襟危坐;夸張的,搖頭晃腦;還有穿漢服,系紅領(lǐng)巾,儼然如行為藝術(shù)。《弟子規(guī)》原名《訓(xùn)蒙文》,是清康熙年間一位名叫李毓秀的秀才所著。傳統(tǒng)蒙學(xué)讀物,以“三百千”為代表,《千字文》文辭優(yōu)美,《百家姓》尋根問祖,《三字經(jīng)》包羅萬象,可謂是各有千秋。可為什么到了大清的康乾盛世,又弄出一部《弟子規(guī)》來呢?《弟子規(guī)》的作者李夫子這個人,我們只知道他是一個秀才,以教書為業(yè)。不過沒關(guān)系,巴爾扎克說過,“時代比人更有趣”。康熙乾隆年間,是我國封建專制登峰造極的時期,是一個“華麗”的盛世,也是一個要靠最嚴厲的“規(guī)訓(xùn)”來維持的末世。因此,“弟子規(guī),圣人訓(xùn)”這樣的《訓(xùn)蒙文》,直接以“規(guī)訓(xùn)”的面目出現(xiàn),是大有時代意味的。
《弟子規(guī)》在語言上,繼承和發(fā)展了《三字經(jīng)》的形式,三字一句,兩句一韻。今天一些主張讀《弟子規(guī)》者說,《弟子規(guī)》語言不錯,通俗易懂,稱得上是“詩教”。可是,你又見過有哪一首好詩,字里行間,是充斥著陳詞濫調(diào)的說教的呢?古希臘戲劇家埃斯庫羅斯認為,大人教小孩,詩人教大人。大人要有“詩意”,才能去教小孩。《弟子規(guī)》問世后,作為蒙學(xué)讀物,可謂是籍籍無名,直到最近幾年才忽然流行開來。
既是“規(guī)訓(xùn)”,就要尋求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合法性,《弟子規(guī)》的作者,顯然深諳其中之道。李夫子以儒家學(xué)說為其合法性淵源,《弟子規(guī)》三百六十句,一千零八十字,借用《論語·學(xué)而》中“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有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xué)文”一句話,鋪衍而成。《弟子規(guī)》以“孝、悌、仁、愛”為核心價值,為“規(guī)訓(xùn)”蒙上一層合法神圣的光環(huán)。也許有人會說,《弟子規(guī)》講“父慈子孝”,講“兄友弟恭”,講“謹而有信”,講“親仁愛人”,講得很好啊,它所宣揚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不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嗎?誠然,《弟子規(guī)》所講,你若一句一句拆開來看,似乎都有道理,比如講孝順父母,總不會有錯吧。但是如果我們對《弟子規(guī)》不僅僅拘泥于“文義”,而對其進行“立法解釋”的話,我們就容易發(fā)現(xiàn)其內(nèi)在的邏輯和真實的意圖了。《弟子規(guī)》,顧名思義,就是對“弟子”的規(guī)訓(xùn),那么誰是“弟子”呢?弟子,最基本的含義,是指一個家庭中年幼的孩子,在中國古代的大家族中,年輕者對于長輩,皆可稱“弟子”,或是“子弟”。大觀園中的賈寶玉是“弟子”,巴金《家》里面的覺新是“弟子”。“弟子”是一個以血緣和宗法為身份連結(jié)紐帶的特定形象,擬制開來,楊林的十三太保是“弟子”,袁世凱小站的新兵是“子弟”。《弟子規(guī)》通過對孝道的反復(fù)渲染,來強化這種私的身份關(guān)系,從而強調(diào)對以身份等級和人身依附為基礎(chǔ)的父權(quán)宗法制的絕對權(quán)威,以及對這種權(quán)威的無條件服從。“父母呼,應(yīng)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zé),須順承”,試想,如果今天的孩子受了這些教條的影響,那么“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何以發(fā)生?且不論這些教條與現(xiàn)代公民社會的價值觀格格不入,就是離真正的儒家思想,也相去甚遠。儒家強調(diào)“孝道”,但孝不等于對父母的無條件服從,“父為子綱,父不慈,子奔他鄉(xiāng)”,相反,儒家認為,如果作孩子的一味順從父母,陷父母于不義,那才是真正的不孝,“于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如此看來,真正的儒家,是有不服從的傳統(tǒng)的,這與梭羅的“公民的不服從”有異曲同工之處。《弟子規(guī)》故意斷章取義地曲解了儒家思想的真義,是“小人儒”。“弟子”的另一個含義是指學(xué)生,在古代社會,老師與學(xué)生,師傅與徒弟之間,本屬契約關(guān)系,但也被刻意轉(zhuǎn)化為“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身份關(guān)系。盡可能地把各種社會關(guān)系,納入到宗法身份中去,是古代中國社會的一大特征,如此,一切“服從”與“規(guī)訓(xùn)”,就都名正言順,師出有名了。在傳統(tǒng)中國“家國同構(gòu)”的社會體制下,在家為弟子,在國為臣民,當(dāng)官者為父母,作百姓的是順民。即便是今天,在官場還流行著稱領(lǐng)導(dǎo)為“老大”的現(xiàn)象,如果你不能和老大“稱兄道弟”,那領(lǐng)導(dǎo)就要考慮“還能不能和你一起愉快地玩耍了”。《弟子規(guī)》以孝道開篇的真正用義,就是要從小培養(yǎng)服從身份等級、隱忍順從的“愚民”,“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難怪某地拆遷辦領(lǐng)導(dǎo)呼吁要“踐行”《弟子規(guī)》,這樣,“沒有拆遷就沒有新中國”的規(guī)訓(xùn),也就能很順利地被“踐行”了。
有人說《弟子規(guī)》是滿清政府為在漢人中推行奴化教育而刻意編寫的,我覺得這顯然是上綱上線了。《弟子規(guī)》的作者李毓秀,一個清朝的落第秀才,自然是申請不了國家課題,也沒享受過什么基金的資助,《弟子規(guī)》完全是利用業(yè)余時間,自發(fā)編寫而成的。李秀才科舉失敗,是專制體制的受害者,可他卻嘔心瀝血,寫了一部為維護專制統(tǒng)治服務(wù)的《訓(xùn)蒙文》,那是那個時代的故事。而我們今天更要反思的,是在走出專制,走向共和已經(jīng)一百多年的今天,在從臣民社會向公民社會邁進的今天,在從身份社會走向契約社會的今天,在平等,自由,民主,人權(quán)已成為“共同的善”的今天,究竟是什么心態(tài),使相當(dāng)一部分教師和社會公眾,對《弟子規(guī)》所倡導(dǎo)的順民教育,依然津津樂道?是民眾啟蒙未完成的無知?還是師者庸俗智巧的偷懶?endprint
也許有人會說:“我們沒有把《弟子規(guī)》想得那么復(fù)雜,《弟子規(guī)》講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小孩子就算是隨便讀讀,也是有好處的,現(xiàn)在的孩子太調(diào)皮,讓他多懂一點規(guī)矩沒什么不好。現(xiàn)代社會多如牛毛的法律,不就是各種各樣的規(guī)矩嗎?比起《弟子規(guī)》來,不知要多出多少倍呢?”其實,此規(guī)矩非彼規(guī)矩,現(xiàn)代社會的法律是以“權(quán)利”為中心的,規(guī)范的作用,為的是保護“人權(quán)”,使人成為“人”。而《弟子規(guī)》里的規(guī)訓(xùn),全是“義務(wù)”,對小孩子的起居、穿衣、走路等行為舉止,待人接物的各個方面,做出最嚴格的規(guī)定,堪稱史上最嚴厲的“小學(xué)生守則”。在短短一千來個字里,就出現(xiàn)過43次“勿”字,如果真按它的規(guī)定去做,人就成為“非人”了。我很懷疑,網(wǎng)上流傳的某些學(xué)校的變態(tài)校規(guī),如“男女生交往須五人同時在場” 、“男女生交往距離不得少于50公分”等,就是模仿《弟子規(guī)》而來的。
錢文忠先生在“百家講壇”講《弟子規(guī)》,一開始舉了這么一個例子,說北京有一位派出所的所長,到轄區(qū)學(xué)校作法治報告,用《弟子規(guī)》作教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相信這個事件是有的,但至于“效果”,我表示很懷疑。在我讀中學(xué)的時候,也經(jīng)常聽這類法治報告,主講的不是派出所長,就是看守所長。所長們把大蓋帽往主席臺一放,就開始講青少年犯罪和監(jiān)獄里的“故事”,中學(xué)期間,我聽過不少“監(jiān)獄故事”,卻從未聽過真正的“法治”。
今天,《弟子規(guī)》在學(xué)校的流傳,可謂是花樣百出,你搞誦讀,我就來個吟唱。可以想象,李秀才之后,《弟子規(guī)》是被反復(fù)吟唱過的,童聲純真,一如雨滴清亮,音律一定是極美的。可淋落這雨滴的烏云,恰是阻擋啟蒙之光的蔽日陰翳,這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第一次隱憂。一直到李秀才之后一百年,才有一個叫龔自珍的詩人,面對奴性十足的中國社會,忍無可忍,發(fā)出直抒胸意的怒吼:“九州生氣恃風(fēng)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詩人的怒吼,自然喚不醒久病的梅樹和亦步亦趨的“弟子”,而此刻,天邊傳來了鴉片戰(zhàn)爭隆隆的炮聲。硝煙彌漫里,德先生和賽先生已然在火光中隱約閃現(xiàn),但是,“一個幽靈”,套用馬克思的話來講,“專制主義的幽靈,依然在中華大地飄蕩”,這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第二次隱憂。
在今天這樣一個“現(xiàn)代”社會,無論是老師讓學(xué)生背《弟子規(guī)》,還是老板讓員工讀《弟子規(guī)》,都有一種虛無感。“一種虛構(gòu)的關(guān)系自動地產(chǎn)生出一種真實的征服”,這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第三次隱憂——“少年中國”虛化后,“弟子中國”之隱憂。
(作者單位:溫州城市大學(xué))
責(zé)任編輯 李 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