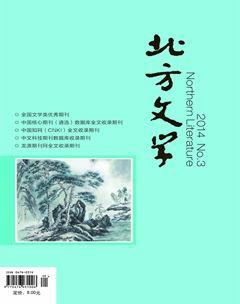莎士比亞悲劇中女性悲劇命運的成因
諸葛巧媛
摘 要:莎士比亞悲劇中女性可分為兩類:誠實善良和陰險毒辣。不管哪一類,她們的命運都是悲慘的。本文將通過對她們形象的分析以及從文藝復興時期的男權思想來探討她們的悲劇成因。
關鍵詞:女性悲劇;男權;悲劇成因
談到莎士比亞,人們馬上會聯想到他劇作中某些人物的形象。其劇中的人物因其生動、深刻、典型而成為研究者們感興趣的話題。莎士比亞筆下的女性更是他創造的人物中突出的一群。四大悲劇中女性的悲劇命運更是讓人對她們的形象記憶深刻。
一、兩種女性
1、 誠實善良、美麗純潔,但又軟弱可欺的女性形象
在《奧瑟羅》中苔絲蒙德娜違背父親的意愿,偷偷出走和摩爾人奧賽羅秘密結婚,但婚后就把自己的一切都委之于丈夫,成了丈夫的奴隸。不管丈夫對她進行怎樣的侮辱,她都逆來順受、委曲求全。在《奧瑟羅》第二幕第二場中奧瑟羅對苔絲狄蒙娜的贊美:我的妻子貌美多姿,愛好交際,口才敏慧,能歌善舞,彈一手好琴決不會使我嫉妒,這是賢淑女子錦上添花的美妙外飾。(Shakespeare, 2001:82)
然而,由于伊阿古的挑唆引起了奧賽羅的嫉妒,最終死在自己丈夫的手下。即使在臨死前,善良軟弱的苔絲狄蒙娜還是在維護著自己的丈夫奧瑟羅。她到死都忠于自己的丈夫,到死都愛他,而且寧肯自己含冤負屈,飲恨而亡,也不忍說一句不利于自己丈夫的話。
2、陰險毒辣、殘忍無比的惡女人形象
在《麥克白》中麥克白夫人是一個比丈夫還要冷酷而貪婪的女人。她的意志膽量超過了丈夫,冷靜、殘忍的性格也為麥克白所不及。她不像她丈夫那樣瞻前顧后、考慮很多,而是心胸險惡、兇狠毒辣,行動時堅決果斷,從不動搖,麥克白夫人本來就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女人,她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幫助丈夫成為國王,可見到丈夫殺人之心動搖時,立即責備他縮頭縮腦,不像個男子漢。她為了鼓勵麥克白殺死國王鄧肯,便說:“我哺育過嬰孩,知道一個母親是怎樣憐愛那吸吮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會在它看著我的臉微笑的時候,從它的柔軟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頭,把它的腦袋砸碎。”(莎士比亞,2007:28)麥克白在他夫人的鼓動下,殺害了明君鄧肯,自己做了國王,而麥克白夫人由于殺人后卻支持不住過多的血債的重壓,受到良心的譴責,以致癲狂發瘋,終于在嘆息、焦慮、夢游、精神失常、無限痛苦中死去。表明麥克白夫人是一個既冷酷無情,又人性未泯的惡婦形象。
二、悲劇的成因
西方傳統中歷來也有男尊女卑的觀念,女性的存在只因為是有待于男性征服的對立面。古希臘時期,女人是男人的戰利品,男女之間是人與物的關系;中世紀,女人是男人的奴隸,男女之間是神與人的關系。的確,從文藝復興開始,文化的覺醒首先表現在重新返回古代,對古希臘、羅馬價值觀進行深入研究,重新肯定人的價值,出現了前所未有對人的注意描寫人、歌頌人,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由此,可能有人認為此時西方女性觀已改變,女性地位已提高。不可否認,這是對人的一次肯定,但這“人”更多指男人。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思想,更多傾向男性,而傳統中根深蒂固的男女地位懸殊的現實,不可能徹底扭轉。
苔絲狄蒙娜,考狄利亞,麥克白夫人,高納里爾和里根最終走向死亡,究其原因,或因“貞操”,或因男權,如同某些祭祀儀式中被選中獻給神的“人犧”,一步步被推向人生的祭壇,做了丈夫或父親的“犧牲”,成了男權意識下的“陪葬”,失去了自身應有的自主和獨立。奧賽羅僅憑一塊手帕及伊阿古一面之詞,便將自己美麗、善良的妻子扼死,有人稱這是愛之真、恨之切的表現。倒不如說當時女性觀,或貞操觀,如無形的手抓住了奧賽羅,使他為了自己的名譽、私心,不分青紅皂白殺妻。
麥克白夫人是個舉世公認的狠毒的“惡女人”。但細讀全劇,我們會發現,她所作所為的原因雖有自己的權力欲,但又何嘗不是出于對丈夫的愛與忠貞呢?真正登上王位的是麥克白。奪得王位后,麥克白夫人常陷入弒君后的負罪感中,并患了夜游癥……可見,其不全為一己之私,同樣是緣于對丈夫的忠貞。最終,她因良心譴責抑郁而死,以死保持了對丈夫的“貞操”,無形中又暗合了當時對女性的種種規范,表面看是惡有惡報,而更深層意識上,無疑是夫權的殉葬品。
三、結束語
從對以上這幾部悲劇的分析,我們看到莎士比亞在劇中塑造的女性基本上是兩類。一類正像他自己在《哈姆雷特》中對女性的譴責所發的震撼人心的感慨那樣:“軟弱!你的名字是女人!”另一類就是那些像蛇蝎一樣的壞女人,她們不是水性楊花,有悖女德,就是一些野心勃勃毫無人性與仁愛,充滿了強烈的權力欲,并且為了權力不惜大開殺戒的女人。而不管是哪一類她們最終的命運都是令人唏噓的。莎士比亞在他的這幾部作品中,宣揚的是父權文化下對女性早已固定的道德規范,由此看來,“家庭天使”、“賢妻良母”仍是莎士比亞心目中抹不掉、揮不去的理想女性。這與他早期描寫的擺脫傳統觀念,掙脫精神枷鎖,追求自我發展的新女性形象是相矛盾的。究其原因,是因為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思想,更多傾向男性,但男尊女卑的傳統并沒改變。“貞操” 、“忠貞” 、“男權”仍禁錮了女性。然而,無論就時代還是個人,都不可能有徹底的男女平等思想,因此,這幾大悲劇中女性的命運是必然的,不能求全責備。
參考文獻:
[1] 劉娜,《莎士比亞戲劇的女性主義解讀》[J],重慶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9):130-132頁。
[2] 莎士比亞,《李爾王》[M],梁實秋(譯)。北京:中國電視出版社,2001。
[3] -----,《麥克白斯悲劇》[M],卞之琳 (譯)。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