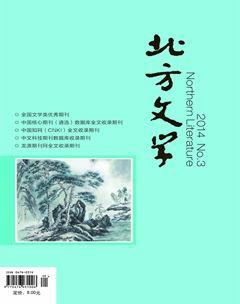論五代西蜀詩人吟詠情性詩學理念的回歸
高銘銘
由唐末到五代十國延續的亂世現狀,極大的困擾著文人們脆弱的心靈,在那個武夫跋扈,皇權衰敗,強權林立,朝不保夕的時代中,文人在政權中的地位極其卑微;即使位居高位,也不得不仰人鼻息以明哲保身。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沖擊震蕩,出仕于亂世的作家逐漸形成了穩定的群體人格——明哲保身、隨波逐流成為主要的人格構成。同時,西蜀文人則在明哲保身之外又把自己放逐到豪奢的宴樂生活之中或逃避到冷寂的紅塵之外,逃避退守的文學品格與吟詠情性的文學理念已經占據了他們生活和創作的重要位置,成為一時風尚。
亂世談道的空泛性與蒼白性,使得五代時期順乎時勢,聽天由命的無奈情緒成為普遍的心聲,也是文人們在亂世中必然的時代心理。馮道《天道》一詩云:
窮達皆由命,何須發嘆聲。但知行事好,莫要問前程。
冬去冰須半,春來草還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1]
正是抱著這樣的態度,道事四朝十一君,很少諫諍,安于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自稱“長樂老”。即便如此,‘“當時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顯而易見,五代人并不以之為非。其實,聽天順命,明哲保身,退居逃避的論調和行為在當時比比皆是。那些在亂離中苦苦掙扎,以及后來出仕于各個割據政權的詩人,似乎忘卻了“功名”這個詞,而代之以“名利”二字。
隨著儒道人格的淡化和士人功名思想的消失,為躲避戰亂和人世間的種種不平而徹底遁世的人數不斷增加,真正的隱逸人格與退居退守的時代心理逐漸步入獨立發展的軌道,那些寄身于諸統政權下,窮達由命,進退維谷的仕宦文人,在追名逐利中,也常常對超然世外的隱逸生活深懷向往和傾慕之情。
唐末五代是隱風極盛的時期,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就出現了司空圖、沈彬、唐求、左偃、史遒白、瘳凝、陶陶(南唐)、劉洞、陳 、閻芷、廖融、 皎、鄭遨、杜光庭、及僧人貫休,齊已、虛中、處默、可朋、曇域、等高人,這還不包括了鄭谷等棄官回家,隱逸而終者。基于時代氛圍、文化心理的迥異,五代隱逸之士和唐代的處士有著根本上的區別。他的再不坐歡垂釣,臨淵羨魚;也不借“終南捷徑”以沽名釣譽;更不隱仕兼顧,半官半隱,他們一旦歸隱,便大多義無反顧,不再回到世俗的名利場中。司空圖退歸之后屢征不起,老死家中;沈彬“禪代之后,絕不求進”;史虛白“南游至九州落星灣,因家嚴常乘雙犢轅,掛酒壺車上,山意總角負一琴一酒瓢從之,往來廬山,絕意世事。”[2]
五代十國,雖干戈擾攘,瓜分豆剖,但各割據王朝尤其是江南西蜀南唐諸國宮廷游樂歌舞活動卻仍然極其興盛,象后唐莊宗李存勖、前蜀后主王衍、后蜀主孟昶、南唐中主李 李煜等,不僅耽溺于歌舞游樂的荒淫縱逸生活,而且皆具有較精深的音樂與文學修養,能制曲、作詞與歌舞。“舞頭皆著畫羅衣,唱得新翻御制詞。每日內庭聞教隊,樂聲飛到龍墀。”(花蕊夫人《宮詞》)“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魚貫列。笙簫吹斷水云間,重按霓歌遍徹。”(李煜《玉樓春》)這些詞句便是對他們歌舞娛樂享受生活的生動描寫。因此,和退居避世的隱逸人格不同的又一遁世之道,便是沉湎于感宮的享樂之中。把自己放逐于尊前花間,酒席酌飲之中,尋求精神的又一出路。無論隱逸田園,還是醉入花間,在文學上,便是對心情、感情的自我心情的描繪,遠遠大過對“功名”和世道人心的描述規劃,對日常生活的關注刻畫便又成了五代詩人的又一追求。
李澤厚認為“在詞里面,中晚唐以來的這種時代心理終于找到了他最合適的歸宿。內容決定形式”。 并舉例加以說明:“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夜夜夢魂休漫語,已知前夢無尋處”;“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這種與“詩境”截然不同的“詞境”的創造,正是這一時期典型的審美音調。“所謂詞境,就是通過長短不齊的句型,更為具體、更為細致、更為集中的刻畫抒寫出某種心情意緒”;“詞則常一首(或一闋)才一意或一境,形象細膩、含意微妙,它經常是通過對一般的、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的白描來表現,從而也就使所描繪的對象、事物、情節更為具體、細致、新巧,并涂上了更加濃厚細膩的主觀感情色彩,不同于較為籠統、渾厚、寬大的詩境”。[3]
歐陽炯的《花間集序》則是這種時代傾向的真實注腳,也說明“吟詠情性”已自覺不自覺的成為當時詩歌創作的理論闡釋。他說:
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迥巧;栽花剪葉,奪春艷以爭鮮。是以唱云謠則金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碎。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歌;響遏行云,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競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娼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
有唐以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守越艷;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代溫飛卿復有《金荃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
今衛卿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廣會眾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為十卷。以炯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為敘引。昔呈人有歌陽春者,號為絕唱,乃命之為《花間集》。庶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4]
這篇序言涉及到好多方面的問題。但從文學觀念和文學理論的角度出發來剖析和梳理其內容,便可發現其中最醒目的一點即是:它公然宣稱,詞是一種用以娛樂和佐歡的文學。這就沖破了“政教文化”的桎梏,并以此作為突破口,導出對于詞文學之言情、尚艷、求美特性的肯定之論。
這樣,吟詠情性這一文學主題便日漸占據了主導地位,成為時代的共同風尚和詩人們追求的共同風格。詩人目光已經逐漸從大漠塞外的苦寒雄渾風光轉移到日常生活的瑣屑與尖新意境中來;士人對人世的追求以及建功立業的雄心也漸漸消磨,更加注重個人身心的逃遁與放逐;士人的詩歌創作也不可避免的轉向吟詠情性之作。這樣,纖細烷媚的花間體、通俗淺切的白體,以及空靈枯寂的姚賈余波成為西蜀詩壇主要的詩風流派。與文學追求相對應的是兩屬文人和儒家思想傳統的疏離,解釋道思想逐漸占據文人頭腦。再加上五代戰亂頻仍,文人們與傳統儒道的疏離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或醉入花間或隱逸田園,有的甚至直接皈依佛道,借以躲避人世間的紛擾和內心壓抑的感傷。
由此可見,五代西蜀文人的社會生活和人生追求正日益由社會政治和功名事業的外部世界轉向自我內心世界,轉向游宴享樂的世俗生活的小圈子。文人參加游樂歌舞的生活更加普遍了,接觸歌妓舞女的機會也更加頻繁,他們的音樂素養自然更為熟悉和通曉,這為他們的詩歌創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活經歷和先決條件;另外,尋求心理慰藉和感官享受的內在需求,使他們產生創作的內在欲望與強烈沖動,并最終較普遍地付諸于創作實踐,他們的詩歌自然就充滿了艷情與瑣事。
注釋:
[1] 《全唐詩》卷
[2] 參見張興武《五代作家的人格與詩格》
[3] 《美的歷程》李澤厚
[4] 《全唐文》卷889 清董誥編 孫映逵校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