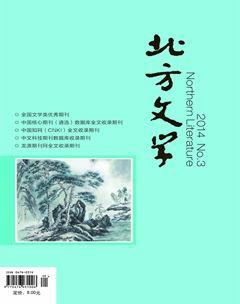如果文學(xué)給你帶來幸福
任寅
《文學(xué)少女》(全8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日)野村美月 文、竹岡美穗 插圖,黃瓊仙、哈娜譯)是本有趣的書。
選擇其中的一個小情節(jié):有兩個女人A和B,是中學(xué)時就認(rèn)識的朋友,A沉靜冷漠心思重,仰賴出版社編輯C的賞識成為了作家。C是A的恩師,也是A最衷心的讀者,可C最后娶了熱情開朗的B為妻。這讓三人之間出現(xiàn)了一道無形的墻。后來B和C因車禍身亡,A收養(yǎng)了二人的女兒D,卻從未和她說過話,日后A將這段經(jīng)歷寫成小說,書中道盡了對B的恨,還暗示B和C是A殺死的……
大凡優(yōu)秀的懸疑小說,有很多是在開始就布下了的思維陷阱,誤導(dǎo)讀者一點點陷進(jìn)去,直到答案揭曉讀者才恍然大悟——和一開始設(shè)想的完全不一樣!上述的情節(jié)其實也是一個思維陷阱——乍看之下是為了男人好友反目的三角戀,而真相到底是什么?
《文學(xué)少女》的特色是每個故事都會找到一篇名著的影子,比如上述故事就源自于法國作家紀(jì)德的小說《窄門》。看過的朋友可能會說:哎,這和《窄門》的情節(jié)不一樣啊。別著急,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處。
借鑒以前的名著的故事是個有趣的手法,但如果是機械的套用,很容易被扣上“抄襲”的帽子。作者野村美月高明之處就是:不套用,而是對原有故事進(jìn)行衍生和解讀。比如《窄門》是男主角杰羅姆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自己愛慕的阿莉莎與愛慕自己的朱麗葉之間的故事,而野村則將敘述人做了個調(diào)整,以阿莉莎的視角來講述她與朱麗葉的故事。阿莉莎與朱麗葉的關(guān)系原作著墨不多,不過二人是青梅竹馬又志趣相投是毫無疑問的。后來朱麗葉為了成全杰羅姆嫁給一個大她很多的富商,阿莉莎必定會因摯友離去而傷心,后來朱麗葉為了丈夫放棄了鋼琴和讀書,阿莉莎也必定會感到失落。而那個ABC的故事正是由這個全新的視角衍生出來的。
A并不恨B,她憎恨的是C,因為C搶走了她最愛的朋友。所以B通過勾引C來離間B和C的感情——乍看起來不是很意外,不過是憎恨的對象換了而已。關(guān)鍵在于和母親性格氣質(zhì)相似的女兒D。A對于D的冷漠,表面看是A對B的恨轉(zhuǎn)嫁到她女兒身上,可事實上A不恨B,那么A的冷漠,則是由于勾引C的行為讓A心生愧疚,對B和C的死亡陷入自責(zé),導(dǎo)致她不知如何與D相處,甚至希望D憎恨她,殺死她!
怎樣?相比表象,真相是不是有人情味得多?
不只是《窄門》,像第一卷中關(guān)注那些讀了《人間失格》(太宰治著)后顧影自憐的讀者,以及第二卷中對《呼嘯山莊》情節(jié)的不足的完善,等等。全書七個故事,每個故事都是野村對一篇名著的重新認(rèn)識。懸念方面,在故事主線中不時穿插著男主角心葉的焦慮和“犯人”的焦慮,我也因此受到傳染對真相越發(fā)渴求起來。然而這并不是重點,《窄門》的故事是全書的核心章節(jié),野村想要通過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個道理:文學(xué)是可以給人帶來幸福的。
《窄門》講的遠(yuǎn)不僅是一段三角戀情。“窄門”源自于《新約圣經(jīng)·馬太福音》:
你們要進(jìn)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jìn)去的人也多。
Enter ye in at the strait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eth to destruction, and many there be which go in thereat:
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Because strait is the gate, and narrow is the way, which leadeth unto life.
阿莉莎作為虔誠的清教徒,深信只有在上帝處才能獲得至福,因此她為了讓杰羅姆不被塵世所困擾,她極力克制自己對杰羅姆的感情,希望最終能穿越“窄門”抵達(dá)天國彼岸。而A作為作家,將“獨自過窄門”視作作家的必經(jīng)之路。看到這里我不禁苦笑,堅信并尋找著窄門,獨自一人踏上荊棘之路的作家又何止是A呢?
人一旦成為作家,可能就要一生與孤苦為伴。《文學(xué)少女》提到的作家中,太宰治自殺而終,宮澤賢治一生孤苦,紀(jì)德被保守人士所排擠,艾米莉·勃朗特一直不被世人理解……不幸總是喜歡與作家為伴,我也曾一度這樣堅信。直到《文學(xué)少女》的女主角遠(yuǎn)子用堅定的語氣說:
“文學(xué)是可以給人帶來幸福的。”
相比起嚴(yán)苛的現(xiàn)實,這種樂觀未免過于幼稚。當(dāng)然,《文學(xué)少女》作為面向青少年的小說,傳播正能量無可厚非。但是,僅僅做出這種解釋又未免是我把這本小說看輕了。因為這個觀點雖然理想化了點,卻也不能算錯。
確實,太宰治或許是在寫完《人間失格》之后自殺的。他也寫過不少讓人看了之后心情黯淡的作品,或許《人間失格》真的是太宰治得到的答案。
但這并不是太宰治的全部啊!
太宰治的作品中,還是有很多善良溫和的人。雖然平凡又懦弱,但是卻努力變得堅強的角色也很多。
“在給朋友的信里面,賢治也曾經(jīng)說過自己的故鄉(xiāng)是一個骯臟的小鎮(zhèn),鎮(zhèn)里也盡是一些陰險的人。真實的賢治,絕對不是什么圣人君子,他的生命中滿是些無法好好做下去、沒有達(dá)成的事情,有的只是連續(xù)的敗北。
但這樣的賢治,有把自己所感受到的絕望和痛苦,以及對于如此不堪的現(xiàn)實的憎恨寫進(jìn)自己的作品中么?賢治寫下的故事,難道是充滿敗北和慟哭的故事么?”
這是遠(yuǎn)子學(xué)姐在書中留下的兩段話。就像開頭的那個的故事,主人公最終用善意的目光去消解A的惡意,和用理想的角度去消解作家在人生中的苦難一樣。但是這種理想化我并不認(rèn)為盲目樂觀,因為“文學(xué)會給人帶來幸福”的觀點不是錯的,毋寧說,它給了我重新認(rèn)識文學(xué)與寫作的契機:文學(xué)不見得非要批判、質(zhì)疑什么,寫作不一定非得與孤獨寂寞為伴,如果質(zhì)疑與反思是文學(xué)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那么給人們帶來幸福和快樂,是否才是文學(xué)的終極意義呢?
寫到這里忽然想起了我的父親:父親這兩年開始寫青少年文學(xué),最近他說他遇到了瓶頸,因為最近的小說里總會出現(xiàn)批評、質(zhì)疑的聲音。我明白這不是有心的,寫了幾十年的成人文學(xué),靠一兩年時間就轉(zhuǎn)變思維實在不現(xiàn)實。不過仔細(xì)想想,自打我記事以來,父親從沒有教過我“文學(xué)是幸福的”的道理,也許是理性思維占主導(dǎo)的人不會如此樂觀,而青少年文學(xué)過于理想化的特質(zhì)看起來不那么接地氣。不過為人處事這回事,更多的是取決于自己——如果一個人相信這個世界是美好的,他才有可能做個好人。
“文學(xué)可以給人帶來幸福”,雖然不一定會去歌頌人間的真善美,但是這個道理可能會提醒我們,要重新拾起對文學(xué)的信心。文學(xué)如果能給人幸福,那么,創(chuàng)造文學(xué)就不是作家的個人行為,而是面向全人類的神圣的使命。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