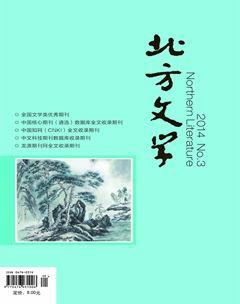秦地小說的都市民間與鄉土中國書寫
摘 要:秦地作家無論是立足鄉村還是面向都市,都從自然和民間的肉身化的生存精神中汲取藝術創作的素材和營養,展現了民間生活的真實樣態,在對地域鄉土進行描繪的基礎上達到了對社會歷史和生命存在的高度理解和概括,他們的作品不僅帶有濃厚的三秦大地泥土氣息,也在某種程度上展現文化中國的鄉土味,成為映現時代精神的里程碑。
關鍵詞:秦地小說;都市民間;鄉土中國
陜西是一個農耕文化占主導地位的省份,陜西的主要作家如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都生于農村,對民間的生活有著深刻的體驗,雖然后來身居都市,但喧囂的城市生活和建立在消費主義文化基礎上的道德行為方式,使他們心里難以接受,始終保留著農耕文化的習俗和生活習慣。與底層生活保持著聯系,他們也從自然和民間的肉身化的生存精神中汲取藝術創作的素材和審美的智慧,揭示人生也創化人生。
秦地的都市題材小說,回歸傳統,回到民間;鄉村題材小說,回到實存,回到人民真實的生活。作家們基于民間立場的書寫,揭示出被歷史有意或無意地遮蔽和忽略的民間生活樣態,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將目光從尋根文學對傳統文化的形而上層面,轉向腳下生存的大地,將尋根文學對傳統文化尋求依附的單純認可,變為對它的流連、嘆惋與批判,展現出以農耕文明為主導的三秦大地的精神特點。
秦地作家以都市為題材的作品較少,《廢都》、《熱愛命運》、《白夜》等是秦地作家小說里鮮見的以都市生活為題材,并且都共同地描寫了文人的民間化的作品。《廢都》對都市民間文化的描寫最為典型。小說雖然以西京城這個“都市”為題材,但卻是一部具有傳統的文人趣味和審美傾向的作品。主人公莊之蝶的姓名頗有意味地讓人聯想到“莊生夢蝶”這個典故,這和小說開頭西京城出現的種種異象,以及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和命運一起,昭示了浮生如夢,恍兮忽兮的人生感受。作為作家的莊之蝶,他享有巨大的名聲,在他所生活的城市,幾乎無人不識。但除了一些應酬文字,不曾見他寫了什么,只知道他一直力圖寫一部作品,一直在為此焦慮,但最后這部作品將是什么樣子,仍然是無從知曉。莊之蝶這個形象突破了五四以來知識分子新傳統的單純性,《廢都》的“濁氣”顯示了“民間文化”藏污納垢的特點,并以此顯示了其對政治話語和知識分子人文主義的反諷。[1]
《廢都》雜陳了新舊時代的文化因子,表現的是時代精神沉落都市民間并與之化合之后的奇妙產物。小說無論是敘事方式還是視角,都具有游離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言說方式和道德判斷標準的民間意味。表現了作家對《廢都》所蘊含的文化舊根的理解與沉迷。但是《廢都》對傳統的“復歸”并不是與現實的脫節,如作品的主要人物,作為西京城四大名人之一的莊之蝶,正是對現實境遇不滿,所以才將精神寄托于一塊石磚,兩方古硯,溫習舊日的繁華,讓精神得到安慰。濕漉漉的文化環境,精神的潮氣困擾了這些人,現實的困擾得不到真正的解決,失去了精神的活力,但又尋求著一種解脫,于是到物質的享受里去滿足內在的精神渴求。因此,有人看到,以此而言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后裔們,也都是生長在一個有著光榮過去而后來衰敗下去的文明古國,在這個意義上,《廢都》展現的就不僅是“西京”城的文化病象,更是我們國族精神在這個時代的一個化身。[2]《廢都》描寫的文化病象,顯示了作家對社會生活的敏銳感知,并且幾乎是預言性地被當下的生活所證實,賈平凹的作品因此有著比別人“舊”、又比別人“新”的東西。
秦地作家基于民間立場的書寫,揭示的是多元文化相交織的民間生存景觀,官方的儒家文化,自然、宗教、世俗均可成為它的價值取向。民間文化不排除一神教的統治,也不排除政治和知識分子的啟蒙精神,但它們一經融入民間,就消解了它們的本來意義,成為一種復雜的存在。因為民間對多元話語的吸收,采取的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生存至上的法則,這是他們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和熱情擁抱生活的結果。
如小說《秦腔》里有一個場景是描寫清風街村干部開會, 主任君亭提出建立農貿市場,支書秦安卻堅持上一屆班子的淤地設想。本來是寫農村建設方針的討論, 最后變成了對農村民主直選的質疑, 而一場無結果的民主討論, 最終還是靠陰謀來定輸贏。作家本意并不是在夏天義與夏君亭兩代村干部的對立意見中尋找中國農村的未來前景, 通過亂哄哄的現實場景的展示, 他著意描寫了農村民主形式的徒有虛名, 以及靠陰謀來解決人事糾紛的官場特色。這與合作化運動以來中國農村題材小說主題先行、圖解農村政策的傳統徹底劃清了界限。[3]
楊爭光的小說《從兩個蛋開始》是一部關于趙北存這個人物的傳奇,許多不可能的事情在他那里都成為現實。如果把這部長篇小說作為這個村莊的編年史,這個舞臺上的核心人物無疑是趙北存。趙北存之所以能當此大任,并不因為他是歷次運動規則的制造者,他作為一個民間小人物,無意間以其荒誕不經的言論遇到了另一個荒誕。小說的第一輯寫了土改運動、人民公社化中的11 件事情。趙北存進農會之前, 因為他偷過別人家的西瓜,還在他叔伯嫂子蓮花跟前耍過流氓, 雷震春、楊富民為了落實這些事情, 當面調查趙北存, 趙北存講述了兩件事情的經過。區長劉昆在得知情況情況后不但沒有阻攔趙北存加入農會,反而認為趙北存偷西瓜和捏蓮花的奶子體現了毅力、恒心、智慧, “說明他肯動腦子會用心思, 四兩撥千斤。”趙北存從此“脫穎而出”, 成為日漸受重用的人, 以致后來成了多年掌握符馱村權力的人。二流子出身的趙北存當上了符馱村的村支書,符馱村經歷了合作化、公社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毛澤東逝世、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等一系列大事,登上歷史舞臺的趙北存不僅體現著荒誕的歷史邏輯,他還是許多荒誕事件的導演者。這個人物因此承擔著作者對革命、政權和民間的反思功能。
京夫的小說《八里情仇》也塑造了左青農這個時勢寵兒。這是一個跨越改革前后兩個時代的人物,在20世紀60年代,為了撈到高升的政治資本,通過樹假英雄興啟,他升遷為公社黨委委員,他在亮麗的革命口號下大售其奸,“文化大革命”后期,他被開除留用,在新時期,他由原先對政治的狂熱追求一改為對金錢的崇拜和迷戀,辦起了生產迷信產品的火紙廠,企圖通過辦企業,“用金錢再展雄風,實現當年未實現的宏愿”,他利用社會上的權力腐敗,鉆法制不健全的空子,行賄偷稅漏稅,“以小錢換大錢”,他得意自己“有錢會玩錢”,得到了“精神可貴”、“開拓型人才”、“育人模范”、“全縣有名的企業家”的贊譽,奪回了政治上的榮耀和威勢,又成了時世的寵兒,一個“不倒翁”。endprint
秦地小說的厚重離不開三秦大地厚重的文化滋養,秦地文學的民間書寫更是直接體現了地域文化的特點。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秦地文學就只反映一個封閉自足的文化空間,秦地文學無論是書寫農村生活還是城市生活,其所反映的文化心態,無論是鄉土民間[1]還是都市民間[2],都是中國某種歷史文化的隱喻和縮影。其映現的歷史內容用賈平凹小說《古爐》封面題記中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一個人,一個村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段不可回溯的歷史。”
賈平凹小說《古爐》中的丁霸槽,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孤身度日,不愿參加集體勞動,以修鞋謀生,常憤憤不平,認為時運不濟。“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他聞風而動,率先在古爐村舉旗“造反”,導致古爐村內部矛盾的白熱化,從而形成了以丁霸槽為首的榔頭隊和以天布為首的大刀隊兩個幫派的械斗,最終血灑古爐村,多人喪命,最后霸槽和天布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下被槍斃正法。賈平凹的小說并不是以故事本身取勝的,這部小說寫“文化大革命”,是宏大歷史敘事的鄉村版文本,把政治當生活去寫,用一種見微知著的方式進行歷史文化反思,更把鄉土中國寫得那么深刻。[4]
賈平凹從“商州”系列開始深入民間,描寫鄉村現代化進程中的點滴變化,有憂思但更多是謳歌,小說《浮躁》一下就嗅到改革初期社會空氣中不太對勁的和悲劇性的東西,照亮了人們對時代的認識。《土門》揭示了鄉村現代化進程的不可抗拒及其給鄉村社會傳統文明帶來的悲劇性毀滅,《秦腔》則為鄉村文明的式微唱出了最后的一曲挽歌,描繪了農民進城務工者的不幸,民工狗剩外出挖礦, 得了病被退回來, 靠拾糞度日, 終于被迫自殺。另外兩個民工到州城去拆水泥房, 沒有掙下錢, 為了回家過年去搶劫, 結果被判了刑。羊娃去城里打工,為了兩百元殺了人, 被省城的公安局抓去……。鄉村社會純樸美好的人性受到金錢物欲的侵蝕,如俊德在城里收拾垃圾而致富, 他女兒雖身份暖昧, 但回鄉來珠光寶氣, 仍受到鄉人的羨慕。倔強刻苦、嘴硬心慈、光明磊落的原村干部夏天義,堅持淤地的理想熔鑄了幾千年農民傳統生活方式的理想, 但是他的實踐是失敗的, 甚至是悲壯的。結尾以一個山崩地裂的災難場面,讓這樣一個背時的、處處惹人厭的老一輩人物,最后埋葬于山體滑坡, 連尸體都挖不出來, 甚至連一塊墓碑也是空白的,表達了作家對于農民傳統生活方式及其倫理式微的無以言狀之感情。
高建群以《最后一個匈奴》為代表的“大西北三部曲”正是于淡出人們視野的歷史深處,探究曾在這塊土地上輝煌地生息過的一個民族的足跡。正是立足于陜北這塊土地和對民間人生圖景的描繪,路遙小說的苦難意識才會那樣的深沉冷峻,他筆下的人物才深深地打動人們的心靈,傳達出粗獷遼遠、樸素渾厚的審美意蘊。
總之,秦地作家的小說,在立足于對地域鄉土進行描繪的基礎上達到了對社會歷史和生命存在的高度理解和概括,他們的作品既帶有濃厚三秦大地的土氣息,也在某種程度上展現文化中國的鄉土味,成為時代精神的里程碑。
注釋:
[1]民間:相對于國家政權而言,民間文化具有自由自在的審美風格和藏污納垢的獨特形態,而民間的傳統則意味著人類以原始的生命力緊緊擁抱生活本身的過程,也因此迸發出了人們對現實生活的愛與憎,以及他們對于人生欲望的追求,這是任何道德說教都無法規范,任何政治條律都無法約束,甚至連文明、進步等這樣一些抽象概念也無法涵蓋的自由自在的東西。見陳思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391~39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都市民間:1.在賈平凹本人看來,時代在進步,但整個中國文化的傳統之根仍深植人心,正如老舍筆下的老北京市民仍舊是舊的鄉土中國的兒女;2.陳思和在評價王安憶《長恨歌》的結構與敘事時指出“以前,與國家權力中心相對應的鄉土民間往往是通過家族或宗族的形態來體現的,而在現代都市里,與國家權力中心相對應的卻是個人化的存在,它在包容了國家權力意識形態的同時,也通過制造多樣化的、個人性的文化審美形態來抗衡和分解大一統的國家歷史敘述,這樣的敘事,應該說就是一種都市民間的敘事。”見陳思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392~39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參考文獻:
[1]陳思和:《民間的還原——文革后文學史某種走向的解釋》,61頁,載《文藝爭鳴》,1994(1)。
[2]王富仁:《<廢都>漫議》,見郜元寶,張冉冉編:《中國當代作家資料研究叢書 賈平凹卷》,243~244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陳思和:《論<秦腔>的現實主義藝術》,7頁,載《西部》,2007(4)。
[4]李星:《我覺得這是賈平凹最好的小說》,賈平凹《古爐》研討會發言,2011-06-08。
作者介簡介:汪宏(1972-),女,安徽六安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現就職于陜西廣播電視大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