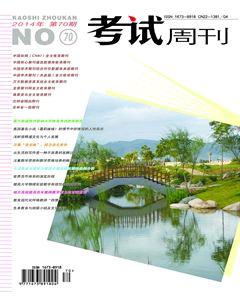對鄉土和家園的守望
嚴明
沈從文是以一個湘西作家身份進入文壇的,他的作品藝術帶有湘西邊地人民特有的樸野氣質,特有的色彩、氣息和聲響。他把自己的社會理想的樂園安置在歷史和地理上催生《楚辭》,并享有桃花源盛譽的湘西,盡情地贊頌了那里的古樸民風,描繪了一種他心目中理想的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邊城》就是這類作品中最杰出的代表。本文由沈從文的中篇小說《邊城》探討他蘊含在作品中豐富而獨特的民間性。
一
《邊城》故事的發生地茶峒所在地屬花垣縣(舊稱永綏縣),是一個苗漢雜處之地。據史料記載,當地的苗族人數遠超過漢族人數。苗族流傳著許多民歌,并盛行唱歌之風,沈從文的《邊城》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情況。如:《邊城》中老船夫“想到了本城人20年前唱歌的風氣,如何馳名與川黔邊地”。同時沈從文對民歌的運用,對于人物思想感情和心理的描寫,對于人物性格的塑造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例如《邊城》中寫初五那天翠翠讓祖父進城,自己留下守船,她“溫習著上次過節,兩個日子所見所聞的一切,心中很快樂,同時萌生了一種對二老的極為微妙的思念,蕩漾著初戀的感情的漣漪。過渡的人中,特別引起她注意的是那些打扮了進城的女孩子。無人過渡時,等著祖父,祖父又不來,便盡只反復溫習這些女孩子的神氣,且輕輕地無所謂地唱著‘白雞關老虎咬人,不要別人,團總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銀釧子,只有我三妹莫得什么戴,耳朵上常年帶條豆芽菜”。這首不完整的民歌恰恰是在“無所謂”、無意識的狀態中,唱出了翠翠面對的貧富差別的現實,唱出了她的憂郁和憤懣。老虎咬人,“團總的小姐派第一”,這是窮人的女兒的觀點,間接地表達了一個懷情的少女對于婚姻以金錢勢利為轉移的憎恨。翠翠一直不愿吐露出自己的真實感情,一方面固然是這個農村少女害羞的情態,另一方面,她已經感受到她的家庭與儺送二老家庭貧富差別,感覺到王鄉紳碾坊陪嫁的威脅。如果說這些感覺是越到后來越明晰的話,那么,在儺送二老闖進她心扉時就已存在了,只不過還處在朦朦朧朧的,連她自己都沒有明確意識到的東西,表現了這個美麗的農村女孩極為復雜、微妙的感情心理,同時顯示出了某種現實關系。
表達青年男女的真摯之情,熾烈的情感,民歌是非常重要的表現形式。沈從文在《邊城》中雖然沒有引出情歌之字,但運用側筆達到了出色的效果,也足以——或者甚至比引出情歌文字更能使讀者從情歌中獲得強烈的美的享受。如《邊城》中寫儺送二老在月夜高崖上為翠翠唱情歌,他的歌聲產生了一種奇妙的效果:“翠翠不能忘記祖父所說的事情,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的歌聲浮起來了,仿佛輕輕地各處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躥過對山懸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掛船時,她仰頭望著那些虎耳草已極熟悉。懸崖三五丈高,平時攀折不到手,那時節卻可以選頂大的葉子作傘。”能夠產生這樣奇妙果的情歌當是怎樣的優美、動人。借助于這種描寫,人物的心靈美,作品所力圖表現的邊地風俗人情的詩意美,就更加濃郁。
二
在沈從文的作品《邊城》中風物、風俗的描寫有相當突出的地位。《邊城》故事發生地茶峒這個地方特有的“物”,往往都能映現當地的“風”,即使非茶峒當地所特有的“物”,因為融入到茶峒這個環境中也帶有了當地的“風”,它成了茶峒這個地方特點的外在標志之一。作者將這種風物與風俗、人情的描寫交織在一起,就構成了人物活動的特有環境,營造出了故事必需的氛圍,加強了生活實感。如《邊城》中寫茶峒地方的地理形勢、物產、河街的市面與水碼頭,小溪流上的渡船及兩邊的白塔,深翠逼人的竹篁和崖壁上肥大的虎耳草,以及老船夫裝燒酒的竹筒,孩子穿的尖尖頭,新油過的釘鞋……這一切所構成的環境和氛圍是那樣寧靜、古樸、秀美,假使你讀過《邊城》就會感到,這樣一個故事是會有這樣的環境和氛圍,它有確定的地方特征,而故事的真實感就是這樣產生的。
在《邊城》中和風物描寫緊密交織在一起的是風俗描寫。20世紀中葉,湘西人民生活狀況、風俗人情、社會心理,都鮮明地保留在他的作品中。在《邊城》中人物活動的主要背景是三次端午節。端午節是當地民間最重要的節日之一,而龍舟競渡則是端午節期間舉行的盛大的活動。作者對龍舟競渡作了具體而細致的描繪:
“每只船只可坐十二到十八個槳手,一個帶頭的,一個鼓手,一個鑼手。槳手每人持一只短槳,隨著鼓聲緩促為節拍,把船向前劃去,帶頭的坐在船頭上,頭上纏裹著紅布包頭,手上拿兩支小令旗,左右揮動,指揮船只的進退。擂鼓打鑼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劃動便即刻蓬蓬鐺鐺地把鑼鼓很單純地敲打起來,為劃槳水手調整下槳節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聲,故每當兩船競賽到劇烈時,鼓聲如雷鳴,加上兩岸人吶喊助威,便使人想起小說故事上梁紅玉老鸛河水戰擂鼓種種情形。”
當然,沈從文不是單純地為記載風俗而寫風俗,他的風俗描寫之所以具有藝術魅力,是因為其中滲透他的感情評價,表達了他的美學理想。如前面關于端午節的龍舟競渡,在作者筆下顯得如此熱火,如此富有詩意,正是作者對當地人民那種互助互愛、好勇敢樂、積極向上的品格的贊美。
《邊城》中語言的生活化、濃郁的鄉土氣息,證明了沈從文小說創作與民間生活的密切聯系。沈從文對語言文字是十分講究的,他曾說:“文字是作家的武器,一個人理會文字的用處,比旁人淵博,善于運用文字,正是他成為作家的條件之一。”這里所謂文字,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字語言,包括非常性格化的人物語言和作家的描述語言。人物語言比起作家的描述語言,可以更多地來源于生活,而描述語言則因是經過提煉、加工過的文學語言,又要明快、平易,接近口語和生活化。沈從文就很著力追求獲得這種語言,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形成自己的語言風格,即語言的生活化和濃郁的鄉土氣息。這種語言風格在《邊城》中得到了較完美的體現。例如《邊城》一開篇就有這樣一段話:
“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叫‘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的小塔,塔下住著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單獨的老人,一個女孩子,一只黃狗。”
這段文字極其明麗、澄清、自然,像用水淘洗過了似的,又很接近口語,頗能代表他的語言特色。同時,《邊城》中還有一些方言、土語及民謠民諺的運用。如“你個悖時砍腦殼的”和“牛肉炒韭菜,個人心里愛”等也都使小說的民族和地方色彩更加濃郁。
當然,《邊城》的藝術成就是不能和魯迅、茅盾這些巨匠的作品的藝術成就比肩的,但它能在國內外享有一定盛譽,應該說,它所具有的相當濃郁的地方和民族的特色,它與民間生活的密切聯系,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青藍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