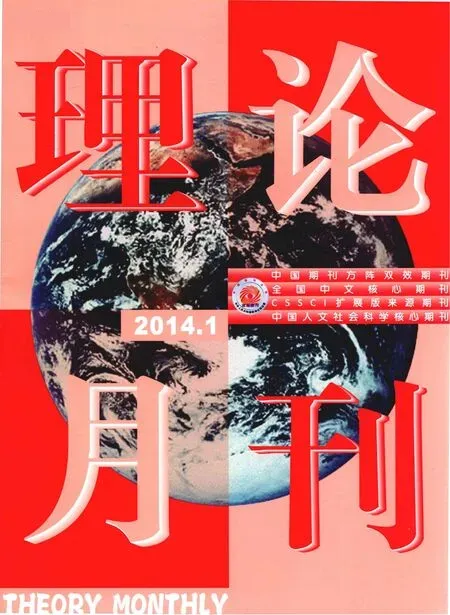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的邏輯及啟示*
赫曦瀅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吉林 長春 130033)
在探討基本歷史的未來時,佩里·安德森(Preey Anderson)認為“主要的歷史問題通常包含雙重困境:一是歷史可變因素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二是辨別歷史事件中相關關系網的層次體系”。大多數歷史和社會學家處理歷史問題時都會采取以一種理論為主導的理解方式。拿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是承認現代歷史的中心組織要素是生產方式,利用這個概念工具,馬克思主義者通過生產方式的轉變來系統理解現代歷史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一系列基本元素。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他們已經通過生產方式這一核心概念找到了未來世界發展的航向。通過生產方式這條主線,馬克思找到了原始積累這個關鍵的研究對象。在對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進行分析時,馬克思強調資本積累的實質就是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相分離的過程,當勞動者的土地被無情的剝奪時,他們便成為了無產階級并投入到了資本主義工業大生產中。
如果說馬克思已經肯定的指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趨勢,它卻在定義和形成城市的分析中沒有捕捉到城市現象或者解釋城市中的問題。因此,這不僅僅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需要發展完善,而且因為我們可以通過理解城市問題來擴大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從而擴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視野。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出現了一股“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的思潮,以獨特的理論視角,對資本主義時期城市進行了尖銳的批判,開辟了西方左翼批判新的理論空間。所謂“新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西方社會出現的新型意識形態,是西方歷史發展中的獨特現象。作為反資本主義的西方激進批判理論,新馬克思主義之“新”在于它是一種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相左的“另類馬克思主義”,它的核心理念在于“重新發現”馬克思和“重新設計”馬克思主義。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城市學者主要出現在法國,也被稱為城市研究中的“法國馬克思主義學派”。1976年,C·G皮克萬斯出版了《城市社會學:批判性文集》,將法國馬克思主義城市研究引入了英語世界,并將列斐伏爾、大衛·哈維和曼紐爾·卡斯特并稱為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三劍客”。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對西方城市社會發展和變遷中出現的城市問題進行的理論解讀,極大地推動了其他國家馬克思主義城市學研究。
一
當接近城市問題時,馬克思主義變得相對保守,它的理論優勢在于強調各種生產方式的時間性與西方城市發展的時間順序之間的相關性。與之類似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以時間為線索方法分析了封建、商業和資本主義城市的差別,全部文獻幾乎都是這樣的分析模式。但是,單純以時間維度為研究對象的模式使得城市研究走進了一條死胡同。
在馬克思的研究中,城市一直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重要“容器”而不是動因,馬克思對城市的興趣只集中在資本主義工業化時期城鄉對立和城市階級斗爭等幾個方面。因此,毫不諷刺的說,傳統馬克思主義對空間和城市的認識十分模糊,很少涉及關于城市空間是重要的或是渺小的論述,這種漠視暗示了后者。城市在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中被忽視了一個多世紀,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的早期發展過程中重新發現了城市。后來,第二和第三國際才真正重視城市和鄉村在社會主義過渡中的關系。但是,這些理論和實踐的立論基礎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在特殊生產方式關系中的勞動分工。這一理論有著反城市色彩,并在馬克思主義實踐中指導著各國的行動。除了理論和政治趨勢外,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馬克思主義都沒有將城市研究納入到關注的中心,包括關于城市空間形式和他們與大規模社會進程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馬克思主義始終堅持以勞動分工作為研究的基點。
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雖然有很多不足,但仍然可以被證明是理解重要城市現象的一個有用工具:如大規模的城市化;資本主義和非資本主義城市的不同點;土地利用和社會地理學的轉變以及城市的衰落與更新的循環。馬克思主義處理城市問題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系統地表現資本形成和集中的關系,以及19世紀城市工業城市的集中發展,從而擴大馬克思主義核心問題的分析方法,即資本的積累。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馬克思把城市發展加入到勞動分工的歷史軌跡中是19世紀末地理學研究中的一個重大進步,通過他的理論也暗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空間因素。
二
20世紀下半葉以來,有很多具有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城市著作產生。馬克思主義與城市對話的再次興起主要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開始的,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的一系列早期作品中體現了這一主題,包括《城市的權利》(1968)(《Le Droit à laville》)、《城市革命》(1970)(《La Révolution urbaine》)和《馬克思主義思想與城市》(1972)(《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ville》), 他將馬克思社會批判演化為空間的分析批判,開創了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研究的先河。他以空間作為哲學批判的基點,將經典馬克思主義所關注的“資本主義生產就是要用時間消滅空間的限制”轉換為“后馬克思哲學”的思考方式,即所謂消滅空間的限制,其實就是“創造出新的空間”。資本主義“為什么幸存而沒有滅亡”就在于資本主義對空間的占有,“通過占有空間,通過生產空間”。[1](p21)在列斐伏爾的“三位一體”的空間辯證法中,他一直試圖將黑格爾、馬克思和尼采的理論做以歷史的綜合,從而構建開放和發展的總體。因而,列斐伏爾提出了一個既非主體辯證法又非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的人”的概念,他認為辯證唯物主義的本質就是通過抽象化去克服抽象化,再現“事物整體”的思維過程,只有通過總體的方法論,才能真正實現人的自我總體化的揚棄過程。在列斐伏爾的著作《空間的生產》(1976)(《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他把“三位一體”的辯證法應用于空間和社會的構建,開啟了社會、歷史和空間研究的新紀元。[2]同時,他反復重申,存在著一種空間的政治學,空間是經濟、政治和文化觀念的權力斗爭場域。城市的興起與擴張成為大規模資本主義空間重組的標志性事件,城市景觀的感覺欲望化源于資本生產邏輯的滲透,其中隱匿著消費意識形態的操控運作,城市空間的單向度導致人們生活的全面異化。[3]
曼紐爾·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代表性著作在70年代初期推動了城市社會運動。卡斯特的代表性著作 《城市問題》(1972)(《La Question urbaine》)引領了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城市學派的發展,再度發現了城市作為客體應被馬克思主義所關注。他試圖把社會生產歷史過程的空間聯系起來,并貫徹以國家權力(政府干預),他創造性地把列斐伏爾關于空間與革命的寫作,阿蘭·杜蘭的社會運動理論和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綜合在自己的理論中。[4]他把基本的社會進程關系的定義進行了空間化,生產等同于“生產手段的空間表達”(住房、公共娛樂);交換起源于“生產和消費之間轉換的空間化”(交通、商業);管理是“政治和制度系統與空間的結合”(市政管理、城市規劃)。他還把意識形態加了進來,意識形態是“用符號網絡來組織空間,符號的意義由空間形成組成,它的所指是意識形態的內容”。[5](p131)卡斯特批判地吸收了列斐伏爾關于城市空間中心化是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動力的觀點,但是在理論上反對列斐伏爾以早期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異化概念為根據推導這一理論的做法,他認為列斐伏爾“把空間看做是創造性自由這一人的屬性的作為,是人的愿望的自發表現”[6](p92)是十分錯誤的,空間只是社會的一個重要物質維度且與其他物質維度發生關系,進入這一關系的人賦予空間以形式、意義和功能。[7]卡斯特認為,社會結構的重要體現就是城市空間,城市空間由經濟、政治、文化系統共同組成。他的理論一直圍繞著三個重要的主題展開,即對芝加哥學派的批判、“集體消費”的構建和城市與社會運動。卡斯特最早在學界被關注源于他對城市學領域一直處于主流地位的芝加哥學派的質疑,他試圖建立新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城市體系,進而解釋資本主義城市形成與發展的進程。在這一過程中,他發現了“集體消費”的概念,認為在經濟的生產、交換、消費三個環節上,城市的主要功能不是生產和交換,而是消費。所以集體消費問題是發達資本主義城市中的核心問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依賴于國家提供消費物品和服務,集體消費不足將導致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的矛盾和動蕩。卡斯特的理論在學界引起的強烈反響,他對傳統城市理論發出挑戰,以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作為未來城市發展的替代模式,帶動了結構主義與城市研究相互融合,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城市問題研究的新紀元。
哈維對空間研究的靈感來自于對列斐伏爾的興趣,他最早的空間理論著作《社會主義與城市》(1973)(《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堅決地與自由地理學決裂,書中的社會主義構想把城市空間納入到資本主義積累方式的分析中,然后把城市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作為書的主題。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研究城市問題,是哈維的一大學術特色,他曾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資本主義城市發展進程進行了細致的描繪,填補了學術上的空白。哈維曾這樣總結馬克思主義城市化研究的主題和成就:
馬克思主義者在20世紀60年代轉向城市問題分析,他們尋求理解城市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方式、社區基礎上的社會運動和他們與勞工運動的關系—都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的關系在城市中的研究像生產、需求和勞動力再生產一樣需要被精細的分析。城市同時也是一個便利生產、交換、消費的建成環境,是一個空間的社會組織形式,是一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分工的特殊表現而被研究。所有這些概念都是城市化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統一體的出現。[8](p503-504)
當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還在《城市問題》和《社會正義與城市》中努力應付城市的困境時,很多新的城市研究開始挑戰卡斯特和哈維的觀點,以這種方式激勵其他人去研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原則。如愛德華·索亞(Soja)在《第三空間》(2005)(《The Third Space》)中用一種“社會空間辯證法”來解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后大都市時代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如后殖民主義、女權主義、階級和種族問題等。而鮑德里亞 (Jean Baudrillard) 則在 《物體系》(1968)(《System of Objects》)中力爭說明全球化對都市問題的深刻影響不僅僅是經濟,而是我們生活中的時---空觀念的巨變,因此消費主義就必須從文化研讀的角度加以探討。與他遙相呼應的美國社會學家沙朗·佐京(Sharon Zuki)在《城市文化》(2006)(《The Cultures of Cities》)一書中認為,文化同經濟一樣是控制城市的有力武器,人類不是簡單的生活在城市之中,而是很大程度上從城市生活的復雜性之中發源,我們不應忽視了城市空間特殊性的解碼性潛力。
20世紀80年代初卡斯特和哈維的著作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城市化研究,填補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空白。總的來說,他們的觀點挑戰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城市的看法,開辟了重新思考城市問題的不同路徑。在卡斯特第二部代 表 作 《 城 市 與 民 眾 》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中,卡斯特把他關注的重心轉向歷史和城市社會運動斗爭的人類動因問題上。《城市與民眾》在組織、分析對象、敘述形式和理論目標等方面與《城市問題》明顯不同。《城市問題》通過批判城市社會學去發展一種城市結構的概念,其目的在于創造一個宏偉的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書中的經驗主義素材被用于闡明各種的理論主張,指定了城市研究的范疇是 “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并且提出了屬于這個范疇的結構理論。相反,《城市與民眾》只是在理論上分析了過去城市社會運動的個案,包括巴黎公社、1915年格拉斯哥租金罷工運動和當代巴黎、圣弗朗西斯哥、圣地亞哥和馬德里的研究。研究的重點主要是運動發生的背景、偶然性、文化性、多樣性和社會意義。主題幾乎在先前在作品中沒有出現過。階級斗爭不再是社會沖突和社會變革的唯一主軸。在這部著作中,理論的建構更像是木工在干活,一邊做一邊調整測量。而不像以往那樣,理論像是建筑,要先構圖才能建造。
如果卡斯特展開他的分析是為了不再讓傳統馬克思主義占據理論的特權,那么大衛·哈維繼續肯定了這樣做的重要性:“我在20世紀70年代轉向馬克思主義研究,再次肯定了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任”,近年來,他的大部分著作都集中在整合空間生產和空間結構方面,同時把空間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一個活躍要素。像卡斯特一樣,哈維也開始探索新的主題,完全超越了他過去對空間和生產的關心,這個主題并沒有直接扎根于權威的馬克思主義文章或是政治經濟的基礎上。如他在《資本主義城市化 的 歷 史 研 究 》 (1983)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第二卷中,通過對十九世紀下半葉巴黎歷史的個案研究,描述了城市景觀產生和塑造意識和經驗的方式。在《意識與城市經歷》(1985)(《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和《資本的城市化》(1985)(《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中,他著力于揭露資本主義社會中政治、經濟與城市地理、城市社會弊病的關聯性,分析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而具體論述了被傳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忽視的社會空間問題。在《新帝國主義》(2000)(《New Imperialism》)一書中,他將自己的理論評價為 “是對資本積累內在時空動力有關的帝國主義問題的重新概念化”。[9]他強調,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一個涉及全球的地理問題,而且資本主義國家曾經歷了“空間修復”(spatial fix)的過程,將自身積累的危機與階級矛盾轉嫁到國外市場。哈維認為在全球化時代,非正式、易滲透卻難以確定的權力的領土邏輯—區域性—在資本積累的時間和空間分子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產生了。[10]他在“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傳統概念中,加上“地理”一詞,成為 “歷史——地理唯物主義”(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使得他獲得了激進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旗手的美譽。
三
列斐伏爾、曼紐爾·卡斯特和大衛·哈維的共同特點是都對現代城市化現象進行了細致的剖析,提出自己對城市發展的階段化劃分,進而對全球化時代的城市進行了大膽的設想。他們大膽地延伸了馬克思的辯證法、資本積累、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斗爭的概念,著重探討了當代資本主義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關系。但是,在論述的過程中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和運用的方式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大衛·哈維作品的特點是大量闡釋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觀點,尤其是對《資本論》進行了細致的研讀,將傳統馬克思主義觀點作為立論的依據,同時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例證進行再解讀和延伸。通過這樣的過程,創造性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城市、空間問題相結合。與哈維相比,列斐伏爾和卡斯特似乎對馬克思主義不是那么執著,列斐伏爾曾經系統的分析了《共產黨宣言》,而卡斯特則沒有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有太多的停留。他們都將問題的核心對準了現實問題,更主張更新馬克思主義以適應全球化和網絡化的需要。
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研究還在不斷的發展中,不能稱其為一個統一的體系或者學派,它包含著不同的理論觀點和研究方法,不同的學者在研究中都保持著各自的特色。我們可以將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研究學者籠統地分為兩派:第一派是所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城市學家,他們一直嚴格的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思想來源,所有的結論都是圍繞馬克思主義理論基本問題而展開,沒有脫離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以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使命,最終研究的目標在于提出一定的政治實踐目標。大衛·哈維是這一派人物中突出的代表,他長期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在西方學術界實屬罕見。第二派學者在某一些具體的研究中引介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而通過這些理論提出自己有代表性的學術觀點,卡斯特在這派人物中比較有代表性。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是否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自己的信仰,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在當代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第二派學者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他們往往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一種政治信仰,所以他們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隨著時代的變遷,相信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研究將會更加多元化、自由化。
四
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的研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可以作為我們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視角。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的研究對馬克思主義學科和城市理論的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一方面,通過對城市問題的分析,填補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空白,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新領域;另一方面,通過將馬克思主義思想引入城市研究,突破了城市研究的傳統角度,突破了城市學科的封閉性和局限性。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的主要特點是延續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將資本積累和階級斗爭作為核心問題的研究方法,用實證的方法突出強調了在城市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資本和階級斗爭的重要性,使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煥發了新的生機。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宏觀性與微觀的城市現象相結合,更生動、更具體地揭示了城市發展的多樣性,使得宏觀理論得以解釋更多的具體現象。
但是,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也存在著固有的缺陷,尤其是結構決定論。它過分的關注于資本、積累和消費等因素對資本主義城市的改造,而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對城市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以及不同國家和城市的獨特歷史條件和人文環境對城市變遷的作用。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最近一段時間涌現出了一批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社會地方變量的差異性和獨特性的學者,他們力圖通過對人的行動和地方獨特性進行研究而發展城市理論的深度和廣度。
當前,隨著經濟和政治全球化的蓬勃發展,中國城市社會也步入了不斷更新的新時期。城鄉統籌發展的口號把中國再次推上了城鎮化的風口浪尖,而在改革開放的30年中,中國城鎮化道路的曲折和復雜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見。當前,中國城市經濟化“危”與“機”并存;城市社會凸現壓力,民生保障不斷受到挑戰;城市環境污染壓力增大,長遠挑戰不容忽視;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工業固定資產投資放緩;大規模投資建設將啟動新一輪城市化熱潮;城市密集區的戰略引擎作用將進一步凸顯。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認識城市社會物質和非物質環境發展和變遷的現象;如何引領資本,創造資本積累的條件;如何均衡利益,減少社會沖突和矛盾,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分析視角,值得我國學者深入研究和借鑒。
[1]Henri Lefebvre.the survival of captital,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 of production [M].Trans by Frank Bryant,London :Allison and Busby,1978.
[2]趙海月,赫曦瀅.列斐伏爾“空間三元辯證法”的辨識與建構[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2).
[3]謝納.都市文化研究與空間理論的興起[J].江海學刊,2007,(2).
[4]赫曦瀅,趙海月.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的批判性重構[J].社會科學戰線,2011,(7).
[5]Edward Soja.后大都市—城市和區域的批判性研究[M].李鈞等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6]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M].MA:Edward Amold,1977.
[7]林曉珊.空間生產的邏輯[J].理論與現代化,2008,(2).
[8]David Harvey.urbanization[M].MA:Blackwell Publishing,1983.
[9]David Harvey.In What Ways is “The New Imperialism Really New?”[J].Historical Materialism,2007,v01.15 Issue 3.
[10]赫曦瀅,常樵.資本帝國主義視野下的領土邏輯與資本邏輯[J].科學社會主義,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