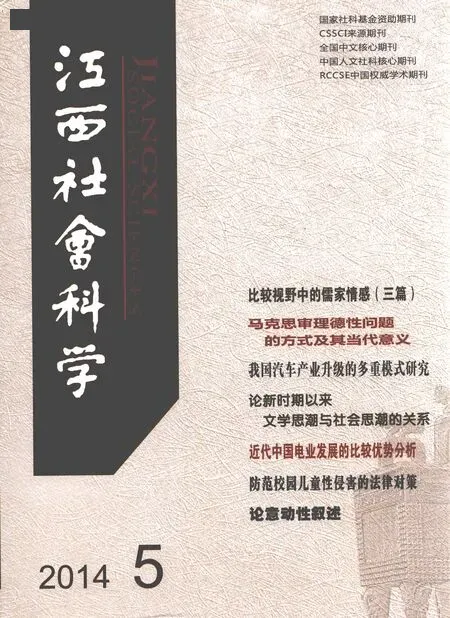北朝佛傳故事圖像藝術中的濟世觀念
■趙 鵬 江 南
佛教傳入中國之初,雖以其轉世輪回思想能滿足中國動蕩社會中流離失所的百姓亟需的精神需求而得到快速傳播,然而又不可避免地在很多方面與中國固有的傳統觀念形成對抗,進而引發一系列爭論。其中最為激烈的問題在于,其一是沙門不拜父母,其二是沙門不敬皇帝、王者及官長。前者涉及社會倫理問題,后者則涉及政治問題。這兩個問題爭論最為激烈的根源是,對中國傳統習俗而言,它們分別是對儒家文化“忠孝”思想的嚴重對抗,這對佛教自身在中國的發展傳播非常不利。但事實上佛教后來在中國社會取得了長足發展且逐漸與中國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化佛教,其中原因頗值得玩味。一方面它不得不轉變方式,至少在圖像傳播形式上表現出對中國固有文化的順從,另一個原因也是最為重要的因素,便是佛教本身的濟世觀念實質上迎合了中國儒家的禮教文化思想習慣。
北朝時期,佛教在社會上廣為流布,帝王百姓無不歸宗佛教而心儀于佛法。佛教經典認為,“行善猶如稼穡,播種善根即可收獲福報,故有福田之稱”。佛教“以像設教”,注重以藝術形象進行教義思想的宣傳和對信徒的教育,加之佛教信仰者認為,雕塑和繪畫佛像能得福,佛教傳入中國之后,將這種特殊的傳播方式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互融合,故而雕佛造像和繪制佛像壁畫便成為最受歡迎的宣傳佛教教義的藝術手段,并從這一時期開始逐漸形成獨具特點的中國佛教美術。佛教的福田思想教人以慈悲為懷,通過救度眾生,最終實現自身的圓滿,其中的普世思想實際上與中國傳統社會存在的濟世觀念有殊途同歸之宗旨。
一、乘象入胎與逾城出家中的濟世觀念
“乘象入胎”和“逾城出家”是北朝佛傳故事圖像最多的成組對稱佛傳故事畫,其典型代表有敦煌莫高窟第431窟壁畫,云岡石窟第5-11窟南壁佛傳故事雕刻。這兩個情節是佛傳故事中最重要的內容,是釋迦牟尼一生的轉折點。“乘象入胎”中,釋迦牟尼的前身善慧菩薩頭戴菩薩花冠,身著天衣,手持凈瓶,乘騎大白象,頭懸雙龍華蓋,從兜率天宮飛奔而來,下降到尼波羅南部迦毗羅衛國凈飯王家中投胎。王妃摩耶夫人因夢見菩薩乘六牙白象進入臥室而懷孕,而后生下太子,名叫悉達多。“逾城出家”中,降生在凈飯王家中的釋迦牟尼——悉達太子,年十九歲時,因出游四門,深感人生無常和生老病死之苦,厭棄宮廷生活。為了解脫人世的苦難,決心出家學道,但父王將他軟禁深宮。一夜,在天神的幫助下,悉達太子頭戴雙髻太子冠,身著王服,乘騎白馬,頭懸傘形華蓋,持韁催馬出城,奔赴深山修道。善慧菩薩和悉達太子都獨乘象馬,沒有天人陪同、歡送。
佛陀降生凡塵再經過苦修成道以救度眾生的整個過程,體現了其濟世觀念,其中乘象入胎和逾城出家兩情節因是整個故事中的兩個轉折點,對該思想的表達最為典型。入胎前的佛陀乃為兜率天中的菩薩,為救度眾生出離苦海而選擇投胎降世,經歷磨難與苦修,比之于艱難的成道過程,其目的本身即具有宗教對人生命的終極關懷之情,也即佛教思想的終極旨歸乃是為了解脫現世之苦,引導其進入西方極樂。
佛陀在乘象入胎之前對降生的種族、國家、家庭以及時間、因緣等問題都有嚴格的選擇標準,此降神選擇各標準的制定內含了佛教之濟世觀念。如選擇國家和家庭的標準乃是“迦毗羅衛國,國家種姓熾盛,人生滋茂和順,奉敬尊長,眷屬和睦,五谷豐熟,安穩貧賤。國王性行仁賢,功勛卓著。王后品行仁良,樂善好施,心如蓮花般高潔不污”。可見樂善好施、心存善念以養樂眾生、造福人民為基本品行,也是佛選擇的人間父母必須具有的性格,這種選擇標準正是因為佛心充滿了濟世情懷才會出現的。入胎時將以何種形貌出現的選擇標準也表達了這種思想。《普曜經·所現象品》中有言:
象形第一。六牙白象頭首微妙,威神巍巍,形象殊好,梵典所載其為然矣,緣是顯示三十二相。所以者何?世游三獸:一兔,二馬,三白象。兔之渡水趣自渡耳,馬雖差猛,尤不如水之深淺也,白象之渡盡其源底。聲聞緣覺其猶兔馬,雖度生死不達法本。菩薩大乘譬若白象,解暢三界十二緣起,了之本無,救護一切莫不蒙濟。
在這個情節當中,六牙白象作為佛陀降生時的坐騎出現,乃是因為佛界將其與佛陀的濟度世人的高潔品行結合起來,認為只有具備了濟世之心方才配得佛陀。從整個乘象入胎及之前的降神選擇標準來看,濟世渡人的濟世觀念始終貫穿其中。
逾城出家是在太子長大成人并經歷富貴生活以及對生老病死四種生命狀態有所體悟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此時的釋迦已經決定拋棄世俗榮華而進入佛國修道之途,以求證得無上正覺,普度眾生脫離現世之苦。《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二記載,太子棄家出城時已下定決心:
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終不還宮;若不得愛如墮落三藐三蓓提又復不能轉于法論,要不還宮與父王相見;若當不盡恩愛之情,終不還見摩訶波者波提及耶輸陀羅。當于太子說此誓時,虛空諸天贊言:“善哉,斯言必果!”
逾城出家明確表示,不修成正覺以解脫世人之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誓不還宮與親人相見,則仍是以濟世觀念為基調的。
二、降魔成道反映的濟世觀念
“降魔成道”是佛傳故事圖像中的一個重要情節,其內容是講,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即將得道成佛時,魔王波旬驚慌害怕,擔心釋迦牟尼成佛后,會給人間帶來幸福太平,他就會失去地盤和權威,因此帶領魔軍眷屬前來阻撓釋迦牟尼成佛。魔王先以美女誘惑,后以武力威脅,均遭失敗,最后釋迦牟尼戰勝魔王,魔王波旬伏地皈依。
由于這是釋迦牟尼由俗人成為佛陀的重要情節,佛陀也由此開始了修身濟世的歷程,而且內容具有戲劇性,所以是北朝佛傳故事圖像的重要題材。其中以云岡石窟第6窟、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4窟和北周第428窟的“降魔成道”佛傳故事圖像最具有代表性。
佛經記載,最先由心底泛起的魔障是代表欲念的三魔女對佛的引誘,這一情節在大多數石窟的佛傳故事藝術中都有表現。接著是恐懼、嗔恨、疑惑、執著等魔軍的襲擊,但佛堅持信念,始終以成就無上正覺以濟世解救眾生之苦為宗旨,通過堅韌的毅力克服魔障,修得無上正覺之境而成為得道之佛。
《修行經》卷下云:
于是菩薩,安坐入定,棄苦樂意,無憂喜想,心不依善,亦不附惡,正在其中,如人沐浴凈潔覆以白褻,中外俱凈,表里無垢,喘息自滅,寂然無變,成四禪行。以得定意,不舍大悲,智慧方便,究暢要妙,通三十七道品之行。……于是三女,嚴莊天服,從五百玉女,到菩薩所,彈琴歌頌,淫欲之辭欲亂道意。三女復言:“仁德至重,諸天所敬,應有供養,故天獻我。我等好潔,年在盛時,愿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菩薩答言:“汝宿有福,受得天身,不惟無常,而作妖媚,形體雖好,而心不端。譬如畫瓶中盛臭毒,將以自壞。有何等奇,福難久居,淫惡不善,自亡其本,福盡罪至,墮三惡道,受六畜形,欲脫致難。汝輩亂人道意,不計非常,經歷劫數,展轉五道。今汝曹等,未離勤苦。吾在世間,處處所生,觀視老者如母,中者如姊,小者如妹,諸姊等各各還宮,勿復作是曹事。”菩薩一言,便成老母,頭白齒落,眼冥脊傴,柱杖相扶而還……(菩薩)忍力降魔,鬼兵退散,定意如故。
整個降魔成道情節在多數石窟中的藝術形象上突出了佛的堅韌正覺之力,而代表著魔道力量的魔女等形象也制作得極為生動,對比明顯,突出了佛的濟世信念。
北朝時期,佛傳故事中的降魔成道圖像在各大石窟建筑中多有出現,且多以浮雕、壁畫的藝術形式展現,佛與群魔形象的鮮明對比給人震撼之力,使觀者在欣賞視覺藝術形象的同時,置身于一種強烈的同感原境當中,從而產生宗教情感上的共鳴。從另一方面看,用如此頻繁的藝術表現降魔成道故事,也正表明了當時人們對此濟世觀念的認可——佛對眾魔的降服也正是他將來要對苦難中的現世人們要做的工作。如云岡石窟第6窟主室西壁的降魔圖,構圖形式嚴謹合理,主佛作跏趺狀,施無畏印,帶有火焰型背光。周邊則滿布眾魔軍,在數量上明顯增多,形象更加怪異,豬馬牛、熊首等各種形象俱全,或拖山抱石,或持弓舞劍、捉蛇等,另有三魔女極盡魅惑之態。魔軍種種行為的喧囂躁動與主佛法相莊嚴的形象正好形成了強烈對比,以突出佛決心濟世所具有的堅韌正覺之力。
莫高窟北周第428窟北壁中層的降魔成道與北魏第254窟的構圖相同,只是魔兵眾妖沒有第254窟那么多,但構圖比第254窟更加對稱均衡。妖魔鬼怪的形象比第254窟更加猙獰可怕。莫高窟第254窟“降魔成道”圖繪在主室南壁中層,高 1.68米,寬 1.45 米,面積約 2.4平方米。畫面正中已成道的釋迦牟尼結跏趺坐于佛壇,背有火焰紋頭光和身光,左手執衣裙,右手作指地印,神態泰然,鎮定自若。左下側魔王波旬率三個女兒,以美色引誘釋迦牟尼。三個女兒,姿態相異,搔首弄姿,千嬌百媚,顧盼有情。企圖以女性的魅力,誘惑、動搖釋迦牟尼的意志。釋迦牟尼毫不動心,以其法力將左側的三個美女,變成了右側皺紋滿面,頭面干癟,白發覆頂的老丑嫫母,又由老丑嫫母變成白色骷髏。畫面上部,釋迦牟尼的兩側是魔軍眾妖,牛頭馬面,虎口羊角,象頭人身,奇形怪異,猙獰兇惡,殺氣騰騰,或張弓搭箭,或操戈持劍,或吐火放蛇,企圖用武力征服釋迦牟尼。佛壇下面,有伏地叩頭,長跪合掌的魔兵,表現魔兵戰敗,向釋迦牟尼伏首乞求,皈依佛門。畫面對稱均衡,動靜結合,故事情節傳神生動,以魔兵眾妖的兇惡丑態和驚慌失敗,來襯托釋迦牟尼的堅定鎮靜的濟世決心和勝利。
三、初轉法輪中的濟世觀念
佛徒稱成道后初次宣傳他的學說為初轉法輪。法輪出自一個傳說,誰能統治全印度,就會有“輪寶”出現,它能無堅不摧,無敵不克,得到“輪寶”的統治者便被稱為“轉輪圣王”。把佛的說法稱為“轉法輪”,即含有這種意義,同時也顯示釋迦所悟為最高原理。佛傳故事的初轉法輪情節表現的是,佛在成無上正覺之后來到鹿野苑的苦行林中,教化此前離棄他的五位比丘。該故事情節實際上體現了佛的寬宏心懷與有教無類的濟世觀念。
其時,五比丘由于不相信佛的成道信念而約定對其視而不見,但已成正覺的佛顯示出了無比莊嚴的法相,令五人恭敬之心油然而生,但他們的表現仍然差強人意,佛指出他已修成正覺,再直呼其名不合世俗禮儀規范,更何況在莊嚴的佛國世界。《過去現在因果經》記載:
爾時世尊語喬陳如等言:“汝等莫以小智輕量我道成與不成,何以故?”行在苦者,心則惱亂;身在樂者,情則樂著。是以苦樂,兩非道因。譬如鉆火,澆之以水,則必無有破暗之照。鉆智慧火,亦復如是。有苦了水,慧光不生。以不生故,不能滅于生死黑障。今者若能舍棄苦樂,行于道中,心則寂定,堪能修彼八正圣道,離于生老病死之患我已隨順中道之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陀觀察五人已具備修行佛法的根基,便悉心開示教導,為他們講解了《轉法輪經》和《無我經》之后,五人皆成就了圣人的最終理想,即阿羅漢,由此體現佛陀濟世救人的博大胸懷。
此故事情節在北朝佛傳故事圖像藝術中多有出現,如敦煌壁畫北魏的251窟、263窟,西魏的249窟、288窟、285窟,北周的428窟,克孜爾石窟的207窟,麥積山的127窟,云岡石窟第6、12、38窟,龍門石窟的古陽洞等窟均描繪了該故事情節。這其中以云岡石窟第6窟初轉法輪的說法圖最有代表性,對后世的說法佛像雕刻影響深遠。圖像位于洞窟東壁,窟龕內主佛褒衣博帶式袈裟,趺坐說法,舉右手,左手施說法印,左前雕刻象征三寶的法輪及鹿,龕外兩側雕刻五比丘及其他聽法弟子。
此情節在石窟中的多種藝術表現,五比丘皈依佛陀反映出文化的認同與融合,同樣給觀者帶來強烈的情感震撼與共鳴,激起人們聆聽學習圣法的心志,以藝術形象宣傳佛教的目的在于使人人信佛。“欲使人人信佛,僅憑講說佛經不夠,必須通過雕塑和繪畫佛像,才能‘美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觀者看到佛像,如走進了佛國世界,‘人佛相交,兩得相見’。無意中可訴之于觀者之高尚情緒,觀者會為那高尚的優美感所陶醉,在藝術美感的潛移默化中,心志升華,頂禮膜拜佛教”,從而皈依佛法以解救此世的無休苦難。
佛教思想中的濟世意義不止體現在北朝佛傳故事的藝術形象當中,而是在整個社會上都有顯著體現,這也是北朝時期佛教救濟事業得到明顯發展的思想動因。隨著佛教思想在北朝社會各階層間的廣泛傳播,人們對佛傳故事圖像藝術所表現出濟世觀念的目的和意義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表現,這從當時很多造像碑記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證明。
四、結語
綜上所述,佛教自東漢之際傳入我國,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同時也漸漸同中國傳統文化融合,逐步走上了中國化、民族化的道路,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北朝以后的中國傳統文化,已不再是純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釋融合的多元文化形態。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除了在北朝時期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時代契機之外,也有濟世思想文化本身的共同之處。佛教神靈世界的圖景,佛國神祗系統的結構和功能,都可以在還遠未成為社會和世界主人的眾生的心靈呼喚中,在永不停息的人生追求中,找到答案。通過對北朝時期的佛傳故事圖像藝術的搜集、考察,可以看到,佛傳故事圖像藝術表達的是佛教信徒的美好愿望,即對佛教中福報思想的體現,這也是人們對佛教濟世觀念的認可。佛教中的福田濟世觀念在漢譯佛教典籍中也有豐富的表現內容,如東漢時譯的《佛說作佛形象經》、梁代釋寶昌所編《經律異相》。
從上述記載來看,北朝佛教藝術行為預設的濟世對象涉及世俗生活中的各階層人群,在宗教文化識別傳播中運用人物、走獸、花鳥、器物等形象,通過借喻、比擬、雙關、象征及諧音等表現手法創造的美術形式,注入了寓福吉祥、驅邪避災之意,它符合人們共有的追求祥和、康泰、喜慶的審美理想和情感需求;以物寓意、物吉圖祥,主題突出,構思奇特,極具裝飾美感,集中表達了人們健康向上的進取精神和美好心愿,所以被廣泛應用于社會生活與喜慶場合之中。中國宗教文化識別具有傳統悠久的特性和濃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它是各種視覺藝術發展的推動力,佛教濟世觀念在佛教造像記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說明。
中國傳統文化面對佛教的傳播、發展表現出極強的包容性和同化力,體現了中華民族強大而鮮明的主體意識。中國文化經過長期“如琢如磨”的發展,已經逐步走向成熟。兩漢時雖“獨尊儒術”,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罷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內部也分化為不同的學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陳獨秀認為:“蓋文化之為物,每以立異復雜分化而興隆,以尚同單純統整而衰退,征之中外歷史,莫不同然。”當代宗教學家貝格爾說:“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動。”人將自己對世界秩序的愿望,對人生目標的追求,通過非世間的形式建立起來,反過來約束人世間的行為,為人的追求創造一個可以超越世間法的環境。佛教面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現出較強的適應性和調和性。由此可見,在佛教弘揚佛法過程中通過“即世而出世,入世而濟世”的精神,將佛教慈悲利他的濟世觀念,借助相應的佛傳故事圖像,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提供行之有效的幫助;并抓住濟世觀念這個根本理念,使佛教真正做到與社會大眾的文化融合認同,得到持久長足的發展,從而共同締造出美好的人間樂土。
[1]邵正坤.佛教信仰與北朝時期的社會救濟[J].許昌學院學報,2010,(6).
[2]劉鳳君,彭云.佛教與“像教”藝術[J].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4).
[3]普曜經(卷一).
[4]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二).
[5]修行經(卷下).
[6]劉鳳君.南北朝佛教的深入傳播與佛教雕塑藝術的發展[A].考古中的雕塑藝術[C].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
[7]葉小文.當前我國的宗教問題——關于宗教五性的再探討[J].世界宗教文化,2013,(3).
[8]趙鵬,江南.“制器尚象”對中國宗教文化識別傳播的影響及表現特征[J].山東社會科學,2012,(6).
[9]王榮才.選擇與重構: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內在機[J].江蘇社會科學,1997,(4).
[10]陳獨秀.陳獨秀文章選編[M].北京:三聯書店,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