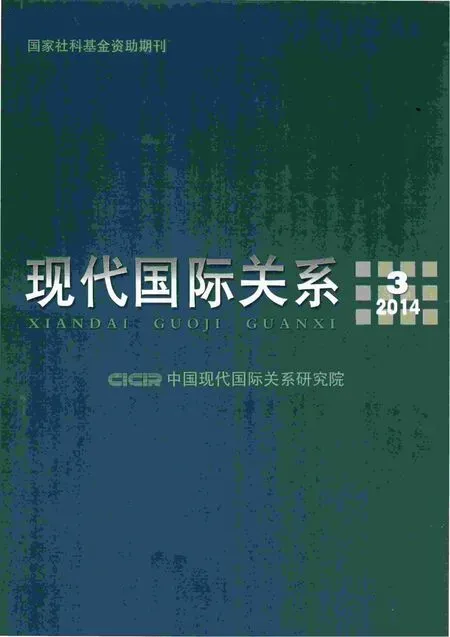比較視野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張 驥
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或類似機構①各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或類似機構的名稱不一,一般稱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或國家安全會議,為行文方便,本文統稱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當代世界各國進行國家安全決策和國家安全治理的主要制度形式和制度平臺,是各國國家安全制度中最核心的組成部分和最核心的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這種制度形式的產生和發展是當代主權國家在其所面臨的內外安全議題、安全威脅發生根本變化后,主權國家對國家政權管理國家安全事務的理念、制度、機構、手段等進行改革的制度結果,也是現代國家實現國家安全治理民主化、制度化、科學化、專業化的制度形式,民主、法治、統籌、專業是這一制度形式的價值體現。作為一種具體的制度形式,各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權功能、運作方式,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整個國家權力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無不與各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相適應,體現著一國的權力結構、基本制度安排和治國理念。
一、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產生
最早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制度形式的是美國(1947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建立主要源自兩方面因素的驅動。一是對內協調統籌軍事力量、情報部門、外交部門的需要。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經驗與教訓的反思使美國政府、軍方和國會認識到戰時決策和管理體制的混亂,特別是武裝力量內部、情報部門之間、軍隊與文官之間缺乏協調和統籌等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因而必須加強部門協作、推行總體戰略。②Zbgniew Brzezinski,“The NSC’s Midlife Crisis”,Foreign Policy,No.69,1987-1988,p.80.二是對外面臨的安全威脅變化和安全事務空前增多。美國國際地位的迅速提升和冷戰的到來,使得美國介入的國際事務空前增多,國家安全面臨不同于戰時的新威脅,貫徹稱霸世界、遏制蘇聯等戰略目標要求改革既有的國防和外交體制,從戰略高度全面協調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資源,建立適應新形勢的國家安全協調機制以及相應的決策、咨詢機制,提升戰略規劃能力。③周軍:“美國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原因初探”,《歷史教學問題》,1997年,第6期,第38-40頁。因此之故,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建立初期主要受內部協調統籌的需求驅動,其職能定位則主要是針對外部安全威脅。
從世界范圍來看,大多數國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在冷戰后建立起來的,或者是在冷戰后得到強化的。同時,大部分國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從國防委員會轉化而來,如英國、德國、韓國等,或者在保留國防委員會的同時,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為國家安全決策的主體,如法國等。當然,對于如今仍然面臨傳統軍事威脅的一些國家,則可能既設立國防委員會又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兩者在國家安全決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受安全形勢及文官與軍隊之間關系的影響,如巴基斯坦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與內閣國防委員會(Defence Committee of the Cabinet)一直隨軍政關系的演變而不斷輪替主導地位。①Hasan-Askari Rizvi,“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A Debate on Institutions and Processes for Decision-Making on Security Issues”,Pakistan Institute of Legislative Developmentand Transparency(PILDAT),http://www.pildat.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CMR/NaionalSecurity-Council-debateon Institutionsandprocessesfordecisionmakingonsecurityissu es.pdf.(上網時間:2013 年11月15日)
冷戰后,這些國家建立或強化國家安全委員會職能的原因來自兩方面。第一,主權國家面臨的國家安全威脅發生變化,國家安全事務從傳統的國防安全向綜合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拓展,國家安全從以領土安全為主向領土安全、政治安全、國土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國民安全等綜合安全及非傳統安全的拓展,這些是冷戰后各國紛紛建立或強化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重要原因。在冷戰末期1990年底建立的蘇聯安全會議和蘇聯解體后建立的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是應對這一轉變最顯著的體現。蘇聯安全會議的職能涵蓋了對外安全和對內安全,明確將經濟安全、環境安全、緊急狀態、自然災害、社會穩定、法律秩序等確定為安全會議的職權范圍。②“Об изменениях и дополненияхКонституции (Основного Закона)СССР в связи с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м систем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http://constitution.garant.ru/history/ussr-rsfsr/1977/zakony/185464/.(上網時間:2013年12月20日)1992年建立的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同樣體現了統籌內外安全的理念,涵蓋個人、社會、國家三個層級的安全,包括憲法安全、軍事安全、社會安全、國防工業安全、經濟安全、邊界安全、信息安全、國際安全、生態安全、衛生安全、軍事動員等領域。
應對國內安全問題是部分國家建立和改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重要驅動因素。例如,1986年雅克·希拉克總理主導建立的法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要是為應對國內外的恐怖主義活動和開展反恐領域的國際合作。③Bertrand Pauver,t“Creation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intérieur”,http://www.jac.cerdacc.uha.fr/internet/recherche/Jcerdacc.nsf/NomUnique/JLAE-5AUGJN.(上網時間:2013年12月30日)2002年希拉克連任總統后新建的法國國內安全委員會則主要是為了打擊嚴重暴力犯罪和國內治安問題。
為有效應對國內安全問題、打擊分裂勢力和極端犯罪活動、維護國家統一,一些國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還將特定地方的負責人納入國家安全委員會。如2000年普京總統首次將7名總統駐聯邦區全權代表列為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成員,這一制度一直延續下來。④上海太平洋國際戰略研究所:《俄羅斯國家安全決策機制》,時事出版社,2007年,第57頁。2004年巴基斯坦通過立法正式確定巴基斯坦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地位,旁遮普、俾路支、信德、開伯爾—普什圖四省省長成為巴基斯坦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正式成員。⑤“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A Comparative Study of Pakistan and Other Selected Countries”,p.16,http://www.pildat.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CMR/nationalsecuritycouncil-comparativestudy.pdf.(上網時間:2013年11月15日)
進入新世紀,特別是“9·11事件”之后,應對日益嚴峻的恐怖主義威脅成為部分國家建立或改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直接驅動因素。英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建立和新加坡安全政策評估委員會(Security Policy Review Committee)的建立就直接與應對恐怖主義威脅相關,并以應對恐怖主義威脅為主要任務。美國在“9·11事件”后立即建立了國土安全委員會和國土安全部,奧巴馬執政期間則將白宮國土安全辦公室并入國家安全委員會體系。⑥孫成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模式變遷及相關思考”,《現代國際關系》,2014年,第1期,第33頁。
冷戰后不少國家紛紛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第二個驅動因素是主權國家面臨的安全威脅多元化、復雜化和國家安全行為主體多元化帶來了國家安全治理的統籌協調壓力和專業化、職能化需求。
與單純的軍事威脅不同,當代主權國家面臨的國家安全威脅越來越復雜和多元。一方面,國家面臨的安全和外交議題的專業性不斷提高,不僅應對傳統軍事安全、政治安全的技術和專業要求大大提升,而且應對諸如經濟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和重大危機等新興非傳統安全威脅對專業技術和知識的要求更是空前提升。另一方面,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以及各個安全議題之間相互交織,已經無法通過單一手段和單獨的部門來應對,國家安全治理的系統性、復雜性因而空前提升。盡管各國普遍將處理國家安全事務的權力賦予最高行政當局或者最高行政首腦,但單純依靠領導人個人或者領導集體已經無法有效應對國家安全決策和國家安全治理所面臨的這些復雜挑戰,迫切需要專業意見的支持、多部門的協商、多種手段的配合,以及專業人員對日常事務的處理。這些是催生國家安全委員會機構的內在驅動力。
與此同時,國家安全威脅多樣性、復雜化帶來了國家安全行為主體的多元化,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參與到國家安全治理和國家安全決策的進程中。對于大多數國家而言,國家安全決策至少涉及軍方、國防部、外交部、內政部、安全部門、經濟部門、情報部門等,多部門參與在為國家安全治理帶來多種手段和綜合應對的同時,也產生了部門利益化、信息情報溝通不暢、分割嚴重、協調不力,甚至相互傾軋等問題,亟需在各個具體部門之上建立一個權威的溝通協商、統籌協調、統一步調的制度化機制,以減少決策和執行的內部阻力和成本。1947年美國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目的就是:對武裝力量、情報系統與外交部門進行全面重組和整合,以解決文官和軍方及各軍種之間的政策協調、各個情報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情報部門對戰場行動的有效支持等一系列問題。①周琪主編:《美國外交決策過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135頁。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則通過建立一系列常設或臨時的跨部門委員會來協調涉及多個部門的安全議題。
當代國家安全治理中的兩項主要任務——危機管理和戰略規劃也對建立在專業基礎上的統籌協調提出了要求。當代國家安全治理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突發事件和危機進行有效管理,包括突發外交事件、恐怖主義襲擊、嚴重暴力事件、自然災害、公共衛生事件、環境事故、核事故等。這些危機要求決策者做出及時、專業和科學的判斷,并進行有效和協同的應對,這就需要為決策提供一個專業、高效,有充分整合情報支撐和各部門會商、響應的機制,國家安全委員會為國家的危機管理提供了制度平臺。韓國國家安全保障體系就呈現出顯著的危機主導特征,韓國的國家外交安保體制和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功能和結構一直處于不斷的調整變化之中,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動因就是應對持續演變的半島危機和突發事件。
當代國家安全治理的復雜性和系統性要求國家進行有效的國家安全戰略規劃。一國如要保障國家的長治久安,除了應對日常的安全議題和進行有效的危機管理外,還必須超越日常事務和官僚機構的部門分化,對國家安全戰略進行宏觀設計和規劃。對核心國家利益和安全威脅的界定、政策和手段的制定與計劃都需要超越國會、內閣和政黨的紛爭,擺脫行政機構和官僚體系的束縛,在綜合平衡的基礎上進行前瞻性、系統性構建。這就需要有一個專門的機制為最高決策層提供專業性、獨立性的意見,提供大戰略的思想資源和政策方案,協助最高決策者進行戰略判斷和戰略謀劃,國家安全委員會同樣能夠為此提供一個制度平臺。美國自1986年的《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改組法》要求總統每年向國會提交《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成為撰寫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主要平臺。此一做法為各國紛紛效仿,成為各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項主要職能。蘇聯解體前,俄羅斯聯邦就已經開始醞釀《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安全系統構想》②王曉東:《國家安全領導體制研究》,時事出版社,2009年,第58頁。;之后葉利欽和普京分別通過頒布《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構想》來構建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戰略;2009年梅德韋杰夫總統頒布了《2020年前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戰略》。其他一些國家則是首先制定國家安全戰略,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直接產物而誕生,比如法國的國防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是2008年法國《國防與國家安全白皮書》的主要機制成果③Livre Blanc sur Défense et Sécuriténationale,Paris:Odile Jacob/La Documentation Fran?aise,2008,p.251.,英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則是2008年英國首份《英國國家安全戰略》和2010年英國《不穩定時代的強大英國:國家安全戰略》催生的結果。①“The Governance of Britain”,p.33,http://www.official-documents.gov.uk/document/cm71/7170/7170.pdf;“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a Strong Britain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pp.34-35,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1936/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上網時間:2013 年 11月29日)
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制度基礎
民主、法治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制度基礎。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制度形式的產生和發展是現代國家安全決策和國家安全治理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體現。民主化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基于各國基本政治制度的民主原則和憲法法律的規定;第二,國家安全委員會受到議會的監督和制約,有些國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要經過議會批準;第三,國家安全委員會為個人決策向集體決策轉變提供了制度平臺,通過集體決策或集體咨詢作出事關國家核心利益的重大決定。盡管在總統制、半總統制國家,法定最終決策權在總統,但總統決策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協商討論的基礎上作出的。法治化也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權力來源于憲法和法律的規定;第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策、運作和執行受到法律的規范和制約;第三,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內部運作有相應的法律和規則進行規范。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和運作基于民主和法治的總的原則,但國家安全事務涉及國防、外交、安全等國家的核心權力,依法高度集中于最高元首、行政首腦或者最高行政當局,具體運作則要求統一、集中、高效和保密。從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上來說,存在著民主與集中、法治與權威之間的張力,如何做到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法治基礎上的集中、專業基礎上的集中,考驗著各國的制度安排和政治領導的政治智慧。作為一種具體的制度形式,各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具體制度安排無不與各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相適應,體現著各國國家權力結構、基本制度安排和治國理念。本文擬通過法律基礎和政治地位這兩個具體要素來比較各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民主、法治基礎。
各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一般都具有堅實的法律基礎。在最核心的憲法層次,國家安全委員會通常根據憲法賦予最高領導或領導機構的軍事、外交、國家安全等的權力建立。俄羅斯、韓國、伊朗都在憲法中明文規定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憲法性機構性質及其職權,并規定國家安全委員會由國家最高領導組織和領導。②俄羅斯現行憲法《俄羅斯聯邦憲法》第83條第7款規定,“俄羅斯聯邦總統組織并領導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constitution.ru/(上網時間:2014年1月2日)。韓國現行憲法《大韓民國憲法》(第六共和國憲法)第91條規定:“為制定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對外政策、軍事政策和國內政策,在國務會議審議前,備總統咨詢,設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由總統主持。”《大韓民國憲法》,姜士林主編:《世界憲法全書》,青島出版社,1997年,第257頁。伊朗現行憲法《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1989年憲法)第176條規定:“為捍衛國家利益和維護伊斯蘭革命、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設立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總統任主席”。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Tehran:Islamic Propagation Organization,1990.一些國家的憲法中雖沒有有關“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明文規定,但其權源來自憲法賦予國家元首(總統制、半總統制國家)或內閣(議會內閣制)的相應權力,并對國家元首或內閣負責,通過專門法或行政命令建立。
在專門法的層次,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通過國家安全立法規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法律地位、職權和活動原則等,建立了一系列相關法律制度。③李竹:《國家安全立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頁。例如美國的《國家安全法》、俄羅斯的《俄羅斯聯邦安全法》、新加坡的《國家內部安全法令》等;其他相關的部門法還有《國防法》、《國土安全法》、《反恐法》、《情報法》、《緊急狀態法》,等等。《政府組織法》、《公務員法》等則涉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組織機構。
部分國家(特別是議會內閣制國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往往通過行政命令(如德國、印度、以色列、新加坡等)或政府政策文件(白皮書、國家安全戰略)宣告建立(如英國、法國等)。
一些國家還通過專門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立法或者行政條例來規范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內部運作,例如俄羅斯的《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條例》、日本的《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韓國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法》、巴基斯坦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法案(2004)》、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法》,等等。美國總統上任后則通過總統行政命令確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組成和機構設置。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的內部法治建設最為健全,其下設的7個常設跨部門委員會、科學委員會和聯邦安全會議機關都分別制定了相應條例。
政治地位指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國家政治結構和權力結構中的位置、與其他國家機構間的關系,主要涉及國家安全委員會權力的大小,對其的監督和制約,這與各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密切相關。
就其法律地位而言,各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有決策型、協調型、咨詢型之分,協調型和咨詢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沒有決策權,但在實際的政治和決策過程中,國家安全委員會往往成為國家安全決策的最高機構。
在總統制、半總統制的國家中(如美國、俄羅斯、法國等),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法律地位一般是服務于總統的咨詢機構和協調機構,不是政府的組成部分。在這類國家,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總統的直屬機構,對總統負責,一般由總統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雖然總統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擁有最后決策權,且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定或建議必須經總統批準,由總統發布和施行,但國家安全委員會囊括了最重要的政治領導和政府部長,決策往往就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形成,并逐漸發展成一個集協商、咨詢和協調、監督執行于一體的實權機構,甚至部分行使執行權力,成為實際上的最高決策機構。
在議會內閣制國家中,國家安全委員會大致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進行部際協調的內閣委員會(如英國、德國、新加坡等);另一種是隸屬于總理的咨詢、協調機構(如以色列等)。議會內閣制國家的決策權屬于內閣全體會議,但在實際政治過程中,決策程序往往被轉移到具體的內閣委員會當中,①[德]沃爾夫岡·魯茨歐著,熊煒、王健譯:《德國政府與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10頁。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為安全決策的主要平臺。近年來,一些議會內閣制國家還在效仿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將國家安全委員會從內閣委員會轉變為總理(首相)直屬機構,如英國和日本等。②朱建新、王曉東著:《各國國家安全機構比較研究》,時事出版社,2009年,第35頁。這一趨勢在英國受到質疑,但在日本,安倍政府通過建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和國家安全保障局,將決策重心從內閣轉向首相官邸,使之成為實際上直屬首相的最高決策機構。
可以看出,無論在總統制、半總統制國家,還是在議會內閣制國家,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各國國防、外交和安全決策中的政治地位有上升的趨勢,這就使得對國家安全委員會進行監督和制約的問題更加突出。
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行政機構的一部分,通常會受到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的監督。議會對國家安全領導機構的監督負有最高的法定義務、權力和責任。③王曉東:《國家安全領導體制研究》,時事出版社,2009年,第200頁。議會通過以下方式對國家安全委員會進行監督和制約:第一,通過立法確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權力、職責,規范其行為和活動,或者通過立法直接影響具體的政策;第二,通過議會享有的權力制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策和行為,如彈劾權(總統制)、倒閣權(議會內閣制)、質詢權(議會內閣制)、違憲審查權、調查權、戰爭權(宣戰或對外軍事行動)、外交監督權(條約批準權)、緊急狀態和動員批準權等;第三,通過任命權、預算審批權控制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組成和運行;第四,通過議會專門委員會直接監督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如美國參眾兩院中的有關軍事、外交、國土安全和情報的專門委員會,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和國家杜馬中有關國防、安全、國際事務的專門委員會,英國國會的情報和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戰略聯合委員會等;第五,通過議會負責人或成員進入國家安全委員會直接監督,如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主席、國家杜馬主席是聯邦安全會議的法定常委,巴基斯坦參議院議長、國民議會議長一度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伊朗伊斯蘭會議議長是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Suprem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法定成員;第六,通過向議會提交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白皮書及實施情況報告接受議會監督。
在一些國家,司法機關的負責人也直接參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并作為成員或者顧問對國家安全委員會進行監督,如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長是俄聯邦安全會議成員;伊朗司法總監是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
英、德等國則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組成上注意平衡執政黨與在野黨,以及執政聯盟內部政黨之間的關系,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形成政黨之間的相互制衡。在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與國務卿之間存在競爭關系,也形成一定的相互制約。
三、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制度設計
民主、法治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制度基礎,是其政治性的體現。其制度設計則追求統籌和專業,體現出功能性。當代主權國家所面臨安全威脅的多樣化、復雜化、系統性和國家安全行為主體的多元化,要求國家安全決策和治理體系的制度設計必須體現專業基礎上的統籌這一理念:統籌對外安全與對內安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統籌內政、外交、國防、安全、情報、經濟等國家安全主體部門;統籌中央(聯邦)與地方;統籌協調政策、情報、資源、手段和執行;統籌戰略規劃、危機管理與日常運作。專業方面,要求國家安全決策建立在充分的情報、科技手段和專業意見的基礎上,經過專業的研究、論證、咨詢和協商,作出科學、理性的決策。
各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功能設定、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具體運作都體現統籌性和專業性的要求。第一,統籌性和專業性首先體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核心功能上。盡管各國在制度設計上賦予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能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圍繞決策、咨詢、協調這三大核心功能展開。一是決策功能。如上文所述,盡管大部分國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法律上不是決策機構,其決策權屬于最高領導人或內閣,但在實際政治過程中,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國家安全決策中起核心作用,成為實際上的最高決策機構。當然,也有些國家賦予國家安全委員會最高安全決策機構的法定地位,如伊朗等。二是咨詢功能。決策咨詢是大部分國家賦予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法定地位和職能,是專業性最重要的體現。咨詢功能體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進行情報和信息整合、聽取和整合各方意見、進行戰略評估和謀劃、政策研究和設計、形成意見和方案,為最終決策提供專業意見,扮演參謀和顧問角色。三是協調功能,主要在政策和執行兩個層面,協調涉及國家安全的政府部門、軍事部門,協調中央(聯邦)與地方,以及在一些國家協調行政機構與立法機構、司法機構(如俄羅斯、伊朗等),是統籌性的體現。國家安全委員會通常設立跨部門的內設委員會或小組進行政策協調和準備。此外,一些國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還發揮一定的代表和執行功能。國家安全顧問或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家安全會議秘書以總統私人代表或政府官方代表等身份進行外交活動和談判,扮演特使角色;或扮演總統/政府發言人,對外發布和闡釋國家安全政策。美國、俄羅斯、印度、伊朗、以色列等國的國家安全顧問都發揮上述功能。國家安全委員會代表政府與其他國家相應機構進行戰略對話,如以色列。國家安全委員會還負責監督執行國家安全委員會或總統、內閣作出的決定。
第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體現統籌性和專業性的要求。機構設置上,總體上有會議型和實體型之分。會議型通常通過召開會議的形式進行協調、咨詢和決策,一般不設專門的下級機構,僅有少量的秘書人員,決策由委員會成員所代表的組成部門具體負責執行,也可能借助總統或總理的辦公機構負責秘書和執行工作。德國聯邦安全委員會是典型的會議型模式,作為內閣委員會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形成決定后由具體的內閣部門去執行。實體型除了設有會議機制外,還有一個相對系統完備的秘書、工作機構和顧問班底,有完備的人員配置和組織體系。隨著國家安全事務的大量增加和專業化程度的不斷提升,大部分國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采用實體型模式,且組織體系不斷擴大,專業化與職能化程度不斷提升,甚至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科層機構。一些國家的會議型模式也在向實體型轉變。這一趨勢反映了當代國家面臨的國家安全決策和治理的任務越來越重大,原有的制度安排已經不能有效統籌決策和執行、不能有效處理日常事務,因而需要進行機構上的變革,以適應安全環境的變化。
實體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通常由委員會核心成員(常委)、全體委員、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秘書)、秘書/工作機構、咨詢機構構成。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任委員會主席,核心成員包括:副總統、半總統制國家的總理、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安全部長(內政部長)、財政部長、總參謀長、情報部門負責人、國家安全顧問、總統/總理辦公廳主任等。核心成員或者常委往往由國家實權部門的領導人構成,以利于進行重大決策、危機管理和保密,并能夠有效地進行最高層級的統籌。其他成員包括根據議題邀請的其他行政和軍事官員,有的國家還包括立法機構負責人、司法機構負責人、相關的地方負責人等,以確保決策的專業性和增強決策的政治基礎。
國家安全顧問(有的國家設置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等)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度設計中的一個關鍵,扮演安全大腦和協調人的角色,是國家安全決策和治理專業化、職能化的體現。國家安全顧問負責領導和組織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日常工作,是國家安全委員會日常運作的核心,在國家安全決策和國家安全治理中發揮中樞作用。在一些國家,該職位不具有法定地位,但因其對決策的重大影響而成為權傾朝野、影響國際時局的風云人物。在另一些國家,國家安全顧問由總理府主任(如德國)或總理首席秘書(如印度)兼任,具有更加突出的政治地位。在實際政治過程中,國家安全顧問作用的發揮受到三個因素的影響:首腦的信任與重視程度、國家安全顧問本人的能力和資歷、其他部門或核心官僚的競爭。①Ivo H.Daalder and I.M.Destler,“How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s See Their Role”,in Eugene R.Wittkopf and James M.McCormick,eds.,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5th edition,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7,pp.185-186.
國家安全顧問的職能主要體現在五大方面。一是參與日常決策和危機決策并提供專業咨詢,每天或定期將相關情報和信息經過匯總整理后提供給首腦,如實反映各方意見并提供獨立意見和可選方案;二是協助首腦或內閣進行宏觀戰略規劃與政策設計,制定國家安全戰略,提供思想和理念,領導預測研究;三是領導國家安全委員會日常工作,負責首腦或內閣的國家安全事務議程設置,組織各級別會議,起草各類文件;四是國家安全政策及政策執行的協調與督促;五是代表首腦進行外交活動、談判和發布信息。
日常秘書和工作機構的設置是為了確保國家安全委員會有充分的決策準備,決策能夠得到有效的執行,國家安全事務能夠得到持續和有效的處理。它由國家安全顧問領導,按職能劃分為若干下設委員會或工作機構。如美國奧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縱向形成部長級委員會、副部長級委員會、跨部門協調委員會的結構,橫向跨部門協調委員會由6個地區委員會和若干個議題委員會構成。②Alan G. Whittaker et al., The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rocess: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Interagency System,Washington,D.C.:Industrial College of the Armed Force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2011,pp.15-19,69.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下設戰略規劃、獨聯體事務、經濟和社會安全、環境安全、軍事安全、公共安全、信息安全等7個常設跨部門協調委員會負責跨部門協調,還設有聯邦安全會議機關處理日常工作。③Совет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scrf.gov.ru/.(上網時間:2014 年1 月15 日)法國設置國防與國家安全總秘書處作為國防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機構,下設5大部門,有216名工作人員。④Secrétariat général de la défense et de la sécuriténationale,http://www.sgdsn.gouv.fr.(上網時間:2013 年12 月30 日)日本設置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事務局國家安全保障局,下設總括、戰略、信息三個職能部門和同盟·友好國、中國·朝鮮、其他地區3個地區部門,初始編制67人。⑤“國家安全保障局が67人體制で発足首相「戦略的に領土守る」”,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news/140107/plc1401072 2160026-n1.htm.(上網時間:2014年1月7日);地曳航也:“走進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7834-20140127.html.(上網時間:2014 年1月28 日)可見,各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日常秘書和工作機構已趨于日漸完備和科層化。
為了增強決策的科學性,一些國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專門的咨詢機構,由國家安全顧問領導,成員包括各個領域的資深專家、相關政府部門的高級官員或退休的高級外交官和退役的高級將領,負責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獨立的專業意見、評估和科技支撐。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下設科學委員會,包括155名成員,主要有科學院系統、國家機關和軍隊所屬研究機構的領導和著名學者。⑥“Состав научного совета при Совет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scrf.gov.ru/persons/sections/17/.(上網時間:2013年12月19日)新加坡高度重視政策研究和科技開發對國家安全的支撐作用,安全政策評估委員會下設的國家安全協調中心(National Security Coordination Centre)通過國家安全工程中心(National Security Engineering Centre)、國家安全卓越研究中心(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National Security)和相關評估研究項目為國家安全提供強大的科技支撐;①National Security Coordinating Secretariat NSCS,http://app.nscs.gov.sg/public/content.aspx?sid=28.(上網時間:2014 年 1 月15日)另一下設機構國家安全研究中心(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Centre)則通過整合全國科研機構提供遠景預判、風險評估和政策研究。②National Security Coordinating Secretariat NSCS,http://app.nscs.gov.sg/public/content.aspx?sid=137.(上網時間:2014 年 1 月15日)法國設有國防與國家安全咨詢委員會;印度設有國家安全咨詢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以色列國家安全委員會則專門設立了經濟顧問和法律顧問。
第三,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運作日趨規范和專業。根據各國經驗,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運作一般有日常運作模式、危機管理模式和戰略決策模式,要求統一、集中、高效和保密。各國通過國家安全立法、專門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立法以及行政條例對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內部運行,特別是議事規則、決策程序、工作程序等作出嚴格規范,確保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策和行政系統根據日常、危機、戰略的不同規則和程序作出響應,并通過保密立法確保決策的機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運作受到法律、行政條例的約束,也深受一國政治傳統、行政文化和領導人風格的影響。在實際政治過程中,各國都存在正式機制與非正式機制,并且兩者同時發揮作用。尤其是在作為首腦直屬機構的國家,核心決策層的非正式磋商以及國家安全顧問作為首腦私人顧問和代表的角色較為常見。這也帶來缺乏監督和制約等問題,為立法機構和輿論所詬病。總的看來,各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實踐中形成了不同的運作模式,總體上趨于建立一整套規范、專業的決策和工作程序及其規則,如美國從老布什政府開始一直延續至今的“斯考克羅夫特”模式③老布什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總結了里根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弗蘭克·卡盧奇(Frank Carlucci)的機構設置經驗,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設置了一個金字塔型運作模式:在底層設置一系列跨部門協調委員會,每個委員會針對一個特定議題或特定地區,提交相關報告,監督、協調與執行相關的日常政策。在其更上一級設置副部長級委員會,審核跨部門協調委員會的報告,提出建議和方案,也處理有關重要政策的協調與執行。在其上一級設置高級別的部長級委員會,審議副部長級委員會的報告,做出決定,提交總統。最終,在金字塔的頂端,總統基于部長級委員會的建議,與國家安全委員會核心成員進行正式或非正式討論,最終做出決策。參見周琪主編:《美國外交決策過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89-90頁;John P.Burke,Honest Broker: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and Presidential Decision Making,TX:A&M University Press,2009,p.169.等。
結論
縱觀世界各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其建立和發展是當代主權國家應對國家安全議題、安全威脅變化的制度反應和制度創新。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機構,而是國家政權進行國家安全決策和國家安全治理的制度形式,體現了當代國家安全治理和決策對民主和法治的制度要求,以及對統籌和專業的功能需求。隨著國家面臨的安全事務空前增長,安全威脅多元化、以及安全威脅內外交織和相互交織的系統性發展,國家安全委員會職能化、專業化程度不斷提升,越來越朝著實體型方向發展,其功能和結構日益龐大,其運作更加日常化和科層化,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政治地位也不斷提升,日益成為一個具有實際權力的最高安全決策機構。這一制度形式有利于主權國家統籌應對內外安全威脅、協調國家安全行為主體、進行科學理性的安全決策和戰略謀劃、綜合運籌政策和資源,從而更好地保障國家安全、捍衛國家核心利益。但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置也帶來了民主與集中、法治與權威之間的張力,對國家安全決策和國家安全治理的法治建設、民主監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世界各國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即如何通過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制度形式能夠真正實現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法治基礎上的集中、專業基礎上的集中,并與各國的基本政治制度、行政文化和實際安全需求相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