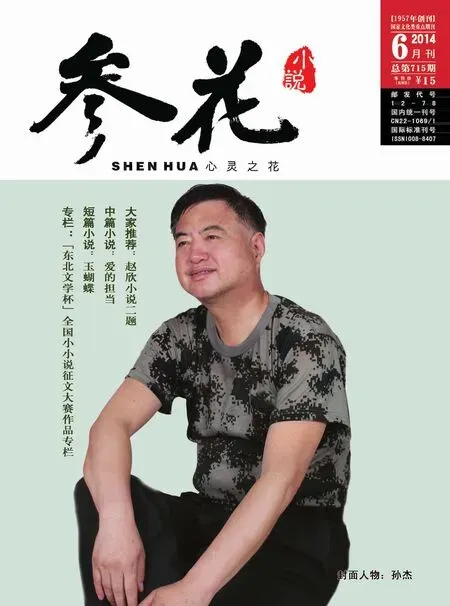“婆娑世界,起于極微”
——試論金圣嘆的戲曲人物塑造細節觀
◎汪雨晴
“婆娑世界,起于極微”
——試論金圣嘆的戲曲人物塑造細節觀
◎汪雨晴
在《第六才子書西廂記》中,金圣嘆借鑒了佛典“極微”的概念,將其應用于人物塑造上,強調細節描寫對戲曲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同時指出,變動的細節對于展示人物性格多樣性和豐富性具有重要意義。
金圣嘆 人物塑造 細節 極微論
《第六才子書西廂記》(下文簡稱《第六才子書》)是明末清初文學批評家金圣嘆的批評作品,蘊含著他對戲曲作品的深刻理解。金圣嘆尤為重視戲曲人物塑造,認為人物的細節塑造是戲曲作品的重中之重。細節在文學作品中有著重要的地位,詳盡、生動、恰到好處的細節描寫能增加作品生命力、提高人物形象的豐滿程度。下文,筆者將對金圣嘆的戲曲人物塑造細節觀進行分析。
一、極微論
《酬韻》總評中,金圣嘆論述了他從佛經中借鑒而來的 “極微論”:
“夫婆娑世界,大至無量由延,而其故乃起于極微。以至婆娑世界中間之一切所有,其故無不一一起于極微。今者止借菩薩極微一言,以觀行文之人之心。”[本文所引《西廂記》原文及金圣嘆評語,均選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金圣嘆評點西廂記》。]
佛教認為,極微是構成事物的最小單位。金圣嘆借用極微論以闡釋他對文學寫作的看法。他認為,一切事物無論大小都是由細節組成的。細節是作品的基礎,也是作品得以成功的保證。周曉癡先生認為,金圣嘆“對極微論的理解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認為大千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均由最小的物質微粒構成,其內部結構均精細無比,這精細無比就是極微,就是萬事萬物顯示彼此差別與內部層次的開始。二是認為即使是人們覺得轉瞬即開的花朵,也經歷了孕育子房、萼片的‘累生積劫’的生命歷程,在這種不易覺察的微妙演進中同樣包含著極微。作家若能抓住并表現這兩種極微, 就能用極平凡的素材寫出好文章。”[周曉癡.金圣嘆戲曲批評芻議[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1期.]實為篤論。
金圣嘆在《酬韻》總評中列舉若干生活細節,以為“至妙”之事,如“清秋傍晚,天澄地徹,輕云鱗鱗,其細若轂”;又如野鴨“成群空飛,漁者羅而致之,觀其腹毛,作淺墨色,鱗鱗然猶如天云,其細若轂”等,以說明細節的重要性。他對于世人只知豎高橫闊,以衣食豐盈為貴,不懂欣賞細節之美的現象不以為然。
金圣嘆認為,輕云鱗鱗,遠看“鱗鱗者”相差不到一寸,實際去丈量才知鱗與鱗之間相差何止一丈,且中間有許多曲折妙處。看野鴨腹毛,鱗鱗之間,相距沒有粟米大小,但也是曲折不斷,妙處橫生。在金圣嘆看來,事物宏大如天上的云,中間也蘊含了無數細節;事物細小如野鴨腹毛,在其細微處仍能體會到細節的妙處。
金圣嘆借用“極微”來表達其對細節的關注。因為細節不僅是作品的一部分,且對于鋪開作品情節,充實作品內容,豐富人物形象均有重要作用。就如金圣嘆在《請宴》一折中所言:“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
二、《第六才子書》戲曲人物塑造細節論
《賴婚》一折中,鶯鶯出場唱【五供養】一曲道:
“若不是張謝元識人多,別一個怎退干戈?”
金圣嘆評道:
“一篇文初落筆,便先抬出‘張謝元’三字,表得此人已是雙文芳心系定,香口噙定……圣嘆每言作文最爭落筆,若落筆落得著,便通篇爭氣力;如落筆落不著,便通篇減神彩。”
金圣嘆從鶯鶯改口叫張生“張謝元”這個細節分析得出,鶯鶯在寺警之后已對張生產生了愛慕和敬仰之情。金圣嘆對這個細節評價甚高,認為它為“通篇爭氣力”,通過稱呼改變就把鶯鶯對張生情感的變化傳達了出來。金圣嘆認為,刻畫人物不需長篇累牘,只要抓住最能展現人物的細節,就能出神入化,人物語言不在多,而在精妙。筆者深有同感,金圣嘆顯然已經抓住了人物描寫的重點,即語言的細節描寫。塑造人物,可以通過語言、動作、神態、心理等多方描寫來凸顯人物性格。但是,就《西廂記》而言,語言描寫是重中之重。《西廂記》不僅是一部敘事文學作品,同時也是一部劇本,需在舞臺上演出。因此,對人物唱詞的揣摩尤為重要。金圣嘆立足于《西廂記》的戲曲本色,他總是敏感地抓住能夠表現人物心理變化的動作和語言細節,通過批點向讀者點明這些小小的關隘,為人們更好地理解《西廂記》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又如,《哭宴》一折中,張生上京趕考,鶯鶯長亭送別。她唱道:
“馬兒慢慢行,車兒快快隨”。
圣嘆批道:
“二句十字,真正妙文!直從雙文當時又稚小、又憨癡、又苦惱、又聰明一片微細心地中描畫出來。蓋昨日拷問之后,一夜隔絕不通,今日反借餞別,圖得相守一刻。若又馬兒快快行,車兒慢慢隨,則是中間仍自隔絕,不得多作相守也。即馬兒慢慢行,車兒慢慢隨,或馬兒快快行,車兒快快隨,亦不成其為相守也。必也馬兒則慢慢行,車兒則快快隨,車兒即快快隨,馬兒仍慢慢行,于是車在馬右,馬在車左,男左女右,比肩并坐,疏林掛日,更不復夜,千秋萬歲,永在長亭。此真小兒女又稚小、又苦惱、又聰明、又憨癡一片的微細心地。”
此批中圣嘆重申了細節的重要性,他認為寫作無需多言,只要能抓住細節,若干字也是妙文。他指出,這句唱詞將鶯鶯個性中的稚嫩、憨癡、聰明,面對與張生分別的苦惱情緒等一齊表達了出來。從“馬兒慢慢行,車兒快快隨”這句話中,透露了鶯鶯在母親答應婚事卻馬上送張生上京趕考情形下,那種渴望與張生長相廝守,不忍分別,卻又必須分別的微妙心理感受。
《西廂記》作為一部戲曲作品,人物的情緒和情節的推動主要依靠人物科介和唱白來表現,心理描寫難以在舞臺中直接表達出來,需要借助于二者。金圣嘆敏銳地從鶯鶯的唱詞中抓住鶯鶯微妙的情感變化,從中歸納出一個憨癡的女子形象。在以舞臺表現為主的戲曲文學作品中,心理描寫對于人物的刻畫同樣非常重要。精準、細致、豐富的唱詞和動作,是表現人物心理狀態,豐富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法。《第六才子書》的廣泛傳播以及鶯鶯、張生、紅娘形象的深入人心,與作品細膩的細節刻畫是分不開的。
三、變動的細節觀
金圣嘆的細節觀是變動的細節觀。《酬韻》總評中,他舉了兩個例子:
“于無跗無萼無花之中,而欻然有跗,而欻然有萼,而欻然有花,此有極微于其中間,如人徐行,漸漸至遠。”
“必有極微于其中間,分焉而得分,又徐徐分焉而使人不得分,此又一不可以不察也。”
在金圣嘆看來,極微并非靜止,它像花開一樣,雖細微,但也會變化,像火焰的顏色,雖連續,但也有不同。連續變動細節觀的提出,可謂金圣嘆的創新。古往今來重視細節寫作的作家和評論家不在少數,但唯有金圣嘆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了連續變動的概念,將靜止的觀點引向流動。
如:《賴婚》一折,老夫人在張生智謀退兵后宴請張生,請鶯鶯作陪。席間,老夫人欲賴婚約。在這個情節發展中,細節的變化對塑造人物形象起了極大的作用。鶯鶯面對母親賴婚的噩耗做出的各種細節反應,充分展現了鶯鶯的性格特點。
在開席前二人偶然撞見,鶯鶯“目轉秋波”,被“唬得倒躲,倒躲”。金圣嘆批道:
“分明一對新人,兩雙俊眼,千般傳遞,萬種羞慚,一齊紙上活靈生現也”。
金圣嘆把握住二人自老夫人許婚后初見的緊張、害羞與驚喜,點出二人在微妙環境下微妙的情感流轉。當老夫人賴婚道“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澆滅二人喜悅時,鶯鶯先看張生,“只見他荊棘刺怎動那!”接下來方才埋怨母親,訴說內心的傷痛。金圣嘆又抓住這個細節,批曰:
“先看謝元,妙妙!”
金圣嘆分析,鶯鶯之所以“先看謝元”,是因為老夫人在寺警后已將鶯鶯許配給張生,鶯鶯已將張生視為夫婿,一心系于他身上。因此,待老夫人賴婚之語一出,鶯鶯便條件反射先看張生,而后才是埋怨。金圣嘆僅以一個“看”的細節,便能分析出鶯鶯情感的變動。此一細節與二者開宴之前撞見的細節相連,更能表現鶯鶯內心對張生的愛慕,在潛意識里將自己與張生命運相連的情感。鶯鶯的這種情感變化,僅以一個細節難以完整地進行說明,需要多個細節的連續和突出,方能給讀者以深刻印象。金圣嘆敏銳地抓住兩個細節內在的情感聯系,對主人公內心世界的變化,情感的發展進行了詳盡而又通達的批評,對揭示在“寺警”之后“賴婚”之時女主人公的情感變化,幫助讀者把握人物形象上有很好的作用。
結語
圣嘆借鑒佛教極微論所提出的細節觀,在其人物塑造理論上,表現為對人物塑造細節的重視,他提出的變動聯系的細節對人物情感流動的揭示作用,對于敘事文學的人物塑造,具有鮮明的指導意義。他對細節的重視,貫穿整個《第六才子書》,使得人物形象更為豐滿,人物性格更為突出,人物情感更為細膩。《第六才子書》的廣泛傳播,與其中塑造的令人記憶深刻的人物有很大關系。這也是在后世幾百年的傳播中,《第六才子書》能成為流傳最廣版本的原因之一。
[1]金圣嘆.金圣嘆評點西廂記[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周曉癡.金圣嘆戲曲批評芻議[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1期.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 劉冬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