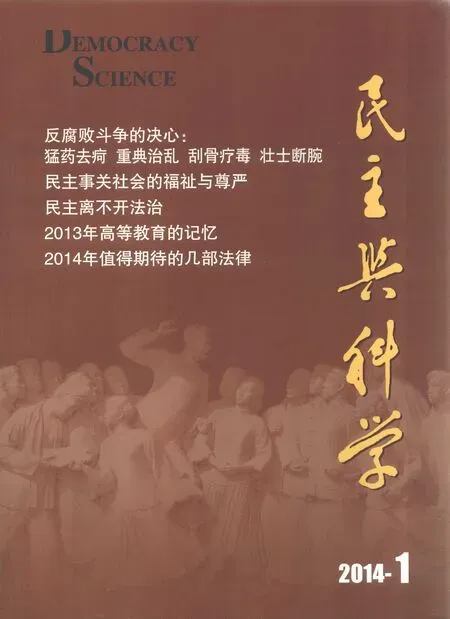科學界的“流星”
■丁福虎
在晴朗的夜空,流星體受地球引力的吸引,在大氣層中劃過一道美麗而耀眼的軌跡,最后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之中,讓很多詩人感慨不已。然而在科學界,這種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現象也有不少。筆者最近在查閱一個學科的高被引文獻時,發現進入該學科千分之一的高被引文獻僅有22篇,其中就有6篇論文的第一作者為博士研究生。千分之一高被引論文,國外也叫熱點論文,大都是一些學界泰斗和學科領軍人物的代表作品,出現在一些初出茅廬的博士研究生之手,確實讓我感到震驚。這6篇高被引論文平均發表10年時間,分別被引用了133次、117次、115次、109次、74次和71次,分別居該領域高被引文獻的第7~10位、第18位和第21位,作者的平均年齡不到29歲,讓人感覺到該領域后繼有人,充滿活力。但接下來的追蹤卻令人更為震驚,在6位博士研究生中,有3位的論文全部是在讀研期間完成的,之后就像流星一樣消失了。類似的情景在其他領域也同樣存在。在崇尚科學的今天,科學界這座圍城確實是有許多人想沖進來,但也有許多人想沖出去。那么,他們為何乘興而來又如何興盡而去呢?經過調研,發現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一是從政說。宋真宗《勸學篇》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引發了無數學子的做官夢。現今,科學家從政的例子也數不勝數,從數十名考生追逐一個公務員指標,到數十名教授競聘高校的一位處長、副處長來看,科學家從政的熱度可想而知。贊成者認為從政有利于個人和團隊資源的爭取,反對者認為是“官本位”現象。但是把科學當作跳板,研而優則仕的用人制度是值得思考的。《中國科學傳播報告(2010~2011)》的調查表明,當問及被調查者“您是否同意‘科學家不應當擔任行政職務’”,表示“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比例為49.4%;表示“反對”和“非常反對”的比例為42.3%,期待值2.87。從期待值來看,在各項科學家可能擔任的角色或承擔的責任中,公眾對科學家“擔任行政職務”的期待值是最低的。中科院副院長李家洋曾經談到,太多的科學家從政,可能會使本該成為科學大師的人無法開展進一步的科學研究,因為科學創造需要時間保證。他認為國家在這方面應該有好的政策,有一種機制保證做一段行政工作后回到科研崗位上,而不是等到退休后再回到科研崗位。
二是移民說。“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科學精英遠比紅杏讓人擁戴。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憑借自身優勢,同發展中國家展開了曠日持久的人才爭奪戰。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3年1月29日演講提到:“我們教會了外國學生這些(科研創新)技能,卻讓他們回到中國、印度或者墨西哥創業,反過來同我們進行競爭。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進行移民改革的原因。”美國新移民法對特殊人才、杰出教授和研究人士、跨國公司高級主管和經理、在任何領域獲得博士學位者、某些醫生,以及這些人的配偶子女等的移民申請,沒有名額限制。對有高級學位和在美國大學獲得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碩士學位的移民申請,增加移民名額。也對一些技術工人的移民申請增加移民名額。此外,草案中明確將為想移民美國并在美國創業的外國企業家設立一個“創業簽證”。2008年,中國科協發布的中國第一份科技人力資源發展研究報告表明,盡管中國科技人力資源已經出現“回流”趨勢,留學歸國人員數量持續增長,但流出明顯大于流入,“人才流失”現象仍然比較嚴重,高層次科技人力資源稀缺現象依然存在。報告顯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后有70余萬具有高等學歷的人員出國留學,但是學成回國的人員不到1/3,2/3以上的人選擇留在國外發展。有關調查顯示,1985年以來,清華、北大涉及高科技專業的畢業生七成以上去了國外。《中國青年報》曾在清華校園做了一個隨機采訪,被采訪的18位學生中,明確表示希望出國深造的有14位。在被問到是否會回國時,表態堅決回國的只有3位。
三是焦慮說。“不發表就死亡” 和“非升即走”科研戒律,是科學家焦慮的源泉。意大利青年物理學家喬爾達諾,1982年出生于意大利都靈,粒子物理學博士,研究的是理論物理中與夸克有關的粒子計算。20世紀之前,科學家是可以讀懂其他學科文獻的。之后科學分化得越來越細密,每個人都在獨自的狹窄領域內耕耘。喬爾達諾講:“我一直在研究物理,但我沒法讀懂化學的文章,哪怕是和物理有關的,甚至是其他物理學家做的研究我都可能會讀不懂。因此在理論物理學界,許多人都很焦慮,沒有人滿意‘標準模型’,所有人都嘗試挑戰它。我曾經在一個極小的一個理論問題上工作了整整三年。從某種層面說,我是有挫敗感的,就像走進了死胡同。我想逃出去,這是我走出科學的原因之一。科學讓我逃避,但是寫作激發了我的興趣,它比科學更能符合我的好奇心。但是,如果我必須說的話,我覺得科學還是比文學,比其他任何學科都更加高級,尤其是物理,它是人類和世界關聯的最好方式。”當然,喬爾達諾是幸運的,他的處女作《質數的孤獨》,一出版便獲得意大利最高文學獎斯特雷加獎,兩年銷售逾120萬本,售出36國版權,暢銷全歐500萬本。從量子物理學家變成作家,從科學走入文學,這樣成功的例子雖然也有,卻不多見。
四是移情說。“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英國劍橋大學生物技術研究公司的研究人員艾瑪·查普曼曾在劍橋大學基督學院學習了四年,接著又做了4年科學研究,之后她在劍橋大學生物技術制藥研究公司謀到一個職位。但是她很快便厭倦了學術世界和科學研究,受一位朋友的影響,轉而喜歡上了跳肚皮舞。查普曼說:“跳肚皮舞讓我感到自由,我終于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這比做實驗有趣多了。我現在很難想象再去從事朝九晚五的工作。”查普曼的選擇得到了家人和男友的支持。與此情景相似的還有央視脫口秀主持人黃西,曾在中國科學院攻讀碩士,1999年獲得德克薩斯州萊斯大學生化博士學位,2000年到一家跨國基因制藥公司從事科學研究,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注射400個青蛙卵,這跟富士康流水線上的工人沒有多大的區別。為了調劑生活,業余時間接觸喜劇表演活動。白天他在實驗室做研究,到晚上就搖身一變成演員,表演單口相聲,2003年擠入波士頓國際喜劇節的決賽。美國深夜節目收視率冠軍的“大衛萊特曼秀”,在2009年的一天晚上破天荒邀請中國口音極重的黃西亮相,以英語講美式笑話,近六分鐘的演出,黃西一炮走紅,被美國人稱為是“喜劇界的姚明”。但讓他真正為國人所知,還是受邀到美國白宮表演。2013年加盟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是真的嗎?》欄目。黃西表示,喜劇表演盡管是他的最愛,“但這還是副業,一直到我能確定走這條路的收入充足穩定之前,還是要努力上班”。如果能支持生活的話,黃西承認他會考慮改行,因為“學術界不缺我這個中國人”。
五是孤獨說。遠行者孤獨,大音者希聲。代表人有孟德爾、馬寅初等。1865年,孟德爾獨創性地進行了豌豆雜交實驗,公布了他的劃時代發現——生物遺傳定律,在當時已經流行的進化論之外,獨辟蹊徑,開辟了生物學研究的新域——遺傳學。1866年,孟德爾的論文《植物雜交的試驗》在《布爾諾博物學會會刊》上發表,孟德爾自己將40本抽樣本寄給一些國際知名學者,但反響寥寥。最熟知孟德爾工作的耐格里出于偏見,讀了孟德爾論文的單行本之后,在自己的著作中只字不提。霍夫曼在專著中五次提到孟德爾的工作,但都是與遺傳定律無關的小問題。俄國的施馬爾豪森在其論著中雖然正確地闡述了孟德爾的創造性發現,但是該書的德文譯者卻把這一重要段落刪掉了。達爾文雖然也收到了孟德爾寄來的著作單行本,但只是讀了目錄就放下了,連正文書頁都沒拆開,看來至少是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而更多的人甚至連郵件都未曾拆封。直到遺傳定律公布34年后的1900年,才有荷蘭、德國和奧地利的三位科學家聲稱重新發現了孟德爾定律,但這時候孟德爾已經去世了16年,最終也未能盼來這一天。在社會科學方面,新中國建立后馬寅初因發表《新人口論》不合時宜,遭受到了來自全國上下的批判,1960年1月,馬寅初被迫辭去北大校長職務。與此同時,也剝奪了他發表文章的權利,馬寅初也由此從政治舞臺和學術論壇上消失了。
六是擠兌說。熙熙攘攘,利來利往,擠兌之說由此而來。有一次居里夫人的一位朋友去她家拜訪,看見她的小女兒正在玩英國皇家學會剛剛頒發給她的金質獎章,驚訝地說:“英國皇家學會的獎章是很高的榮譽,你怎么能給孩子玩呢?”居里夫人笑了笑說:“我是想讓孩子從小就知道,榮譽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絕不能看得太重,否則就將一事無成。”像居里夫人這樣視名利如糞土的科學家誠然是中流砥柱,但更多的科學家卻也是蕓蕓眾生中的一位,就連大科學家牛頓都不能例外,有的甚至是斤斤計較。木秀于林,風必摧之。1963年,來自臺灣的李文和懷揣著美國夢赴美,7年后獲得博士學位,于1974年加入美國籍。靠天分和努力成了“國家實驗室受擁戴的精英科學家之一”。他研究的多種核反應堆及其模式被許多國家所采用,為防止核泄漏立下赫赫功績。難以想象的是,即將退休的李文和由于被懷疑“向中國泄露核機密”,遭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最后陷入牢獄之苦。亞裔組織認為,李文和案背后存在著嚴重的種族歧視。由于李文和的訴訟獲得了積極的結果,2006年6月3日,美國聯邦政府和5家媒體組織宣布他們會一起向李文和支付160萬美元。另有一位斯坦福大學博士曾在東南亞一所分子與生物細胞研究院擔任16年的首席研究員,可是卻在事業顛峰期接到通知,告知他的應聘合約將在下一年度被終止。由于經濟蕭條,工作難找,離職半年后就當了的士司機。有一種推測講到,這與該地區的排擠風氣相關聯。
以上幾種觀點,只是對科學新星消失的注釋或猜測,相信還有許多觀點未能點到。
科學史表明,科學生活是清貧的,選擇科學就意味著選擇奉獻。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他們有自己的家庭和自由,如果能夠謀到一份比科學更好的職業,改善一下自身的生活環境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出出進進可以產生科學共同體的活力,進來時不一定為“最優秀的”,但是留下來的一定要是最優秀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若不能將一流的科學職位配置給最具有才華和最具有毅力的青年人,則就意味著會給次優人才配置一流的資源,就會造成為淵驅魚的效應,這一點務必要引起我們政策決策者和執行者的深思熟慮。1742年,英國天文學家布拉德雷被任命為格林威治天文臺第三任臺長。英國國王體諒天文學家的清貧,準備給他提高薪水時,布拉德雷謝絕了這一好意,他說皇家天文學家的薪水太高,必然會遭到許多投機鉆營者的覬覦,反而使真正的天文學家得不到這一職位。這絕非杞人憂天,如果在用人考評制度上不能月月新日日新,一些“人才工程”就會被鳩占鵲巢,而布拉德雷們就很有可能淪為打工仔。我們期待科學界少一些流星,多一些恒星和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