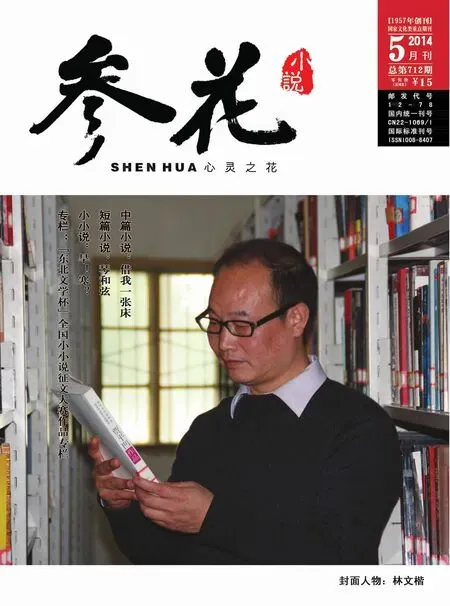論文藝的空靈美與充實美
◎劉德釗
論文藝的空靈美與充實美
◎劉德釗
本文從哲學的高度以及古人、西方、東方對藝術中美的追求,以藝術的空靈美與充實美為角度,探討了藝術中空靈美與充實美之間的關系。空靈美的高境界與充實美的實誠和諧為一個不可分離的文藝作品的整體。
文學藝術 兩元 空靈美 境界 充實美
一、藝術精神的兩元
藝術是一種技術,古代藝術家就是技術家(手工藝的大匠)。現代及將來的藝術應該特重技術。然而他們的技術不只是服役人生(象工藝)而是表現著人生,流露著情感個性和人格的。這一切都能反映在文藝里。它憑著韻律、節奏、形式的和諧、色彩的配合,成立一個自己的有情有相的小宇宙;而這一切都是圓滿的、自足的、必然的,因而是美的。
文藝站在道德和哲學的旁邊能并立而無愧。它的根基卻深深地植于時代的技術階段和社會政治的意識上面,它要有土腥氣,要有時代的血肉,縱然它的頭須伸進精神的光明高超的天空,指示生命的真諦。孟子說:“充實之謂美”。然而它又需超凡入圣、獨立于萬象之表,憑它獨創的形相,范疇一個世界,冰清玉潔,脫盡塵埃,這又是何等的空靈。
空靈和充實是藝術精神的兩元,而對空靈美和充實美,人們有一種近似本能的需求。
二、文藝的空靈之美
空靈美感的美成于能空,對物象造成距離,使自己不沾不滯,物象得以孤立絕緣,自成境界:舞臺的簾幕,圖畫的框廊,雕像的石座,建筑的臺階,欄桿,詩的節奏,韻腳。從窗戶看山水,黑夜籠罩下的燈火街市,明月下的幽淡小景,都是在距離化、間隔化條件下誕生的美景,即距離產生美。古人最懂得這種距離隔開之美,李商隱詞:“畫檐簪柳碧如城,一簾風雨里,過清明”。董其昌曾說:“攤燭下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他們懂得“隔”字在美感上的重要。
然而這還得依靠外界物質條件造成的“隔”。更重要的還是心靈內部的“空”。司空圖《詩品》里開了空藝術的心靈當如“空譚瀉春,古鏡照神”,形容藝術人格為“落花無言,人談如菊”,“神出古異,談不可收”。藝術的造詣當“遇之匪深,即之愈稀”。“遇之自天,冷然希音”。
精神淡泊,是藝術空靈美化的基本條件,歐陽修說:“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家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動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蕭條淡泊,閑和嚴靜,是藝術人格的心襟氣象。這心襟,這氣象能令人“事外有遠致”,藝術上的神韻油然而生。陶淵明的名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南下,悠然見南山”更能說明這一點。可見藝術境界中的空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由此獲得“充實”,由“心遠”接近到“真意”。
陶淵明愛酒,晉人王薈說“酒正引人著勝地”,這使人人自遠的酒正能引人著勝地,這勝地是什么呢?正是空靈的相反之面——充實美。充實之美正是我們要談的下一個問題。
三、文藝的充實之美
在歐洲歌德的生活經歷著人生多種境地,充實無比。在中國古代,杜甫的詩歌最為深厚有力,也是由于生活經驗的充實和情感的極其豐富。
司空圖形容著壯碩的藝術精神說:“無風浪浪,海山蒼蒼,真力溺滿,萬象在旁。”“返虛入渾,積健為雄”。“生氣遠山,不著死灰。秒造自然,伊誰與裁”。“是有真宰,與之浮沉”。“吞吐大荒,由道反氣”。“行神如空,行氣如虹”!藝術家精力充實,氣象萬千,充實美油然而生,藝術創造追隨真宰的創造。
中國山水畫趨向簡淡,然而簡淡中包具無窮境界,倪云林畫一樹一石,千巖萬壑不能過之。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種靈氣。惟其品著天際冥鴻,故出筆便如哀弦急管,聲情并集,非大地觀樂切中可得而擬議者也。
哀弦急管,聲情并茂,這是何等繁復熱鬧的音樂,不料能在元人一樹一石,一山一水中體會出來,元人造詣之高和南田體會之深,都顯出中國藝術境界的最高成就!然而元人幽談的境界背后仍潛隱著一種宇宙豪情,南田說:“群必求同,求同必相叫,相叫必與荒天古木,此畫中所意也”。相叫火于荒天古木,這是沉痛超邁深邃熱烈的人生境界。
葉燮在《原詩》里說:“可言之有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會意象之表,而理于事部燦然于前者也”。
為就是藝術心靈能達到的最高境界!由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實,然后宇宙生命中的一切理一切事無不把它的最深意義燦然呈現于前。
總之,如上所敘,空靈美于充實美實在是一對孿生兄弟,無空靈則無充實可言,無充實則空靈無從可談,它們是辯論統一的關系,互相對比、映襯又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特別在中國的文藝,空靈美于充實美兩方都曾盡力達到極高的成就。所以中國詩人尤愛把森林萬象映射在太陽的背景上,境界豐實空靈,像一座燦爛的星天。
[1]《藝術美學》田川流著,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7.07. 01
[2]《美的歷程》李澤厚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9.07.01
[3]《文藝美學》胡經之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06. 01
(作者單位:重慶師范大學涉外商貿學院 )
(責任編輯 劉冬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