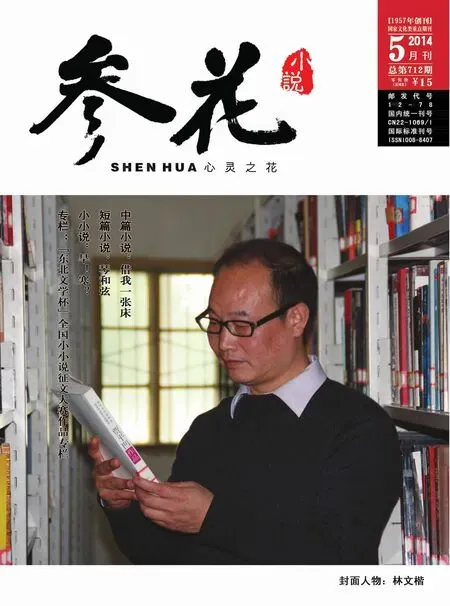虛擬的視覺文化時代
——淺析電腦游戲的互動及感官作用
◎孔令潔
虛擬的視覺文化時代
——淺析電腦游戲的互動及感官作用
◎孔令潔
在“虛擬文化”崛起的今天,理解玩家與電腦游戲的關系已經成為文化研究中的一個熱點。互動具有怎樣的意義,電腦游戲中的人機互動之所以有效,其背后的邏輯是什么,感官又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本文將在探討電腦游戲中人機互動的基礎上,挖掘感官在其中的作用。
電腦游戲 互動 感官
隨著傳統的圖像時代向“虛擬的視覺文化時代”[1]轉型,發生繁榮在網絡媒體與“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羽翼下的電腦游戲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理解玩家與電腦游戲的互動及其背后的邏輯,是面對“虛擬文化”時不可回避的問題。美國學者Friedl將電腦游戲的互動性分為三個維度[2]:玩家與計算機、玩家與游戲、玩家與玩家的互動。玩家與計算機的互動是作為其他兩種互動的基礎而存在的,“這種類型解決了玩家與游戲之間的所有問題,如系統的圖形和聲音功能”[3]。本文在探討玩家與計算機這一基本互動類型的基礎上,挖掘互動過程中玩家的感官對游戲互動“質量”的補充。
一、玩家與計算機互動的意義
將電腦游戲看作一個人,能更容易地說明互動的意義。人與人獲得關聯可以通過面對面的溝通,也可以依賴于各種媒介,人們總是根據不同的場合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媒介。但是無論何種交流方式,其本質卻都是互動,即傳達信息與獲取反饋。游戲的過程是互動的過程,互動是玩家獲得一切體驗與意義的基礎。正如麥克盧漢所言,“所謂‘游戲’,無論是生活中的游戲還是輪子里的游戲,都包含著相互作用的意義;必須要有來有往”[4]。Friedl認為每一種媒體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不同類型的互動性,而互動性在電腦游戲中之所以重要,正是由于它是人們玩游戲的背后驅動力。這是說,人們之所以玩游戲,是由于人們渴望在游戲的過程中互動,游戲的互動既意味著玩家可以在游戲中槍擊一個虛擬人物的快感,也意味著被虛擬人物擊中的風險。
玩家與計算機的互動是其他兩類互動的基礎,玩家必須以計算機為媒介才能進入游戲的世界。這種互動是“玩家與計算機之間的雙向交流,其中系統被看作是一個人物角色和伙伴,它與玩家具有同等的地位”「5」。玩家直接面對的是計算機,而游戲是由計算機呈現出來的,所以計算機更像是玩家與游戲之間的一個過濾帶,可以說玩家與計算機的互動是整個電腦游戲實現的過程。而玩家與計算機的互動之所以區別于普通的人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是由于玩電腦游戲過程中的人機互動本身還增加了游戲的成分。《人機互動手冊》(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andbook)的作者提出了玩家與計算機互動同普通的人機互動的六條區別,其中之一是玩電腦游戲中的人機互動側重于使用過程而非過程的結果,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學者對于玩家與計算機互動的探討多側重于游戲的設計方面。
二、玩家與計算機互動的“質量”與“同步性”
正如Friedl所言,現實中面對面的交流被看作是最有效率、最流暢的交流方式,是由于它滿足了兩條標準:“質量”與“同步性”。[6]所謂質量指的是信息的接收程度,其他任何的交流方式都難以達到當面交談的質量,面對面的交流不會有任何信息上的損失,一切都仰仗于人的感官能力。當面交流可以達到最佳的同步性卻不僅僅由于交流者能夠最即時地獲取信息,還在于第一時間做出的反饋動作也最迅即地被接收。可以說,玩家與計算機的互動是否有效,主要在于游戲過程中模擬當面交流的兩條標準達到了何種程度。在處于技術最前沿的當今,玩家早就能夠在電腦游戲中獲得流暢的體驗,但是這種體驗同現實的交流依然無法相提并論,這是由于游戲過程中質量與同步性往往此消彼長。游戲所提供的細膩畫質首先依賴于計算機顯卡的成像能力、cpu的處理速度,超高的畫質與酷炫的特效是以增加硬件負荷為代價的,對同一臺計算機而言,愈佳的視覺體驗意味著損失速度,也就是同步性。
耐人尋味之處在于,當面對質量與同步性無法兼得的情況時,玩家往往會選擇降低游戲畫面的幀數來換取游戲的流暢度。這似乎正應了Friedl所說的“玩家與計算機互動中的關鍵即控制因素是同步性”[7],因為計算機即使呈現出最高清的畫面,但如果要以延遲反應速度為代價,游戲將不再具備互動性的特征,也可以說是不可玩的。那么,當游戲過程中的質量在為同步性讓步而遭受損失時,又是以何種方式獲得彌補的?
三、感官的作用
美國學者邁克爾·海姆曾言,“虛擬現實”意味著在一個虛擬環境之中的感官沉浸[8]。電腦游戲作為虛擬現實的一種,它是在玩家與計算機的互動過程中,充分調動玩家的各種感知覺,將玩家帶入一個幻真的世界。這就是說,質量這一標準的實現有賴于玩家感官能力的配合。電腦游戲提供給玩家沉浸于虛擬世界的錯覺,是通過刺激玩家的視覺(影像)與聽覺(聲音)完成的,計算機憑借成像和高仿真技術,呈現電腦游戲中既模仿現實而又富有強烈美感的場景。下面是電腦游戲中常見的一個普通畫面:人物在山腰間行走時腳底揚起了簌簌塵埃,飄渺的白云在頭頂緩緩移動,玩家看到前方陡峭的山峰依然高聳云端,他身旁塊狀的斑駁巖石卻似乎可以觸手可及,仿佛只需輕輕一觸碎塊就會紛紛剝落,另一側飛舞的蝴蝶輕離花朵,粉紅色的花瓣似乎還在微微顫動……當今多數的主流配置的計算機都可以輕易將上述場景呈現在玩家眼前,與此同時輔以三維聲效,德勒茲所言的“觸覺化的視覺”功能已然被調動起來。所謂“觸覺化的視覺”即視覺在自己身上發現了一種它本就具有的觸摸功能,這一功能與視覺功能分開,只屬于它自己。[9]在游戲的過程中,玩家不僅看到了山巖與蝴蝶,而是只要玩家愿意,他仿佛就可以觸摸到它們,除了視覺與聽覺的愉悅,玩家還獲得了一種觸摸的快感,即是說玩家不僅僅是用他的眼睛和耳朵在玩游戲,他也在用眼睛觸摸游戲的虛擬世界,并且不覺得它是虛擬的。除“觸覺的視覺化”功能外,人的各種感官也是統一的,盡管在玩游戲的過程中玩家的視覺與聽覺功能占主導,但永遠不可能只是這兩種感官被喚醒,各種感官總是處于不可分割的聯系之中的。梅洛`龐蒂曾以聽覺為例做過這樣的解釋:“即使人們懷疑聽覺能給予我們真正的‘東西’,也至少能肯定聽覺能向我們提供在空間里除聲音以外發出聲響的某東西,所以聽覺與其他感官是有聯系的。”「10」玩家正是由于感官的聯合作用而進一步使“質量”這一標準得到提高,使他感覺到在游戲中的行動更像是在經驗世界中,游戲中人物的交談仿佛是他本人在與人面對面的交流。當玩家聽到游戲中嗒嗒的馬蹄聲,他被刺激到的不僅僅是聽覺,他仿佛還看到了一匹膘肥體健的駿馬正從他身后奔馳而來,仿佛馬上就要從他眼前掠過……感官的聯合營造了一種整體的現實效果,因為除了視聽之外,玩家的其他感官諸如味覺、觸覺等同樣會被喚起。
本文強調感官在玩游戲過程中的作用,是以計算機至少提供游戲所要求的最低畫質及音質的基礎上的。無可否認游戲畫面本身以及計算機硬件具有更基礎性的意義,但是從玩家這一主體的角度,感官卻表現出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很顯然,對于人的感官研究,是深入虛擬文化過程中無可回避的問題。
[1]《視覺文化的轉向》[M]周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47。
[2]、[3]、[5]、[6]、[7]《在線游戲互動性理論》「M」弗里德里.(Friedl,M.)著,陳宗斌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40,40,48,49,50。
[4]《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譯林出版社,2011:273。
[8]《從界面到網絡空間——虛擬實在的形而上學》「M」邁克爾·海姆著,金吾倫、劉鋼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15。
[9]《弗蘭西斯·培根:感覺的邏輯》[M]德勒茲著,董強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157。
[10]《知覺現象學》[M]莫里斯·梅洛-龐蒂著,姜志輝譯,商務印書館,2001:294。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 馮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