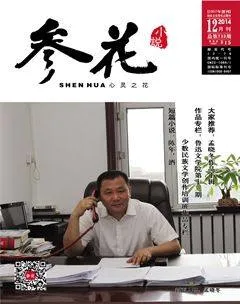基于生態美學的陶淵明田園詩研究
◎周健偉
基于生態美學的陶淵明田園詩研究
◎周健偉
陶淵明作為東晉末期宋初期的詩人、文學家、辭賦家、散文家,在詩歌、散文、辭賦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其創作具有獨特的風格和極高的造詣,其中對后世影響最為深刻的以其田園詩為典型,詩多描繪自然景色及其在農村生活的情景,語言質樸自然而精練,為古典詩歌開辟了新的境界。陶淵明的田園詩是他用全部的生命能量構筑的精神家園,蘊含著深刻的生態美學意義。因此,本研究主要從田園自然生態的展現、社會生態的描繪、精神生態的呈現三個方面來研究基于生態美學的陶淵明田園詩。
生態美學 陶淵明 田園詩
一、自然生態的展現
陶淵明田園詩中的生態美學意義首先體現在其詩作的自然生態展現方面,表現出一種天與人和的田園生態,筆者從其田園風光的生態美與田園環境的和諧美兩方面進行具體分析。
1.田園風光的生態美
生態美是伴隨著生態美學的產生而出現的一個新概念,對其具體的定義還存在著一些爭議,但都認同它它存在于人類與自然構成的整個生命共同體中,是一種共生的美。生態美把人們自發萌生的生態審美經驗上升到美學理論的高度,把人們的生態意識滲透到人的情感生活中去,因此,生態美概念的提出對生態文明建設與美學研究都有著重要意義。
從生態美來觀照陶淵明的田園詩,隱含于其中的生態智慧在一種敞開形態中顯現自身的力量,他的田園生活描寫處處體現了“生態美”,如鄰里的嬉笑、村舍的炊煙,田野的芬芳等。下面我們通過陶淵明的兩首田園詩來具體闡釋與感受其“生態美”。
其一:《歸園田居五首》之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在這首詩中,詩人用方宅、草屋、榆柳、桃李、村莊、炊煙、狗吠、雞鳴這些簡單的意象描繪了一幅樸素美好、自然清新的鄉村生活圖景,向人們展示一種寧靜、優美、和諧的鄉村田園風光。詩中并未涉及任何典故,也不曾運用物繪聲的形容詞,但是讀到這首詩,仿佛給人一種格外和諧的自然美的享受,似乎耳邊聽到了一支支悠然古樸而充滿詩意的鄉村牧歌,眼前看到了一幅生動逼真而富有立體感的田園風光圖。詩中一景一物都飽含了詩人的情感,充滿了田園的生活氣息。
其二:《和郭主薄二首》(其一)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飚開我襟。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余滋,舊谷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遞望白云,懷古一何深。”
這一首詩是陶淵明以夏季田園生活為內容的抒懷作品。此詩最大的特點是平淡沖和,意境渾成,令人感到淳真親切,勾勒出一幅完美的田園“生態美”畫面,讓人陶醉在這其中。詩中展現的都是人們習見熟知的日常生活,雖如敘家常,然皆一一從胸中流出,毫無矯揉造作的痕跡,因而使人倍感親切。無論寫景、敘事、抒情,都無不緊扣一個“樂”字。如,詩中前兩句寫到“堂前夏木蔭蔭,凱風清涼習習”,這是鄉村景物之“樂”;“既無公衙之役,又無車馬之喧,杜門謝客,讀書彈琴,起臥自由”,這是精神生活之“樂”;“園地蔬菜有余,往年存糧猶儲”,這是物質滿足之“樂”;“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這是天倫之“樂”。總之,景是樂景,事皆樂事,則情趣之樂不言而喻,從而構成了情景交融,物我渾成的意境。在這幽靜清涼的舒適環境里,詩人息交絕游,與書為友,過著適意得書齋生活。
2.田園環境的和諧美
陶淵明在田園詩中描繪了一種處于自然與社會之中的和諧田園環境,它給人帶來的“和”的享受,在這種環境中,互相作用的各種成分都處于最佳的關系狀態。在陶淵明的詩歌中,具體表現為天地與人的最相宜。
如《擬古九首》之一
日暮天無云,春風扇微和。 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 歌竟長太息,持此感人多。 皎皎云間月,灼灼月中華。 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在這首詩中,詩人描繪了這樣一種場景:在春風醉人黃昏夜,晴朗少風和煦,對盞把酒美人歌,看起來何其樂哉?詩人與環境之間處于一種和諧美好的狀態。
再如《時運》: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獨游,欣慨交心。
暮春是一年最好的季節,萬物生長,盡管詩中表現的情緒、蘊含的內容是復雜而深厚的,但是,詩人從寄情自然中獲得欣慰,無論是歡欣還是痛苦,詩中表現得都很平淡,語言也毫無著意雕飾之處。陶淵明追求的人格,是真誠中和,不喜不懼;所追求的社會,是各得其所,怡然自樂,因而在他的詩歌中,就形成了一種沖淡自然、平和閑遠的獨特風格。任何過于夸張,過于強烈的表現,都會破壞這種和諧的美,這是陶淵明所不取的。
在陶淵明的詩歌中,能夠讓人感到一種大自然的天籟、地籟與人籟和諧之美,他對自然有著一種溫和、樸實的感知,如《歸去來兮辭》中,他寫到“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擬古》中寫到“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歸園田居五首》之一中寫到“桃李羅堂前,榆柳蔭后檐。”《勸農》中寫到“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等等。這些詩句表現出的閑靜的內心世界對大自然恬淡和暢、充滿生機的偏愛,體現了陶淵明獨特的審美風格。從這些詩中樸素、優美、流暢的詩句中,可以感到陶淵明的內心與大自然之間的和諧,感覺到他內心的寧靜與和穆,在作者靜穆心態的觀照下也呈現出無限的審美意蘊。
陶淵明通常會在勞動中發現自然美,通過對農業生產自然環境的描寫,體現了天與人的和睦關系,歌頌自然的“和氣”。
如《歸園田居五首》其三:
種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 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 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這首詩寫的是田園勞作之樂,詩句樸素如隨口而出,不見絲毫修飾,表現的是歸隱山林的遁世思想,歡樂的情緒映射其中,體現出一種生活的質感。因為有了勞作,所以有了“南山”的美麗,將自然平淡的詩句融入全詩醇美的意境之中,使自然與人和諧地統一起來,形成陶詩平淡醇美的藝術特色。
陶淵明在詩歌中曾經多次寫到“鳥”,有時候它與詩人的心境結合在一起,如《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一》: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烏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撤,頗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詩中描繪的是在耕種與收獲的季節里鳥與詩人的生活的和諧,這是由于這種耕種和收獲的背景,使這種和諧之美展現的更加自然。在這些詩句中,詩人將田園里人的勞作,鳥及一切生命一一展現出來,顯示出田園生態的和諧之美。
二、社會生態的描繪
1.社會生態破敗的描寫
陶淵明 44 歲以后,在經濟上開始經受著一些波折,幾乎走到了山窮水盡的悲慘地步。陶淵明歸田躬耕之時,東晉王朝正處于內外交困的境地,百姓痛苦不堪,民不聊生。他不僅承受著上層統治者的瘋狂搜刮,而且也由于晉末農民起義的興起而面臨著殘暴的反動統治集團的血腥鎮壓帶來的各種威脅。加之于陶淵明的家鄉潯陽柴桑地區,是兵家必爭之地。詩人經濟生活上的巨變影響到創作,使田園詩的情調、色彩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長期的動蕩不安中,他看到社會生態的嚴重破壞,在其詩中也表達了深刻的感慨。
如《歸園田居五首》其四:
久去出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馀。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詩中描寫丁凋零殘破的農村景象,詩人用簡潔的詩句真實地反映了晉未軍閥混戰在農村造成的巨大破壞和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抒發出作者對故居面目全非的深沉感慨。首先作者通過“久去出澤游,浪莽林野娛”兩句道出詩人曾經長久離開山澤去做官,現在重返田園,又能在山林田野之間縱情游玩。“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寫作者與子侄撥開榛莽,步入荒墟。接下來具體描寫了一幅殘敗凄涼景象,昔日熙熙攘攘的村落,如今只剩下斷壁殘垣。
由此可見,陶詩中的農村,也絕非一片歡騰,其中也不乏愁苦之音。此類情景,還如其詩《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殫。
盡管在詩中作者并沒有直接描繪破敗景象,但從其詩句中,也能體會到詩人感慨萬千。“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寫在某一天氣候很好的日子里,和一些朋友結伴出游,就地開顏歡飲,或唱“清歌”,或吹管樂和彈奏弦樂以助興。這都是很普通的活動,詩所用的語言也很普通,看似是一件平凡的出游事件。但是又提到“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也就是說他所游是在人家墓地的柏樹下,要“為歡”偏又選擇這種容易引人傷感的地方,想起那些柏樹墓下的長眠者,千百年來,天災與戰亂是破壞社會生態最殘酷的殺手。在引人傷感的地方能夠“為歡”的人,不是極端麻木不仁的庸夫俗子,應該就是胸懷極端了悟超脫,能勘破俗諦,消除對于死亡的畏懼的高人。淵明并不麻木,他明顯地“感彼柏下人”死后長埋地下所顯示的人生短促與空虛;并且又從當日時事的變化,從自身的生活或生命的維持看,都有“未知明日事”之感。在這種情況下,還能“為歡”;還能做到“余襟良已殫”,即能做到胸中郁積盡消,歡情暢竭,當然有其高出于人的不平凡的了悟與超脫。以論對于生死問題的了悟與超脫,在淵明的詩文中,隨處可見,如《連雨獨飲》:“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五月中和戴主簿》:“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神釋》:“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挽歌詩》:“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歸去來兮辭》:“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2.良好社會生態的追尋
陶淵明對良好社會生態的追尋,主要體現在其與朋友、鄰居、親人的友好和睦的關系中,陶淵明自己躬耕于田園中保持著和他人友好的關系,他十分向往一種“人與人和”的和諧社會環境。在他的田園詩中存在很多描述“人和”的景象。
陶淵明喜歡山野生活,但他非常注重農村中人與人的溝通相交流,并不主張遠離人群,而是主張建立和睦的人際關系。
首先,從陶淵明與親人的關系來看,是十分融洽的。如《贈長沙公并序》中寫到:
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諧氣冬喧,映懷圭漳。
詩中表達了詩人對陶氏宗族,能夠繼承祖業的信心與榮耀感。詩中人物的氣度如同冬天的太陽,懷抱與圭璋互相輝映,表現出他與親人之間和睦相處的良好生活狀態。
其次,從陶淵明與鄰居的關系來看,也是十分融洽的,它是最能體現陶淵明“人和”思想的典型。如《歸園田居五首》里寫到: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日人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詩中“近局”即為近鄰,詩人獨自一人滿懷惆悵策杖歸來,經過了崎嶇而榛棘叢生的彎曲山路。山間的溪澗清澈且淺,洗我的雙腳也洗去了身心的疲憊。回到家中,濾出了新釀熟的美酒,殺雞招待鄰里鄉親。太陽落山了,室內暗了下來,烤制美味山雞的小灌木柴火燃得正旺,比明燭還亮堂。歡樂時總是苦于夜晚太短,邊吃邊說,不知不覺已經又到了天亮時分。這種融洽的鄰里關系不言而喻。
最后,從陶淵明與朋友的關系來看,也是十分融洽的,這些朋友是一些文化人或者在仕途中結識的朋友,并不是鄰居或普通的村人。性情相投的朋友們可以經常來往,經常見面,是“人與人和”的補充成分。如《飲酒》中寫到:
故人賞我趣,摯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殤酌失行次。
詩中描繪了老朋友贊賞我的酒趣,提著酒壺相會而至的和諧情景。鋪上荊條坐在松樹下,幾杯下肚便已有醉意。父老兄弟間七嘴八舌,飲酒也失去班輩次序。已感覺不到我的存在,哪還知道他物的重要。悠悠然不知身在何處,酒醉中自有深長的意味。其中的“班荊道故”的朋友,與“父老”相對出現在詩中,不是農人。
二是與詩人志趣相投,言語也非常投機的朋友。
由以上這三首詩可以看出,陶淵明與親人、鄰居、朋友之間存在著十分和諧的相處關系,其在田園生活中對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的關注與重視表現的淋漓盡致,人們都能夠生活在一種和睦的社會環境中是他的理想。
三、精神生態的呈現
精神生態,我們可以理解為人的一種理想,信念,情感等。在中國眾多的古代詩人中,陶淵明的精神生態體現在其超凡脫俗、追求心靈自由的處世態度上。一個人的思想與心態會受到其自身秉性、社會環境及文化氛圍等做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同時決定著陶淵明的精神生態。陶淵明的精神生態是和諧、健康的,筆者具體從以下兩方面進行具體闡釋。
1.對人生自然境界的追求
追求一種自然境界是陶淵明的精神內涵所在,并主要通過其精神上的自由與灑脫進行表現。陶淵明一生中最注重的就是本性率真的“自然”,其對自然之意的隱含表達在很多詩文中都有所體現,尤其突出表現在其歸隱之后的田園生活中。陶淵明之所以棄官歸隱,正是因為其“性”,即“自然”的本性的支配,當一個人充分展現出其“性”時,就可以達到一種至高的審美境界,獲得極大的樂趣,他依著自己的自然天性奔向田園,而并非一時心血來潮,他強調自然之性構成了他基本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態度。在陶淵明的田園生活中,內心充滿了愉悅與滿足,并通過其諸多的田園詩淋漓盡致的表現了他的自然之性。
如《歸園田居》(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陶淵明敏銳地感受到社會的腐敗、黑暗和虛偽,他厭惡這個社會,追求一種理想的生活,他認為只有用“自然”之義去凈化人類的道德,以凈化社會風氣。詩的開篇說,年輕時就沒有適應世俗的性格,生來就喜愛大自然的風物。“誤落塵網中”,很有些自責追悔的意味。以“塵網”比官場,見出詩人對污濁官場的鄙夷和厭惡。“羈鳥”“池魚”都是失去自由的動物,陶淵明用來自喻,表明他正像鳥戀歸林、魚思故淵一樣地思戀美好的大自然,回到自然,也即重獲自由。那么生計如何維持呢?“開荒南野際”就可以彌補以前的過失,得以“守拙歸園田”了。接下來描述恬淡自然、清靜安謐的田園風光。雖然陶淵明從小生活在廬山腳下,這里的丘山、村落原本十分熟悉,但這次是掙脫官場羈絆,從樊籠塵網中永遠回到自由天地,所以有一種特殊的喜悅之情和清新之感。他后顧前瞻,遠眺近觀,方宅、草屋、榆柳、桃李、村落、炊煙,以至深巷狗吠、桑顛雞鳴、無不是田園實景,又無一不構成詩人胸中的真趣。“暖暖”,遠景模糊;“依依”,輕煙裊裊。在這沖淡靜謐之中,加幾聲雞鳴狗吠,越發點染出鄉居生活的寧靜幽閑。結尾四句由寫景而寫心,“虛室”與“戶庭”對應,既指空閑寂靜的居室,又指詩人悠然常閑的心境。結尾兩句“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回應了詩的開頭。這里顯示的人格,領略自然之趣、從躬耕勞作中獲得心靈安適。田園生活充滿著情趣,能夠給人帶來很多淳樸的歡樂,這正是陶淵明夢寐以求的理想生活。只有在田園中,詩人才能得到生命的“真意”,才能找到真正的精神歸屬,體悟到人生的本真意義。
2.對精神家園的不懈追求
陶淵明生活在東晉王朝內外交困的時期,政治腐敗黑暗,社會動蕩不安,在他29歲時懷著“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出任江州祭酒。后因出身庶族,受人輕視,便“少日自解歸”。此后一直過著或仕或隱的生活。
陶淵明辭官歸隱故里之后,由于對現實社會的厭惡,在其詩歌中構筑了一個理想的社會,《桃花源記》便是其理想社會構建的典型代表,并期望以此超越現實的黑暗社會的束縛,使自己的心靈得以自由舒展。
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
詩人描繪的桃花源社會安寧,生活幸福,民風古樸,和諧相處,生態環境優美。如詩中“芳草鮮美、土地平曠,屋舍儼然,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等詩句都表現了詩人理想中的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統一。
陶淵明一生追求人生自然境界,安貧樂道又心系社會這種超然的人生態度,體現了其真正曠達與灑脫的精神生態。
結語
歷史無法逆轉,我們無法再回到當時的社會。盡管我們現代社會生活中沒有當時的苛捐雜稅,沒有那個特定時代的內憂外患,沒有戰亂的流血犧牲。但是,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們的社會中生態危機日益加劇、現代病癥肆虐蔓延,陶淵明追求和樂的自然生態觀,與他人和睦相處的社會生態觀,以及追求內心平和的精神生態觀,對當前的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依然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
[1]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 88 頁
[2]吳小如等.《漢魏六朝詩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版,第554頁
[3]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4]周秀榮.五十余年陶淵明田園詩研究綜述[J].九江學院學報.2006-08
[5]馬艷.談陶淵明的生態思想——以田園詩為例[J].長城.2011-10
[6]曹章慶.論陶淵明田園詩的精神生態[J].浙江社會科學.2008-07
[7].張今歌.趙圓圓陶淵明田園詩不朽魅力之探索[J].南陽師范學院學報.2010-11
[8]潘琳.試論陶淵明田園詩的思想主題和藝術特色[J].學理論.2012-05
[9]時蘭蘭.淺談陶淵明田園詩的藝術魅力[J].絲綢之路.2011-07
[10]林芬.陶淵明田園詩的再解讀[J].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9
(作者單位:東北財經大學職業技術學院)
(責任編輯 馮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