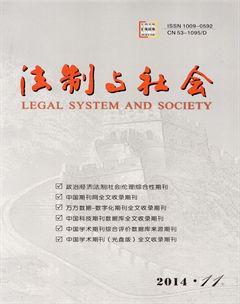論對生命權的憲法保護
摘 要 生命是從事一切活動的基礎,是首要的人權。地方政府“禁討區”的劃定與設置阻斷了乞討者獲得幫助的主要來源,導致的結果就是乞討者的生命權受到威脅,政府所設置的“禁討區”涉嫌違憲。我國憲法中并沒有明確規定生命權制度,應當修正憲法,將公民生命權的保護明文寫進憲法。為了實現對生命權的有效保護,我國需要建立起有效的針對包括公民生命權等基本權利在內的憲法救濟制度,設置專門的憲法監督機構,明確憲法監督機構的審查范圍及審查程序。
關鍵詞 禁討區 生命權 憲法監督
基金項目: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2011年度項目(11E105)。
作者簡介:鄧志宏,黑龍江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從事憲法學、行政法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D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4)11-020-03
一、 問題的提出
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安置城市流浪乞討人員,國務院于1982年制定頒布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試圖通過收容和遣返回原籍的辦法解決流浪乞討問題。但此制度在實施過程中暴露出很多問題,2003年發生的孫志剛案是積累多年問題的總爆發,它促使人們思考收容遣送制度的合憲性。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對任何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必須由法定機關依照法律規定進行。《立法法》規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設定法律。《行政處罰法》規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而收容遣送屬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其制定主體不合法。《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應該屬于《立法法》第87條規定的“超越權限的”和“下位法違反上位法的”行政法規。當年3位法學博士致信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審查收容遣送規定的合憲性,國務院自行廢止了收容遣送辦法,并出臺《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將原來的收容遣送改為自愿性質的社會救助措施。
更加人道的《救助管理辦法》并沒有有效解決城市中的乞討問題,有些地方出現了職業乞討者,影響了社會治安甚至導致犯罪行為的發生。為了維護公共秩序,各地采取各種手段試圖規制乞討行為,最受人矚目的就是“禁討區”的設立,所謂“禁討區”,就是在城市中劃分出特定的地點,禁止在劃定的區域進行乞討。有些地方政府通過制定規章明確規定在城市中的某些地點禁止乞討, 有些地方并未直接使用“禁討區”的稱呼,而是使用了“流浪乞討人員重點救助區域”等概念,但實質上在這些區域的乞討行為會被管理人員“勸離”,實質仍然是一種“禁討區”。針對我國目前越來越多的城市已經或正在醞釀設立“禁討區”這一事實,學術界與實務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有人支持政府維護公共秩序的行為,而更多的人則提出了質疑。有學者指出政府的行為侵犯了公民自由乞討的權利,也有學者指出“禁討區”侵犯了乞討者的生命權。本文擬探討乞討行為是否應當納入憲法生命權的保護,如果應該納入,則如何設立有效的制度從而實現對公民生命權的全面保護。
二、“禁討區”的設置與乞討者的生命權
(一) 生命權的內涵
有學者指出,生命權同自由平等權、財產權一起構成了當今社會的三大基本人權,它是人類享有的最基本的權利,是人享有其它權利的前提條件。學術界對生命權的定義有很多種,有的定義注重說明生命權不受非法剝奪的特征,這種說法有一定代表性,但其內涵有所局限。有的定義認為生命權的內涵應該從廣義理解,包括政治、文化、經濟等多方面地權利,這種觀點混淆了生命權與生存權,內容太過寬泛,也不可取。筆者認為以下兩種對生命權的定義比較合理,可以對我們理解生命權的內涵帶來啟示。第一種定義:“生命權是指自然人按照自然規律,安全地存在于世界上,其生命不受非法剝奪和各種危險威脅,以及在法定的特殊情況下可以放棄生命的權利。”此定義表明,生命權的主要內容包括存在權、安全權和一定的自主權,存在權是指人按照自然規律存在于世界上,生命不受非法剝奪。生命安全權是指人有權生活在安全的環境之中,生命存在不受各種危險的威脅。一定的自主權是指在極端特殊的情況下,人有權利選擇放棄生命(比如已經有國家立法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第二種定義:“生命權是指個人享有的維持其生命的延續和健康發展的資格。”此定義強調了生命權包括生命存在權、生命自主權和生命健康權。生命存在權是指胎兒脫離了母體成為生命體以后,其生命的存在具有法律上的意義,必須被作為獨立的生命看待,不能區分價值的高低。生命自主權是指每個人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有權自主地去照顧自己的生命,并謀求生命價值的實現。生命健康權是指每個人享有維護生命按照自身規律成長及患病時尋求治療、受到傷害時尋求保護的權利。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生命權的內涵也得以擴展。不僅包含任何人不得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內容,還含有國家和社會應對生命權給予尊重,國家要積極履行職責,避免損害個人生命權的現象發生。
(二)“禁討區”侵犯了乞討者的生命權
乞討行為是乞討者在生活無著、又沒有其他方式謀生以維持其基本生活時,用乞求的方式使他人給予施舍或者幫助的行為。可以理解為乞討行為發生時,乞討者由于饑餓、困苦等原因,其生命安全已經受到了實質威脅,乞討者試圖通過乞討的方式擺脫困境、維護基本的生命利益。在實踐中,有些乞討行為并不符合以上條件,違反了相關法律規定甚至涉嫌犯罪。其中一般違法的常見方式是強行乞討,這種特殊乞討方式是指行為人采取反復糾纏、強行討要或以其他滋擾他人的方式進行乞討,這種乞討方式已經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權益,《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1條第2款認定其為違法行為,治安管理機關可以對此類行為給予處罰。另外,現實生活中還存在一種乞討是為了牟取不正當利益,這些所謂的乞討者常被稱為“職業乞討者”,這些乞討者的生活并未遇到無法克服的危機,也沒有處于饑餓等無法消除的困苦狀態,只是由于好逸惡勞等原因,想通過“偽裝”而獲得路人的同情,從而達到不付出太多勞動就能有所收獲的目的。我們所探討的“乞討行為”排除以上分析的“強行乞討”和“職業乞討”兩種情況。
乞討者因生活無著或者遭遇某種困境,在無法維持基本生活的情況下,乞求他人幫助,這種乞討行為是一種自救的方式,是為了維護其本人的生命安全。那么乞討行為是否可以納入到“生命權”的保護范圍呢?那些乞討者在生活無著的特殊情況下,通過乞討的方式能維持其起碼的“活著”的權利,禁止乞討會使乞討者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生命權的首要內容就是“活著”的權利,生物學上肉體的生命不存在了,生命權其他的內容就是空談。所以有學者指出生命權是針對國家主張的權利,對乞討行為的保護就是對乞討者生命權的保護。上文論述生命權的定義時也談到生命權包含了生命自主權,公民個人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和社會公認的道德,就有權自主決定如何維系自己的生命,政府不能任意干涉和限制。從這個角度看,應當將乞討行為納入到“生命權”的保護范圍。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能有效解決許多低收入群體的生存問題,而憲法的“生命權”的義務主體是國家和政府,政府設置了“禁討區”,意圖規制乞討行為時,不僅沒有如憲法所要求的那樣,為公民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維持公民最基本的生活水平,從而履行尊重和保護公民生命權的義務,還對乞討者的“生命權” 構成侵犯。的確,乞討行為會給城市居民的生活帶來不便,還會影響市容和環境,但并不能因此就得出乞討行為擾亂了公共秩序這一結論,而“禁討區”的劃定與設置使乞討者不能在城市的主要街道、繁華路段乞求他人幫助,這樣就阻斷了乞討者獲得幫助的主要來源,導致的結果就是乞討者的“生命權”受到威脅,可以推斷政府所設置的“禁討區”涉嫌違憲。
三、構建我國的憲法生命權保護制度
(一) 我國憲法對生命權的相關規定
在我國憲法中并沒有對生命權制度做出明文規定。有學者提出生命權在我國憲法中屬于一項可以從其他條文中推導出來的隱含權利,與生命權相關的條款構成了我國的生命權制度。例如,憲法第44條、45條關于社會保障權的規定,就是通過具體的憲法規范,確認了與公民生命權密切相關的生存權。但仔細分析憲法上的所謂生命權條款,有的是對公民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等方面的保障(憲法第37、38條),有的是生存權保障(憲法第44、45條),嚴格說來,并不屬于通常意義上的生命權的內容。這里有必要澄清一個概念,生命權與生存權并不是一回事。國際人權憲章規定,生存權是指人人享有為自己和家庭獲得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足夠的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的權利。生存權的內涵更廣,尤其強調國家的積極作為義務,即國家與政府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使本國公民維持適當的生活水準。
而學者們指出的所謂生命權的隱含條款,多屬于保障公民生存權的條款,不能將憲法上的公民生命權保護擴大解釋到與生存權相同。另外,也有學者指出,我國2004年憲法修正案已經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內容,人權最重要和基本的內容就是生命權,人權條款可以看作我國現階段的生命權保護條款。筆者也不贊成此觀點,雖然生命權保護是人權保護的基礎,但人權是一個高度原則和概括性的概念,我們可以把憲法規定的所有公民基本權利都看作是人權保護的內容,甚至那些沒有納入到憲法保護的權利也是人權的組成部分,比如近年來有學者提出我國憲法應當增加多項人權,包括生存權、財產權、環境權、知情權、隱私權及遷徙自由權等多項內容。可見,人權條款并不能代替生命權保護條款,我國憲法現有規定對生命權的保護內容并不明確,也沒有建立完整的生命權保護制度。
(二) 完善憲法監督制度,保護公民生命權
1.將生命權寫入我國憲法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憲法中都明文規定了生命權,有學者統計,至2010年4月底,世界近200個國家中,有一百六十多個國家在其憲法中規定了生命權,范圍涉及世界各個大洲。值得注意的是,有九十幾個國家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將生命權納入憲法的。沒有在憲法中規定生命權的國家主要分布在亞洲和非洲。正是由于生命權對公民的基礎性、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將其作為一種隱含權利遠遠不夠,更何況如上文分析,我國憲法中和生命權相關的條款并不能涵蓋和取代生命權條款,其與專門規定的公民的生命權還存在很大差距。從世界范圍看,有的國家通過制定新憲法或修改原有憲法,在憲法上明確規定生命權的內容。有的通過解釋憲法相關條款使生命權成為一項憲法基本權利。在我國,學者們的觀點涉及到了這兩種方式,或主張通過解釋憲法對公民生命權進行保護,或主張直接將生命權寫入憲法。筆者贊成后一種觀點,即應當將生命權明文寫進憲法。關于具體的表述方式,我們可以參考國外比較成熟的立法模式。例如,在憲法中規定“人人享有生命權”(泰國、南非、印度尼西亞、尼日爾等國家);在憲法中側重規定國家對生命權的尊重與保護義務(日本、巴拿馬、希臘、阿爾巴尼亞等國家);在憲法中強調公民的生命不被任意剝奪(馬來西亞、阿富汗、緬甸、美國等國家)。很多國家的憲法還同時規定了依法剝奪公民生命的例外情形,比如死刑適用的條件與限制,胎兒的生命權等。我國憲法關于生命權保護的條款,不僅應當包括公民享有生命權的內容,還應該涵蓋國家對生命權的尊重和保護義務,從而順應生命權保護的世界潮流,體現出消極權利與積極權利兩個方面,同時適當規定有關死刑適用與胎兒生命權的問題。
2.構建我國的生命權憲法救濟制度
我國至今并未建立起有效的針對公民基本權利的憲法監督與救濟制度,雖然我國的《憲法》與《立法法》都對憲法監督制度有所涉及,但相關規定存在很大局限性。我國專門的憲法監督機構被公認為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而眾所周知,全國人大常委會每兩個月開一次會,會議內容涉及國家權力機關要解決的方方面面的問題,從時間與精力上看明顯力不從心。在具體監督程序與監督內容上,現有立法都沒有可操作性的規定,使我國的憲法監督只有一個宏觀設計,此制度并沒有有效運轉,公民的生命權等基本權利受到侵害時,也不能通過這一制度得到有效保護。我們既要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又要通過設置憲法監督機構等措施使這一制度運行起來。在現階段,我國的法院無法承擔違憲審查的重任,比較合適的方式是將憲法法院設立在全國人大之下,在全國人大之下設置憲法法院,與我國的政治制度并無沖突與矛盾。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是國家權力的享有者,人民有權通過各種方式監督一切國家權力的運行,通過設立憲法監督機構施行憲法監督制度就是人民行使監督權的一種方式。有學者指出,通過設立在全國人大之下的憲法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審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法律的合憲性,就相當于全國人大自己來行使違憲審查權,并不違反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保護公民生命權為例,憲法法院受理審查案件的內容,可以包括普通公民提出的憲法控訴案件,由法院來審查涉嫌侵犯公民生命權的立法和其他國家公權力侵犯公民生命權行為。當然,由公民提出的立法審查請求,應當同時附帶具體侵犯其生命權的案件。法院審查的涉嫌侵犯公民生命權的立法不僅應當包括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及單行條例,還應當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我國現行立法并未將法律納入到違憲審查的范圍,是現有制度設計的一大缺陷。另外,在我國目前立法及司法體制下,國務院部門的規章與地方人民政府規章還不能受到全面、有效的審查監督,應當將各類規章也納入到違憲審查的范圍,待將來通過行政訴訟等其他途徑能對規章進行有效監督時,再將這部分內容從違憲審查的范圍中去除掉。另外,還應當允許有權國家機關(如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省級人大常委會等)對涉嫌侵犯公民生命權的立法向憲法法院提出審查申請,這是國外相關制度中的所謂“抽象審查”,也是違憲審查制度的重要內容。審查機構、有權提出審查的主體及審查內容明確后,還要對審查程序做出科學合理的設計,使違憲審查制度真正起到有效保護公民生命權的作用。
公民生命權的保護是憲法學上的一個重大問題,從憲法條文對此權利的保護模式到執法、司法實踐中對此權利的保護,在我國都屬于嘗試與總結階段。生活當中與政府設置“禁討區”涉嫌侵犯公民生命權相類似的現象還有很多,我們要在人權保護等法學理論指導的基礎上,密切關注生命權保護的執法與司法實踐,借鑒和吸收他國的成功經驗,將我國憲法上對公民生命權的保護制度建立起來,并使之不斷發展、完善。
參考文獻:
[1]D市關于加強乞討管理的規定.新京報.2005-5-10.
[2]呂鑫.論禁討區.法學雜志.2012(5).
[3]楊海坤.憲法基本權利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4]張千帆.憲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5]王廣輝.比較憲法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6]上官丕亮.憲法與生命:生命權的憲法保障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7]王振民.中國違憲審查制度.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