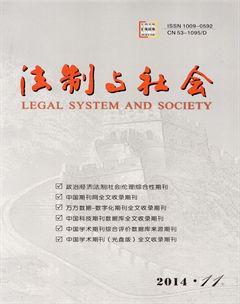宣告死亡制度的幾點思考
摘 要 宣告死亡制度是通過法院的宣告,人為地使自然人的人格歸于消滅。其目的重在維護被宣告死亡人利害關系人之利益,但其結果對失蹤人的影響也甚為巨大。自然人被宣告死亡后,將對其婚姻關系、財產關系與子女監護關系等產生影響,而宣告死亡被撤銷后對上述關系狀態的影響如何也需討論。
關鍵詞 宣告死亡 申請順序 撤銷宣告
作者簡介:湯光輝,南京財經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D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4)11-077-02
自然人離開其住所或者居所,或因戰爭、自然災難、事故等的發生而致使下落不明、音訊全無的狀態持續存在,謂之失蹤。宣告死亡制度意在解決因失蹤人生死不明而引起的民事法律關系不確定的問題。 我國的《民法通則》對宣告死亡制度作了規定,然而,或因立法過于簡略,值得商榷之處頗多。
一、宣告死亡制度的概況
(一)宣告死亡制度的概念
宣告死亡是指自然人離開自己的住所,下落不明達到法定期限,經利害關系人申請,由人民法院宣告其死亡的法律制度。以宣告死亡為研究對象,始于中世紀注釋法學派,但在法律上對之予以明文規定,肇始于德國普通法。1763年的普魯士失蹤法,則被認為是現代死亡宣告制度的起源。在當代大陸法系的立法中,設置宣告死亡制度的典型代表為德國和我國臺灣地區,德國與臺灣地區宣告死亡制度的特點在于,在規定宣告死亡制度的同時,還輔以設置“失蹤人的財產管理制度”,以解決在失蹤人在失蹤期間的財產管理與保護問題;有的國家雖未設置宣告死亡制度而僅對失蹤人失蹤期間的財產管理加以規定,但是其最終的效果卻等同于宣告死亡。如雖然《日本民法典》中并未設置宣告死亡的制度,但是,日本式的宣告失蹤的特點是明確推定失蹤達一定期間的人已經死亡,令其直接發生權利能力消滅的法定效果,但其效果卻等同于宣告死亡。
(二)宣告死亡制度的爭論
關于宣告死亡制度,學界對此的批判一直以來從未平息。持反對態度學者的理由或為“死亡”是中國人的一大禁忌,日常生活中人們總是本能地回避死亡,同時,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倫理道德的觀念影響,人們更加忌諱他人論及自己乃至至親的死亡;或為“然就我國倫理習慣而言,妻為夫之失蹤或子為父之失蹤訴請法院宣告其死亡,未免有背倫常,就實質言,死亡宣告本系對生死莫卜之失蹤人所作法律之宣告,”又或“宣告死亡與宣告失蹤就理論上言,經宣告死亡以后,而安然無恙歸來者,亦非事所必無,則死亡宣告一詞,似有語病,不若失蹤宣告之較為合理也。因而,極力主張宣告失蹤之稱謂替代宣告死亡,” 以上論斷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倫理說”僅僅從我國倫理感情的角度來闡述,且不是足以哪怕嚴重撼動倫理底線的倫理,在倫理觀念日益開放的今天,未免言之過重,僅以此來拒絕一項法律制度的適用,理由稍顯無力。在當代,宣告死亡制度并非僅僅是為了利害關系人與近親屬的物質利益,同時也事關未成年的監護與失蹤人配偶的生活與身份問題,因此,“很早很早以前以輿論宣告某人死亡的各種制度……得以延續,并非歷史的惰性力量,而是主張自己財產利益的抵抗力” 的論斷并不適用于評價今天的宣告死亡制度。
二、宣告死亡制度構成要件
我國《民法通則》第23條規定了宣告死亡的條件,可概括為:自然人下落不明達到法定期限,經利害關系人申請,人民法院可宣告其死亡。下面將就我國的宣告死亡制度提出兩點思考:
(一)申請死亡宣告的主體
依我國《民法通則》第23條之規定,當失蹤人在滿足宣告死亡的時間條件時,利害關系人可以向法院宣告死亡。利害關系人包括被聲請宣告失蹤人的近親屬以及其他與被聲請人有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人。 但經比較德國《失蹤法》第16條和《臺灣民法典》第8條可以發現,其均規定檢察官有權申請死亡宣告。
筆者認為,宣告死亡制度設置的目的主要在于保護失蹤人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在失蹤人生死不明的狀態持續一定時間后,為了解決一直懸而未決的民事法律關系,利害關系人可主動向法院提出申請宣告失蹤人死亡。如果利害關系人一直沒有向法院申請失蹤人死亡宣告,說明失蹤人的失蹤于其利益無損,或者可以推定為其與失蹤人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得到了妥善解決。如果國家公權強行介入,必將有損于其他利害關系人之正當利益。至于失蹤人沒有利害關系人的情形,檢察院更加不應該介入。宣告死亡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護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在法律上看來,如果利害關系人不存在,那么失蹤則無損于任何人之利益,也未把任何民事關系置于不確定的狀態。所以,申請宣告死亡與否,乃利害關系人之權利,全憑自己決定,否則即違反私法自治原則的基本要求。
(二)申請死亡宣告的順位限制問題申請宣告自然人死亡不論對失蹤人本人還是對利害關系人都影響甚巨
對申請宣告死亡是否應有順序上的限制一直以來學者們都見仁見智并各執己見。目前,學界主要存在兩種主張,即“有順序說”和“無順序說”。我國民法上采用“有順序說”,即如果第一順序利害關系人(配偶)不提出死亡宣告申請,其他利害關系人無權提出申請;近親屬不提出申請,其他利害關系人無權提出申請。
筆者認為,最高院采用“有順序說”有失妥當。其一,宣告死亡制度在于了結因自然人失蹤而導致的其與利害關系人之間未決的法律關系,保障利害關系人之民事權益。而不論債務人、債權人或者近親屬,他們都是法律上利害關系人,其法律地位應是平等的,與誰提出無關。其二,聲請宣告死亡的情況下,若必須征得配偶的同意,那么將有損于其他利害關系人之利益。實踐中,如果允許失蹤人的配偶對死亡宣告的申請可以“一言以廢之”,那么將有產生以下后果的極大可能:(1)其他繼承人利益受損。如有雖已成年但生有殘疾、生活難以為繼的子女需幫助,而失蹤人的配偶卻基于某種目的既不幫助又拒絕申請宣告死亡,失蹤人的子女卻因此而無法提前獲得遺產;(2)有害于債權人之債權。當失蹤人的配偶基于不正當的目的,如轉移失蹤人的財產以逃避債務,不愿意提出申請時,若債權人之前對此事因不知情而沒有及時申請設定財產代管人,那么其債權則有遭受危害之虞。(3)保險金受益人之利益受損。如失蹤人在失蹤前曾給自己投保死亡險,并指定受益人為其摯交好友,失蹤人在一起嚴重的意外事故發生后生死不明,經有關單位證明不可能生存。此時,如果失蹤人的配偶拒絕申請宣告死亡,則受益人則無法領取保險金。故“有順序說” 不免可能損害其他利害關系人的合法利益,違背死亡宣告制度設置的立法目的。
三、撤銷死亡宣告的效果
當被宣告死亡的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間重新出現或者被證明確實沒有死亡時,可以通過申請撤銷死亡宣告使財產關系、婚姻關系與其他民事關系得以回復。筆者認為,《民通意見》對收養關系的規定比較合理,但是對繼承關系與婚姻關系的規定存在缺陷。
(一)繼承關系
《民通意見》雖然規定,應本人之請求,依繼承取得原物的公民或者單位應該返還原物或給予適當補償。但是并沒有進一步規定。可以理解為如果失蹤人重新出現后要求返還原物,而繼承人拒絕返還時,那么將需要本人先申請撤銷死亡宣告后才有法律依據請求其返還。王澤鑒先生認為:“死亡宣告未經撤銷者,關于已經結束之法律關系不能自行復活,惟歸來后之法律關系可得以有效成立。” 誠然,依《繼承法》第2條之規定,繼承自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發生,而宣告死亡也是繼承的原因。雖然失蹤人重新出現但若不撤銷死亡宣告,那么繼承的基礎不會喪失,繼承人仍然可以拒絕返還財產。在現實生活中,被宣告死亡的失蹤人重新出現后如果沒有特別的需要,很少有人會主動提起撤銷死亡宣告之訴,況且撤銷死亡宣告的判決也需要一定的時間,不利于即時保護本人的民事權益。民法又稱市民法,嚴格來講是自然人法,市民法應當體現對自然人最終極的關懷。如果嚴格遵循法理,則我們就“剝奪了理應與自己平等的市民所應有的人權和應當得到的最起碼的尊重”; 在自然人長期生死不明之時,為了保護利害關系人之利益,經過價值的慎重權衡,才不得已作出宣告其死亡的決定。那么當失蹤人重新出現之后,法律應該在第一時間保護其合法權益。所以,筆者認為,當本人重新出現后,因繼承產生的財產關系可以自本人主張日起回復至宣告死亡之前。
(二)婚姻關系
宣告死亡為保護利害關系人之利益,其中,配偶的地位尤為特殊,所以,宣告死亡制度對婚姻關系應產生何種效力的問題應該格外慎重。我國《民通意見》規定:若被宣告死亡人的配偶未締結新的婚姻,那么夫妻關系自撤銷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復。但是,只要配偶已經再婚,不論后來是否離婚或者再婚后的配偶他方是否死亡,婚姻關系均不得自行恢復。如果失蹤人的配偶再婚,那么當失蹤人歸來時,原有之婚姻關系并不能自行恢復,失蹤人之配偶若仍想與失蹤人組成家庭必須提起離婚訴訟。筆者認為,如借鑒德國《婚姻法》第39條:其配偶如再婚時,不知道被宣告死亡者尚活于世,可以提起撤銷之訴,解除新的婚姻關系。 那么即可解決上述窘境,保護失蹤者的家庭關系。如果配偶知道失蹤人并未死亡,而后婚的對方當事人卻不知道,如果此時失蹤人出現,當如何處理?依德國《婚姻法》和我國民法后婚均有效。但對此等惡意宣告自然人死亡之情形,卻可以通過法律獲得正當的“名分”,不得不說是立法的疏忽。對此,臺灣地區的觀點:“若后婚雙方當事人均系善意,前婚因生存之配偶再婚的同時消滅”。 綜上,為解決以上困境,可以在民法上補償規定:被宣告死亡的人與配偶的婚姻關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滅。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消后,若后婚雙方當事人均系善意,前婚因生存之配偶再婚的同時消滅。同時,若后婚雙方均為善意,賦予失蹤人的“配偶”提起撤銷后婚之訴的權利。
注釋:
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67.
梅仲協.民法要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費安玲,朱慶育. 民法精要.中國政法大學教務處.1999.101.
依據《民法通則》我國的近親屬范圍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
王澤鑒.民法總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92.
劉洋.宣告死亡制度批判.研究生法學.2004(4).
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法律出版社.2003.130.
王澤鑒.民法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93.戴炎輝,戴東雄.中國親屬法.第2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