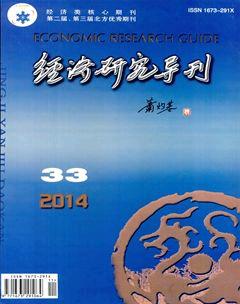四川省統籌城鄉的制約因素與發展路徑
唐虹
摘 要: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心,而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二元”的經濟與社會結構下,四川省表現為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的長期對立,派生出系列阻礙城鄉統籌的制約因素。要實現科學統籌城鄉,應從財政政策、體制機制、農業現代化、經濟區域規劃等方面突破。
關鍵詞:統籌城鄉;四川省;制約因素;路徑選擇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33-0064-03
2003年11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五個統籌”發展戰略,統籌城鄉居于首位。黨的十七大提出:“要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2010年中央發布了以“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為主題的一號文件,突顯了統籌城鄉發展的緊迫性和重要性。黨的十八大明確指出:“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繁榮。”
作為全國農業大省和西部唯一的糧食主產區,四川省糧食產量常年位居全國前列。但在開放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比較效益低的種糧行為使省內財政收入微薄的產糧大縣難逃財政窮縣怪圈,導致在社會經濟效益的激烈角逐中處于劣勢。在二元經濟結構和二元社會結構的“雙二元”現實中[1],四川省農村居民的土地資源優勢難以有效轉化為經濟優勢,致使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的差距日漸拉大,不利于省域經濟健康、協調發展,嚴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不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構建。為此,筆者認為探討制約四川省城鄉統籌發展的瓶頸,并提出協調城鄉發展的有效路徑具有重大的實踐價值。
一、四川省統籌城鄉發展的制約因素
(一)農村人口非農化速度緩慢
在二元結構體制下,城鄉長期的分割局面使工業對農業的反哺、城市對農村的輻射帶動難以達到預期目標,導致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的初衷與發展農業農村的現實漸行漸遠。一方面,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生活條件改善缺乏穩定充足的資金投入,較之快速增長的經濟水平農業產出效益每況愈下,城市房價漲速遠遠超出農民增收水平而無力購買,客觀上阻礙了四川省農民市民化進程。另一方面,作為人力資源輸出大省的四川省雖然有豐富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但滯后第三產業的發展水平又制約了農村人口城市就業容納量,緩慢的農業人口非農化進程嚴重工業化發展,從而成為四川經濟發展的一大短板。
(二)城鄉收入差距日益擴大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03年、2013年全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2 936元和8 896元;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9 422元和26 955元,絕對收入差距從6 486元拉大至18 059元。收入差距問題在四川表現也較為突出。據統計,2004—2013年四川城鄉居民收入比分別是2.99、2.99、3.11、3.13、3.07、3.1、3.01、2.92、2.83;四川省同期城鎮基尼系數為0.275、0.263、0.266、0.276、0.278、0.273、0.275、0.267、0.291[2]。這與國家在2013年1月首度公布的數據,即2003年0.479、2006年0.487、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2年0.474,相距甚大[3]。四川省統計局方面解釋為四川的城鄉基尼系數是對城鎮和鄉村分開核算的,核算口徑與國家不一致。所以在分析中,國家統計數據更有參考意義。因此,從城鎮收入上來看,城鎮居民生活水平雖然已實現小康標準,農民生活也較為富足,但是基于基尼系數判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很大。而事實上,四川城鄉居民生活的實際差距往往大于官方數據。原因在于統計口徑的不一致,農民純收入往往囊括了生產資料費用,若扣除其生產資料投入后,農民生活開銷僅為其純收入的70%左右。加之農村居民所能享受的各種福利也遠遠少于城市居民,若再計上各類福利,保守估計四川的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實際差距已越5倍,客觀上拉大了城鄉居民間的收入差距。
(三)工業化、城鎮化水平低
2013年底,四川省常住人口約8 107萬人。其中,城鎮人口占44.8%,城鎮化率為44.9%,遠低于51.27% 的全國平均水平。全省共有城市21座,省會成都是全省唯一的副省級城市,地級市17個,3個自治州。由于四川省城市較之發達省份數量少,人口基數大而城市規模小致使城市人口密度較大。較大的人口密度增加了原本有限的城市人口容納壓力,使得城市空間負荷加大。就工業企業而言,四川省的現狀是缺大弱小,較低的行業集中度很難輻射農村發展,較低的產業關聯度難于帶動農業發展,加之相對弱小的民營經濟也是導致四川省城市化落后的現實困境。相比于城鎮化飛速發展的東部省市,四川省的私營企業、個體經營戶的數量遠不能望其項背。
(四)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布局下四川未能從產糧大省向農業強省轉變
糧食既是人民群眾最基本的生活資料,也是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戰略物資。糧食安全始終是關系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戰略問題[4]。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國家會給各糧食主產區下達糧食產量指標,并且嚴格把關主產區耕地的征用與去向,盡可能減少農田去耕化。中國約有800個縣符合產糧大縣的標準與條件,其中四川省有88個,占據全省181個縣級單位的48.62%。為積極配合國家糧食安全的戰略部署,四川省的糧食主產縣堅定不移地執行國家戰略任務,而沒有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自主決策經營其他,絕大多數農地只能用于種植比較收益低下的糧食作物。同時,四川省城市人均耕地僅為1.11畝,比全國1.36畝的平均水平低0.25畝。
基于國家戰略,四川作為糧食主產區的農業大省地位無可替代,如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所言,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農業不能對國民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只有現代化的農業才能對經濟增長做出重大貢獻[5]。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四川目前難以發展為農業強省。為調動糧農的種糧積極性和激勵產量大縣對糧食種植的重視度以確保國家糧油安全,自2005年國家陸續以現金流的方式對產糧大縣進行獎勵,財政部出臺無以復加的政策加大對產糧大縣的財力支持,但是平均后微薄的設立專項資金獎勵糧油大縣卻難以化解產糧大縣的財政困境。四川不少人口近100萬的產量大縣,人均種糧補貼僅有10元上下,遠遠不能真正激發農民種糧積極性。endprint
二、新時期四川省統籌城鄉的發展路徑
(一)加大財政資金投入力度
為解決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村與城市長期分離、農民和市民社會地位不平等、農業嚴重落后于工業和其他產業的現實,以促進農業發展、助推農村建設和扶助農民增收,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確保“三個優先”,即“確保財政支出優先支持農業農村發展,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優先投向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村民生工程,土地出讓收益優先用于農業土地開發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6]但是單單依靠國家財政資金“單兵突進”無法從根本上破除三農困境,還需發揮金融行業對農業農村發展的主導作用,為其發展贏得更多的財力支持和物力援助。事實上,在四川省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中,薄弱的農村金融服務已然是制約農業發展、農村繁榮和農民增收的瓶頸。為完善農村金融服務功能,增加農村信貸資金投放額度,四川省的政策指向可以中央一號文件的“三個優先”為藍本采取措施:一是為加快現代農業建設步伐和完善農村基礎設施,開設長期穩定的政策性信貸業服務;二是搭建鄉村銀行、投資公司、資金互助社等融資平臺;三是確保消除部分偏遠鄉村基礎空白的金融服務。概言之,結合四川鄉村金融服務的實際需求與明顯表征,通過完善措施以實現方式改進,從體制機制層面推進四川省農村金融服務不斷創新。
(二)推行農地適度規模化經營
當前,四川省農村地區尤其是偏遠農村的土地利用有效率普遍偏低,即使不斷增加單位面積的資金投入也難以明顯提高單產,致使本來就低下的比較收益相比更低,這從根本上挫傷了農民種地積極性,更愿意將土地擱荒而外出務工。為從根源解決此癥結,在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可依法對農地進行自愿有償、合理有序的流轉,推行土地的適度規模經營,使農村土地向愿種糧、能種糧、會種糧的經營大戶集中,實現集約化經營模式下的農業產業化,為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提供平臺保障,并以此拓寬農民的增收渠道,扶助農民大幅度地穩定收入。
(三)促進農業產業化、現代化
一是要積極響應《國家農業綜合開發高標準農田建設規劃》部署,加快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以提升耕地質量,既提高糧食生產能力又確保糧食安全的現實需求,在發展現代農業的同時又滿足農民增收的迫切需要,在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指導下推進新農村建設。二是突出以良種培育為農業科技創新的重點,加快推廣應用創新體系建設;充分發揮龍頭企業的引領效應,鼓勵成立農村經濟合作組,大力建設準化的農產品標基地,走出一條“公司+基地+農戶”的產業化新路子[7],加快推進改革農村經營體制,重視科技創新,以產業化、現代化的農業為統籌城鄉助力。
(四)加快推進小城鎮建設步伐
加快推進城鎮化建設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舉措。發展城鎮化是中國緊迫的現實任務,農業雖是破題城鎮化難題的有力支撐,但實現城鄉統籌必須在農業以外下大功夫。就城鄉關系而言,小城鎮是連接城市與鄉村、工業和農業的紐帶,既為農村社會提供公共品以滿足農民的日常需求,也能為農業以外的其他產業行業提供服務平臺和搭建服務載體。因此,四川在打造大中型城市的同時,要重視小城鎮建設。應積極制定有效措施并有力貫徹執行,加大政策保障和資金扶持力度,加快城鎮化發展步伐以加速城鄉一體化進程。
(五)加強城市帶建設和主體功能區規劃
一是做好天府新區規劃。成都天府新區的設立能為四川發展和城鄉統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天府新區包括成都市高新區南區、雙流縣、龍泉驛區、新津縣、簡陽市、彭山縣、仁壽縣,共涉及3市7縣(市、區)37個鄉鎮和街道辦事處,總面積1 578平方千米[8]。2011年11月這足以形成以現代制造業為主、高端服務業集聚、宜業、宜商、宜居的國際化現代新城區,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舉措,利于助推四川在西部地區迅速崛起。二是執行好四川省金沙江下游沿江經濟帶發展規劃。金沙江下游沿江經濟帶范圍包括攀枝花市仁和區、西區、東區、鹽邊縣,涼山州會理縣、會東縣、寧南縣、布拖縣、金陽縣、雷波縣,宜賓市屏山縣、宜賓縣、翠屏區[9]。沿江經濟帶的合理規劃與有效執行,利于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科學發展。三是科學規劃四川省主體功能區。主體功能區包括成都平原地區、川南地區、川東北地區和攀西地區[10]。主體功能區的合理規劃,有利于引導人口分布、經濟布局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促進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的空間均衡總之,無論是天府新區、主體功能區,還是金沙江下游沿江經濟帶的設立都利于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帶動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重大戰略決策;利于不斷加強開放合作,促進城鄉居民增收,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有利于按照以人為本的理念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規劃》的科學制定和良好實施可以為四川加快實現城鄉統籌提供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三、結論與余議
協調城鄉統籌,根本上要立足于充分發掘農業自身潛能,工業對農業的反哺也是必不可少的助推器。作為城鄉統籌的主要參與者和受益者,廣大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就業與其增收息息相關,應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進程中,加快健全完善以工促農的政策體系和以城帶鄉的體制機制,以良性的城鄉互動促進統籌。在城鄉間經濟社會長期“二元”的體制下,破解三農問題必須實現從二元向一員轉換[1],尤其是作為國家糧食主產區的四川省是國家不可或缺的糧食戰略基地,要協調好城鄉統籌,實現經濟一元化、社會一元化是基本前提。
參考文獻:
[1] 王國敏.城鄉統籌:從二元結構向一元結構的轉換[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9):54-58.
[2] 四川統計局.四川統計年鑒(2004—2013)[K].
[3] 國家統計局.國家統計年鑒(2004—2013)[K].
[4] 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2020年)全文[Z].
[5] 西奧多·W.舒爾茨.報酬遞增的源泉[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6.
[6] 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Z].
[7] 張振江.河南省縣域經濟類型及其發展模式選擇[J].安徽農業科學,2009,(15):401-407.
[8] 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區總體規劃(2010—2030)[Z].
[9] 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金沙江下游沿江經濟帶發展規劃(2012—2017年)[Z].
[10] 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主體功能區規劃[Z].
[責任編輯 陳丹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