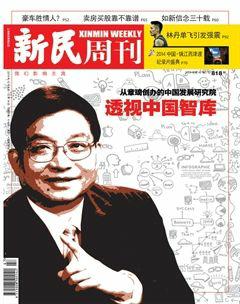大學生紀錄片人:有好嗓子就想唱歌
闕政


今年,鎮江西津渡國際紀錄片盛典在初選階段已經收到700多部紀錄片報名。而這之中,旨在扶持新銳導演的“新地平線”單元,就有多達500余部作品。
越來越多年輕人進入了紀錄片的世界,90后的加盟也早已不稀奇——事實上,今年盛典上,短片單元的最高獎獲得者,就是90后,西津渡最佳(定制)紀錄片獎獲得者,也是90后,她們都是學生,還都是女孩子。
上海女生解修遠的徽州情結
解修遠來自上海,正在上大廣電編導系就讀研究生。這并不是她第一次參加盛典——去年,她的《挑山女人》就在首屆盛典上拿到了中片最高獎:金山獎。
1991年出生的她看起來就像個典型的90后上海女孩,長發飄飄,說話細聲細氣。初三那年,她第一次舉起攝像機,拍下自己爺爺奶奶的一天生活,那時用的剪輯軟件還是“繪聲繪影”。爺爺奶奶是徽州人,在他們的影響下,解修遠上了許多徽州地方論壇,了解到日漸消失的傳統地方文化,“徽學、藏學和敦煌學,是中國三大地方顯學,但現在,相比敦煌學研究的繁榮和藏學研究的國際影響力,徽學顯得有些冷清。”
2009年,她跟父親去徽州山村,在那里拍了第一部作品《不嬉不行》。“那里的山上有一塊光面的大石頭,容易反射太陽光引起火災。當地村民一直有‘敬火神的祈福儀式,由祠堂組織大家一起‘嬉魚燈。但是這樣的傳統正在慢慢失傳。”這部《不嬉不行》,讓她獲得了搜狐全球華人紀錄片盛典的“最佳文化傳承紀錄片”。
這之后,解修遠的徽州紀行,一發不可收。她的父親就是她的最佳拍檔,兩人經常一呆就是半年——到后來走在鄉間的路上,村民們都會熟稔地以網名相稱。
外表柔弱的她,內里對紀錄片的執著卻很堅硬。每次拍攝之前,解修遠都要進行長期的田野調查,用她的話說:“在山區亂住,對那里的人有了了解之后,就會感到自己的眼睛、耳朵全都打開了。”
徽州祠堂文化發達,績溪北村還保留著一種習俗:男人到了40歲,要做包子分給全村16歲以上的男丁。“有個很有名的徽廚,平時已經在北京定居,到了40歲那年,還會舉家回來,完成這個約定俗成的儀式,這也是他們對子孫的一種誠信教育。”解修遠說,“村里對這件事非常重視,包子一個四兩,做之前,家里的秤都會先拿去祠堂校驗。母親也會提前一年養一頭黑毛豬,到這天,用三支香請出來,還要給豬穿上絲綢衣服,安上玻璃眼球,看起來炯炯有神,他們叫作‘豬倌,抬到祠堂,先敬拜祖先,再分給幫忙做包子的村人。”
這段故事,被解修遠拍成了紀錄片《男人四十》。而她跟過時間最長的,還是《挑山女人》的主人公汪美紅——“從大一寒假一直跟到研一。丈夫意外去世之后,她就帶著三個孩子,靠挑山過活,每天挑著兩個液化氣罐,幾百級臺階,上上下下好幾次。有一次我也試著去挑挑看,扁擔放到肩上,用盡全力,兩個氣罐根本就沒有離開地面。”
最讓解修遠深有感觸的是:“她對生活完全沒有抱怨。我從來沒有見過心態這么平和的人。”她拍了一部以此為題材的短片《媽媽是座山》,引起不少媒體關注,央視《新聞30分》報道之后,柴靜的知名節目《看見》也對汪美紅進行了專訪。后來這個故事還被上海寶山滬劇團改編成了滬劇,在高校巡演,今年更獲得了中宣部的“五個一工程獎”。
不過,解修遠對此卻高興不起來,因為她看到,成為宣傳事跡之后的汪美紅本人,生活并沒有因此產生多大改善,反而會被鄉鄰視為“名人”另眼相待,誤以為她借機生財。
去年,《挑山女人》獲得鎮江紀錄片盛典大獎后,又被組委會推薦給卡塔爾半島國際紀錄片節參賽。今年,她講述抗戰老兵重聚首的新作《最后一次集合》,又獲得了西津渡最佳(定制)紀錄片獎。這部作品同時也成為盛典《看見中國》的100部定制紀錄片之一,解修遠以簽約導演的身份,獲得了組委會給予的3萬元拍攝資金。
“去年領獎的時候我說:感謝組委會我又有錢拍片了。大家哄堂大笑。”解修遠說,“今年盛典的定制片統一格式、打包起來對外推廣,對我們自由制作人來說,傳播力量更大了。”
西藏女生旦增的異鄉廚房
來自西藏的大學生旦增色珍,同樣入圍了本次盛典。在藏語里,她名字的意思是“永不消失的明亮燈光”。
色珍也是個90后女孩,正在英國普利茅斯大學就讀,學習媒體藝術。留學期間,她在當地一家中餐廳打工,身邊的三個同事,都是異鄉人——強哥,香港人,20多歲被母親勸說從香港來到英國;桑德拉,英國出生的香港二代移民;奧斯卡,庫爾德來的偷渡客。
許多個夜晚,色珍和他們三人一同忙碌在異鄉的廚房。一開始,她只是想通過拍攝廚房生活,記錄一段自己的打工經歷。但越拍,越發現,“每個人都和他們看起來不太一樣”。
“強哥性格獨立,不喜歡跟外界交流,一開始看到我的攝像機就躲。但后來我發現他其實很渴望能和他那些說英語的孩子們溝通。而桑德拉,她生在英國,生活一直很英化,卻還是會不由自主地往自己的文化根里走。她讓我覺得文化其實沒有好與壞,你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去選擇。還有奧斯卡,看起來邋里邋遢玩世不恭,其實對庫爾德的動蕩很有自己的看法。他剛來英國的時候很長時間都是黑戶,住在很小的房間里,沒有一個朋友。現實很悲哀,他卻很樂觀,經常會說一些‘我以后要開個店,以后要回庫爾德去當農民之類的話,給自己希望。”色珍說,“他們對人生的態度、對本國文化的認同,都會影響到我。”
這些細碎的人生表里,都被色珍忠實記錄在了紀錄片《一夜廚房》里——它最終獲得了盛典短片最高獎,數位國際評委都對它交口稱贊。
細細觀察這些大學生紀錄片人,會發現他們拍攝紀錄片的共性——從對一件事產生感情,到想記錄自己的一段生活,再到繼續挖掘出有價值的拍攝對象——這三部曲式的創作心路,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
盛典評委、中國傳媒大學資深教授朱羽君說:“紀錄片之所以對青年人有這么大的吸引力,正因為表達本身就是一種愉快,就像你有一副好嗓子,就會想唱歌。”
和從前相比,如今的紀錄片拍攝更個性化:“我們以前做片子很慎重,十幾個人才有一臺機器,創作講規劃,有組織。現在呢?科技解放了影像,年輕人的紀錄片隨心所欲,想拍就拍。有喜歡獵奇的,愛往西藏青海跑,暑假旅游一趟,順便就拍成了片子;也有沉穩一些的孩子,關注現實,關注弱勢群體,專業精神比較強。尤其是女孩子,本就細膩、敏感、善于觀察生活。這次入圍的紀錄片里就有許多是女大學生的作品。”
在她看來,過去是文字傳播時代,盛產文學青年,一紙一筆就能寫作;如今已經到了影像文化時代,盛產影像青年,而攝像機,就是他們的紙和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