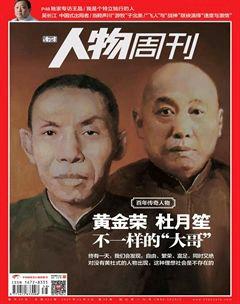記憶與遺忘
“我清楚地記得那個早上。我們紐約辦公室的一個負責人剛好到澳大利亞公司總部來開會,他們一般很少到總部,所以我記得特別清楚。那天我們本該按照例行安排開視訊會議。但紐約那邊一直都沒有回應。接著看新聞,我們就看到飛機撞擊雙子塔的畫面。”
在“9·11”紀念館外,A跟我說起她的“9·11”記憶。她是澳大利亞人,剛好在紐約旅游,很早就到紀念館,希望能參加紀念儀式,但被守在紀念館入口處的警察告知,早上的儀式只有受害者家屬能夠入場。但她并沒有離開,而是坐在外面,希望這是一種特殊的陪伴,向罹難者表示悼念,向受害者表示尊重和支持。
在館內,每年例行的儀式如期舉行。罹難者家屬們在紀念館外的Memorial Plaza聚集,開始輪流上臺念逝者的名字。每一個名字在Plaza大水池的流水聲、哀傷的大提琴聲、人群的靜默聲中蕩開。當他們念到自己的親人、愛人的名字時,聲音突然顫抖起來,甚至忍不住抽泣。很多人都哭著說一小段話介紹逝世的親人,表達自己的思念之情。
“我的同事說,念名字的儀式持續(xù)了5個小時,在現場,感受一定很復雜。”夜色中,紀念館的工作人員C說。她是賓州人,2月份剛在紀念館找到工作。她向我介紹兩個水池的設計理念,指給我看那個在“9·11”的大火、煙塵和碎屑中幸存下來的生命之樹的位置。
夜色中的Memorial Plaza雖然人還是很多,但沒有了白日的喧囂。月光灑在水池邊上的鐵欄,上面鏤刻的罹難者名字上,很多插著鮮花。我走過了一個日本人的名字,看到了祈禱世界和平的千紙鶴。
“恐襲發(fā)生后一個星期,我從科威特回國,當時站在廢墟上,心里就特別生氣。這件事情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身穿軍裝的H回憶起來并不平靜。他批評克林頓在90年代早已發(fā)現本·拉登的蹤跡,卻對在海外接連發(fā)生的恐襲未采取強硬手段。他對于奧巴馬未能吸取克林頓時期的教訓也是十分不滿:“伊斯蘭國現在的情況,跟奧巴馬要求撤軍、減少干預脫不了關系。”
這是一個特別的紀念日。一個籠罩在新的恐怖主義威脅下的紀念日。但對于夜色中望著大水池哭泣的男子來說,這是他的摯愛至親離開的第13年。很多人的生命中,突然消失了一個重要的人,像是紐約的天際線中,雙子塔永遠地消失,只有在紀念日時才有兩束藍光去填補那片空蕩蕩的天空。
但就是那兩片水池一樣,生命雖然消失,卻又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