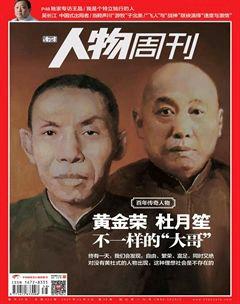獵人小屋
1
在經過無數次打探后,宋林終于找到了路邊的一個小站牌。從上面的波蘭語里,他僥幸認出了幾個斯洛伐克地名,其中一個叫Zdiar的村莊就是他打算去的地方。
他看了看表,離下一班15:15的車,還有3個多小時。這意味著他有足夠的時間,在扎帕科內——這座列寧呆過的小城市晃蕩一番。他沿著小鎮的街道走著,山非常美,山頂云霧繚繞。早上天氣很涼,但太陽出來以后,就讓人感到一股暖洋洋的熱意。宋林進了路邊一家餐館,去洗手間換下襯衫,換上一件干凈的短袖polo,然后點了一份烤雞肉串和一杯啤酒。
一群俄國人也走進來,從他們手中的小旗上,宋林看出這個團來自莫斯科。其中一個人突然指著宋林的盤子問服務員這是什么。然后,他們每個人也加了一份烤雞肉串。莫斯科來的同志把這一餐吃得杯盤狼藉,不亦樂乎,酒杯碰得鐺鐺響。服務員問他們,覺得波蘭菜怎么樣?
“Cheap!Cheap!”
走出餐館時,宋林不由感慨東歐乃至中歐國家的當代史,就是一部學習如何忍受俄國的歷史。
在柏林時,宋林曾碰到過一個格魯吉亞人。他說前兩年的冬天,因為政府拖欠了俄國一部分天然氣款,又頻頻向美國暗送秋波,俄國人憤怒地切斷了對格魯吉亞的天然氣供應。這之后,首都第比利斯的室內溫度降到了冰點以下,政府不得不把一車車木柴運往市區,任由市民們拿走燒火取暖。
“俄國人,very bad,”格魯吉亞人說,這讓宋林想到俄國歷史上最有權勢的人物斯大林也是格魯吉亞人,不過一切都時過境遷了。
宋林在等車處買了一個窩夫,果醬桶里爬滿了蜜蜂,但無論老板還是顧客似乎都毫不在意。過了15:15,車仍然沒來。按照站牌上的說法,下一班車是16:15,但宋林已經開始懷疑這趟巴士線路是否存在。
在這個漫長的午后,和宋林一起等車的只有一個瘦高的光頭男人,穿著短褲、船襪、球鞋,困獸一樣地在他眼前晃來晃去。
“你不會也去Zdiar吧?”宋林問。
“我去Zdiar。”
為免頭暈,宋林說服光頭男人在旁邊的椅子上坐下來說話。光頭男人說,他叫Armen,美國加利福尼亞人,定居華沙。宋林讓他重復了兩遍才搞清楚,他的名字和祈禱時說的“阿門”沒什么關系。他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父母都是俄國人——蘇聯人。冷戰時期,他們從蘇聯逃到美國,Armen和妹妹都是在洛杉磯出生的。
“他們是怎么從鐵幕下逃出來的?”
“很長很長的故事。”
總之,Armen的父親逃到了美國。他曾經是蘇聯的電影導演,但被政府剝奪了拍片的權利。到好萊塢以后,他做過一段時間演員,只能演冷戰電影里的俄國間諜。除此之外,他也開過店鋪,做過很多小生意,但生活始終都很艱辛。
Armen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在憂慮中去世,Armen和妹妹靠母親的微薄收入長大。所幸的是,他們在美國接受了教育,所以無論如何,總能到國外去教授英語,混口飯吃。
Armen否認是出于這個原因來到波蘭的。他說,18歲時他交的第一個女朋友是波蘭女孩,教了他很多波蘭語,也點燃了他心中深藏已久的斯拉夫情結。盡管后來他們分手了,Armen還是來到華沙謀求發展。
“華沙是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和洛杉磯一樣,非常現代。”Armen說。
他在波蘭生活了20年,娶了一位波蘭太太。5年前,他開辦了一個英語教學網站。“開始很難,入不敷出,”他說,但是憑借英語在波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網站流量終于越來越高,一些廣告商開始把產品廣告投放在上面。而且,凡是下載英語學習資料的用戶,也需要支付一筆費用。Armen雇了人,有了更多的閑暇時間。幾天前,他聽朋友說斯洛伐克境內的塔特拉山很好,于是決定獨自去那里徒步幾日。
盡管懂波蘭語,可是Armen也不確定這趟去斯洛伐克的鄉村巴士是否還在。沒錯,有站牌戳在這里,可在波蘭這并不能太當回事,它最多只表明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條巴士線路經過這里,但是沒人對它現在的命運負責。
Armen操著波蘭語問了幾個路人,得到了幾個截然相反的答案。正當他和宋林猶豫不決之時,一輛鄉村巴士像高中舞會遲到的校花一樣,翩然而至了。
“到不到Zdiar?”宋林大聲問留著八字胡的司機。
“到!You on the bus!”
就這樣,在一個波蘭的傍晚,宋林花了16茲羅提——32塊錢,坐在吱吱作響的座椅上,向著斯洛伐克,向著未知之地,飛馳而去!
一路上,奇峰異石隨處可見,綠色的山谷在眼前鋪展。透過窗玻璃,宋林看到一些波蘭農民面無表情地扛著農具,行走在山間,山腰上不時可以看見一些嶄新而漂亮的房子,那是富人們度假用的別墅。天空突然陰沉下來,雨點伴隨著山風,吹打在布滿塵土的窗玻璃上,流下一條條土色的淚痕。山石在雨水中變成了一種水墨畫一樣的黛青色。“我已經跨過了波蘭邊境,”宋林想,“如果一切順利,我可以在斯洛伐克的山村里享用晚餐。”
對宋林來說,這似乎就是人生的最好演繹:在黃昏時分,獨自到達異國他鄉的陌生之境——不是一本正經的首都,不是活色生香的都市,而是離他所熟知的世界幾百公里之遙的山村。在那里,日子簡單綿長,人民淳樸好客,因為從未見過中國人,因此格外熱情,如同歡迎遠道而來的大唐高僧。
巴士穿行在塔特拉山里,窗外到處是山毛櫸和冷杉,不時可以看見畫著鹿的標志牌。
宋林向車上的一個斯洛伐克人詢問附近是不是有很多鹿。
“到處都是,”斯洛伐克人說:“夜幕降臨以后,這里經常有鹿群經過。”
2
等到了Zdiar,暮色已經開始降臨。宋林和Armen被丟在空無一人的山路上。這時他們才意識到,Zdiar的確只是山間相對平坦的陡坡上的一個村莊而已。它看上去孤獨寂靜,放眼四望,除了森林和群山,再也看不到任何人跡。
這里沒有什么旅館,但是一些村民在門外掛出牌子,歡迎投宿。Armen在山腳下找到一家,但這家只有一間空房,接待能力有限。宋林說沒關系,他可以往山上走一點。他希望找到一家高處的房子,這樣透過窗戶,就可以俯瞰整座村莊了。
宋林沿著山路跋涉,經過一棟棟漂亮的房子。村子的古樸、靜謐容易給人一種荒涼感,可實際上這里并不貧窮,一些村民的庭院里甚至還停著德國和美國牌子的汽車。他經過村中的教堂,那里剛舉行過一場彌撒。一位神父從教堂里出來,經過宋林身旁時,對他說“感謝主”。宋林回答說“Amen”,并且想到他新認識的朋友Armen。教堂后面是一片墓地,豎著無數十字架,世世代代,村里的人們在這里生老病死,繁衍不息。沿著墓地向上走,宋林看到半山腰處有一棟房子,那是整個村子的最高點,如果住在那里,視野一定相當不錯。
宋林就走到那里去投宿。女主人剛剛翻新了房子,一切看上去都干凈明亮。宋林一個人擁有了一間舒適的屋子。站在陽臺上,可以俯視教堂和墓地,抬頭則是高大沉默的塔特拉山。宋林感到自己非常幸運,因為這一切只要15歐,而且女主人還打著手勢告訴他,這里新安裝了免費的WiFi。宋林想,即便在這里定居,他所需要的一切也都已經具備了。
這時他才感到饑餓,不過他決定先去找Armen喝上一杯。他下山,敲門,像俄國媽媽一樣的女主人告訴他,那個光頭的波蘭人已經出去了。他只好走回教堂墓地,因為他之前看到,在幾棵大樹的掩映下,這里有一個獵人小屋,掛著酒館的招牌。這是你能喝上一杯的地方。
宋林踏著滿地的落葉,呼吸著山里清新的空氣,一只拉布拉多犬飛快地向他跑來,圍在他的腿邊轉來轉去。它是那種可愛的小狗,對任何人都毫無戒心。宋林從兜里摸出一枚波蘭茲羅提,向遠處扔去,它飛跑過去,在地上左尋右嗅的。因為找不到,焦急地叫喚起來。
“別吵,史努皮!”一個年輕姑娘從掛在木屋外的吊床上喊道。
宋林跟她打了個招呼,她正看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看厚度,不是《罪與罰》就是《卡拉馬佐夫兄弟》。
“你好,陌生人,”她沖宋林一笑,“大家都在里頭。”
屋里,五六個外國人正圍在一張原木桌旁聊天,室內明亮溫馨,氣氛熱烈,墻上掛著抽象主義的油畫和照片,照片上是一副黝黑的麋鹿頭蓋骨。
“我看你是中國人,對嗎?”一個姑娘問,“旅途愉快嗎?”
“非常愉快。”
“從中國跑到這兒來?那可是夠遠的。”姑娘旁邊一個胖乎乎頗像大猩猩飼養員的小伙子說。
“你也夠遠的,不是嗎?”姑娘轉過頭說,然后又看著宋林,“我從澳大利亞來,他從美國來,我們是在路上認識的……”
“波羅斯島,希臘。我的錢包在那兒被人偷了。”
“于是愛情故事上演,美國小伙兒傍上了澳洲大妞,跟著她一路到這里,說這是羅曼蒂克。”一位從斯圖加特來的德國小伙子擠眉弄眼。他比像大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還胖,戴著一副古老的圓邊眼鏡。
像大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反唇相譏:“對于羅曼蒂克,我看德國人可沒什么發言權。”
大家哄堂而笑,德國小伙子紅著臉。
“嘿,你有過女朋友嗎?”像大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不依不饒。
“當然有過,我看上去有這么差勁嗎?”
“什么時候有的?”
“大學。”
“對方也認可嗎?”
大家又嘻嘻哈哈地笑起來。
宋林覺得氣氛不錯,就拿了瓶本地啤酒,在中間找了個凳子坐下。他旁邊是一個美國姑娘,大概28歲,淺栗色頭發,一副古靈精怪的樣子。宋林問她是做什么的。
“我是作家,”她一本正經地說,看上去一點都不像開玩笑。
“寫什么?”
“剛寫完一部長篇小說。”
“在哪里能看到嗎?”
“目前還在找出版社,”她瞇著眼睛,“你呢?你是做什么的?”
“scribble,scribble。”
她咯咯地樂起來。
“我也做點翻譯,”宋林說,“我剛翻譯了一本約翰·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說集。”
“真的?”她看上去頗為震驚。
宋林告訴她,他確實翻譯了。
她搖著她身邊伙伴的胳膊:“嘿,你猜我遇見了誰?我遇見了一個中國作者,他剛翻譯了厄普代克的小說。”
她身邊的小伙子是加拿大人,有一頭卷曲的短發,胡子刮得干干凈凈。剛才他一直趴在硬皮本上,修改一幅素描。
“哦?你翻譯了厄普代克!”他抬起頭說。他長得很像年輕時的艾倫·金斯堡,有一雙瘋狂的眼睛。他說自己是畫家,從巴爾干半島一路北上,常被路上的場景、人類的勞作感動得熱淚盈眶。每次這樣,他都畫一幅素描,記錄下自己的心情。
“一個多愁善感的家伙,”像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評論道。
可是,澳大利亞姑娘突然說:“我很羨慕你們這些作家、畫家什么的,我也遇到過很多打動我的場景,但我不知道如何表達。”
“比如什么場景?”畫家問。
“比如,今年春天我在尼泊爾的加德滿都。一天清晨,我走在霧中的杜巴廣場上,寺廟啊什么的看上去都模模糊糊。我聽到修行者誦經的聲音,但卻看不到他們。這時我抬頭,隱約看到天上有幾只鷹在翱翔。那一瞬間,我感到自己被打動了。”
“你知道嗎,你已經表達出來了,”美國女作家說,“而且表達得很不錯呢。”
“但我不會像你們一樣,把這種感覺寫出來或者畫出來。”
“重要的是感受而不是表達,”宋林說,“能用心感受到,旅行的目的就達到了。”
“他說得沒錯,”畫家說,“我同意這位中國同志的觀點。”
像大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打了個哈欠,澳大利亞姑娘則頗受鼓舞。她告訴宋林,5年前第一次出國旅行就是去的中國——北京、上海、西安、成都。她說她對中國的印象很好,人們很熱情,尤其對中國食物印象深刻。
“和我們平時吃到的中國菜不一樣吧?”畫家問。
“完全不同,我最喜歡的是火鍋,你們一定不相信,他們把一條魚放進滿是熱油和辣椒的鍋里。”
“天,不可思議!”
“是啊!”
宋林想,澳大利亞姑娘說的應該是水煮魚,可要把水煮魚和火鍋跟他們掰扯清楚,難度實在不小,于是只好任由他們保持錯誤印象。
澳大利亞姑娘有一副小巧俊俏的鼻子,臉上長著淡淡的雀斑。她感嘆自己5年前還是個年輕姑娘,如今和她同齡的姑娘們大都結婚生子。她說今天又在Facebook上看到一位大學好友舉行婚禮的消息。她很惆悵,不知道是否應該提前結束旅行,回去參加婚禮。
像大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側頭傾聽著下文。如果澳大利亞姑娘走了,他的前景將尤為堪憂。
幸好畫家把筆一摔。“我告訴你我的經驗,”他一副灑脫的表情,“你只需在那條Facebook狀態下點‘贊(Like)’,就萬事大吉了。”
這時,一直在吊床上看書的姑娘探進頭來:“你們不去吃飯嗎?”
于是,一行人動身前往村里的一家餐館。里面坐滿當地人,老板娘穿著傳統斯洛伐克女性的大裙子,忙里忙外。屋里擺著長凳,放著幾排桌子。他們把兩張桌子拼到一起,才勉強夠坐。宋林和澳大利亞姑娘點了特色烤鹿排,其他人點了澆有山羊奶酪和煙熏肥肉的餃子。
“你不來點肉嗎?”澳大利亞姑娘問像大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
“我倒是可以嘗嘗你的鹿排,”他撓了撓頭皮。
鹿排火候稍大,味道有點像馬肉,但宋林還是堅決地把它吃完了,而其他人都認為飯菜美味至極,由此可見東方和西方在味覺上的差別有多大。
宋林和美國青年女作家聊著文學,她說了幾個她喜歡的當代美國小說家,可惜宋林都沒聽說過。在她的暗示下,宋林留下了自己的郵箱,讓她發幾篇小說看看。這段時間里,像大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不僅吃完了自己的餃子,還吃完了半塊鹿排。
飯后,宋林爬山回到住處。對他來說,這一天顯得相當漫長。早上他還在波蘭,而此刻卻在斯洛伐克群山的包圍下。窗外天色已晚,萬籟俱靜。走到陽臺上,但見星光如沸。群山仿佛巨人的黑影降臨。宋林這時才發現,山在白天是一種壯美,在夜晚卻令人心悸。那種龐大而未知的存在,不分晝夜地永恒矗立,讓他感到自己的渺小和脆弱。

“如果山愿意,它可以輕而易舉地摧毀我,”宋林想,“如同汶川地震,而我此刻還活著,不過依賴于它的垂憐。”
宋林上網,看到微信上有個長久未曾謀面的姑娘問他在哪里。
“在斯洛伐克的群山里,此刻星光滿天,”他回復道。繼而可恥地向自戀傾向繳械投降,又頗為矯情地發了一條朋友圈:
“穿越波蘭邊境,進入塔特拉山,此地到處是山毛櫸和冷杉。一個斯洛伐克人說,夜幕降臨后,會有鹿群經過。我在想,可以把這句話作為新小說的開頭……”
3
第二天早晨,窗外下起了蒙蒙細雨。雨正以一種不聲不響的姿態下著,像舊電影膠片上一條條流竄著的白色直線,山上霧氣蒙蒙。
宋林打開電腦,看美國女作家發來的小說。她叫Eden Robins,住在芝加哥。寫作、旅行、學習外語,得過兩次瘧疾,賣過女性自慰器。看完小說,宋林就冒雨到獵人小屋找她。昨晚躺在吊床上看書的姑娘告訴宋林,他們都出去爬山了。
宋林走到村口的一家餐館,喝咖啡,吃午餐。他點了土豆煎餅配燉牛肉,煎餅上有熱乎乎的奶酪,用叉子挑起的時候會拉出長長的絲。他又點了蔬菜面條湯,為的是看看斯洛伐克的面條。結果上來的面條就像方便面的碎屑泡開以后的形態,口感也相似,不過湯很好喝。
吃完飯,雨已經停了,氣溫則驟降,空氣仿佛一塊濕布,能擰出水來。宋林穿上夾克,把領子豎起來,才感到暖和了一些。
他在村里隨意走著,看到一個斯洛伐克老人拄著拐杖,在自家門前的草坪上散步,她的狗沖宋林狂吠,老人呵斥它安靜。宋林走過去和老人搭話,但她聽不懂英語,只是目不轉睛又好奇地望著宋林,臉上布滿皺紋。宋林想她可能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過這個山村,就像很多中國山村里的老人一樣。
他朝山上走,經過自己的住處,然后順著坡路繼續往上爬。眼前是一塊起伏不平的高山草甸,遠方有幾只牛在靜靜吃草,旁邊是一輛拖拉機,而草甸盡頭又是無窮無盡的山峰。和捷克相比,斯洛伐克似乎一直這樣與世無爭。
宋林的雙腳被草上的雨水打得濕漉漉的,可這無所謂。他在心中暗自籌劃著之后的行程:他得乘車去離這里最近的城市波普拉德,再從那里搭乘開往布拉迪斯拉發的火車——這將是一趟從東到西橫穿整個斯洛伐克的旅程。他想到了Armen,他也在這里呆兩天,或許他們可以一起離開。于是宋林走到Armen的住處,給他留了張字條,然后寫下了自己的電話號碼。
宋林回到住所看書,此刻天空又變得陰沉沉的。直到夜幕開始降臨,他才走回獵人小屋。只有像大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坐在那兒,穿著短褲和T恤,像得了熱病一樣抖抖索索。宋林問他怎么不多穿點衣服。他說他根本沒帶長袖。
“我他媽的不知道歐洲的夏天也會這么寒冷!”
宋林又問其他人在哪里。像大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說,其他人都去村里的一家餐館吃飯了。
“你沒和他們一起?”
“我發燒了,”說完這句話,他的表情頓時顯得萎靡、虛弱。他告訴宋林,白天他一直躺在床上,沒有飯吃,沒有水喝,也沒有出門,“他們都去爬山了”。
“你現在餓了嗎?”宋林問。
像大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點點頭。
“那我們去餐館找他們怎么樣?”
“好。”
“你知道他們去了哪家餐館吧?”
他搖頭,一副聽天由命的表情:“村里就那么四五家餐館,我們可以挨個去看看。”
路上,像大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問宋林是怎么知道這個村子的。宋林說他的旅行指南上有半頁介紹。像大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說,他的旅行指南是老版,丁點沒有提到這里。
“哪一版?”
“1999年版。”
“那你為什么還要帶它?”
“我想地圖至少沒變吧。”
“好吧,” 宋林說,“斯洛伐克是1993年獨立的,之后地圖就沒變過了。”
他們先去了昨晚的餐館,沒人在。他們繼續走,下起了雨,空氣又濕又冷,宋林能聽到像大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牙齒打顫的聲音。他拐進一家pizza屋,建議就在這里吃飯。

“我要去找他們。”
“下雨了,我們沒帶傘,又這么冷。”
像大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搖搖頭,像處在一種迷幻狀態。
“我知道你錢包丟了,我可以請你吃飯,沒問題。”宋林說。
“不,我還是應該去找他們,” 像大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沉思著,“他們說不定就在下一個餐館。”
宋林試圖阻止他,可無濟于事。他還是冒雨走了。雨越下越大,宋林看見他抱著雙肩小跑著,像一只孤獨落難的小狗。
宋林點了一張大號pizza,喝了兩杯啤酒,給了好看的斯洛伐克女招待兩歐元小費。等他回到獵人小屋,大家都圍在桌旁,只有像大猩猩飼養員的美國小伙子不在其中。
“嗨!剛才雨下得真大!”他們跟宋林打招呼。
“你看到你男朋友了嗎?”宋林問澳大利亞姑娘。
“他在洗熱水澡——可憐的,剛才一直被雨困在樹下了!”
4
如果時間允許,宋林很想在Zdiar多住幾天,爬山,打獵。但是他不屬于這里,而且再美好的地方,也終須一別。
離開Zdiar那天,仍然下著毛毛細雨,昭昭的霧氣讓一切都顯得那么蒼涼。宋林和Armen坐在前往波普拉德的汽車上,它爬過巖石嶙峋的山崗,經過野草叢生的森林,一路上也見不到個人影兒。等他們好不容易進入平原地區,把山甩在身后,路邊才開始出現一些蒼白的舊房子。他們穿行在大片的莊稼地里,風擺動著莊稼,上面落滿了烏鴉,仿佛一幅梵高的油畫。一些農民站在路邊,但是看不到他們的表情。
大巴順著一條彎道,駛進一個小鎮,可以看到一些吉普賽人,穿著灰撲撲的衣服,戴著鴨舌帽,旁邊是同樣灰撲撲的房子,仿佛時間被凝固了,表針一直停留在過去的某一時刻上。
Armen說,他熱愛這種荒涼的感覺,這更容易讓他感覺到自己還活著。宋林告訴他,這地方讓他想起新疆,和哈薩克斯坦接壤的邊界地區。
“你去過那里嗎?”
“去過,有件事很有意思。”
那是很多年前的夏天,宋林一個人去新疆旅行。他坐的汽車在路上拋錨了,當時天色已晚,一車人不得不困守在車上,等待天明以后有人來救援。清晨時分,宋林終于攔住了一輛過路車,漢族司機跳下來說的第一句話是:“中國申奧成功了。”宋林愣在那兒,感到特別穿越,但還是很快反應過來,沖回車里告訴一車的維族人:“中國申奧成功了!”
“他們怎么說?”
“他們只是呆呆地望著我,不明白我在說什么。”
Armen笑起來:“就像在這里,就像這些吉普賽人。無論這里屬于捷克,屬于斯洛伐克,還是屬于匈牙利,對他們來說,都是無所謂的事情。”
“無論這里屬于誰,他們都必須臣服。”
多拿些酒來,因為生命只是烏有。
——費爾南多·佩索阿
到達波普拉德時,已近正午。這里就像中國西部的一座縣級城市。宋林和Armen喝了杯咖啡,在火車站分手告別。宋林將前往首都布拉迪斯拉發,而Armen將轉車去往另一個村莊。
“我們肯定會再聯系的。”
“一定會的。”
但他們彼此都知道,他們的人生很難再發生交集。旅行中的相遇,就如同空中交匯的流星,短暫的火花過后,依然是兩塊丑陋的隕石。人們期待旅途中的相遇,但相遇也注定了分離。
坐在火車上,宋林看到遠處的雪山閃閃發光。雪山和火車之間,是遼闊的斯洛伐克平原。他凝視著窗外,感到某種情感的重負,而他身邊的一位斯洛伐克大媽兀自埋首于報紙上的填字游戲。
宋林看到很多年輕的斯洛伐克人背著行囊和睡袋,立在站臺上。他們不慌不忙,悠閑自得。他們熱愛這片土地,熱愛在這片土地上游蕩。宋林在一本書上看到,游蕩(Ist’ na prechadsku)是斯洛伐克全民性的娛樂活動。在周末,在郊外,你會看到無數游蕩的斯洛伐克人。如今,在火車上,在他身邊,同樣站滿了背著睡袋的人。宋林第一次感到,他并不是一個孤獨的旅行者,而是浩蕩的游蕩大軍中的一員。
宋林將追隨他們,也很高興能夠追隨他們,和他們一起到達布拉迪斯拉發——一座幽靈之城,然后喝上一杯冰鎮的斯洛伐克啤酒。
是的,這樣很美好,宋林想。即便只是這樣想想,不也感到很美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