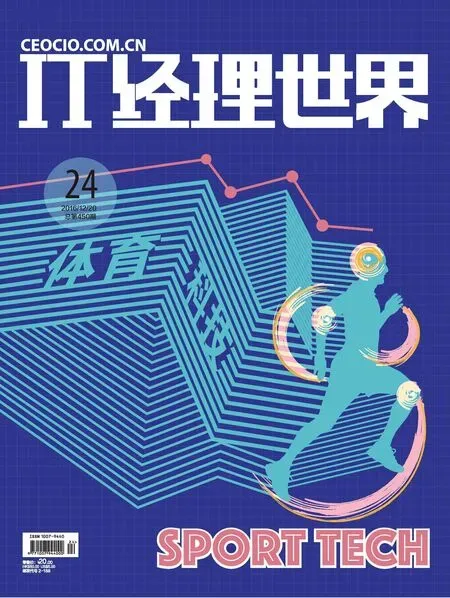均衡與秩序
胡泳+郝亞洲
哈耶克的均衡觀(均衡是人們計劃的兼容)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的供求相等。
在人行動的時候,競爭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過程。哈耶克嘲諷傳統經濟學的競爭理論,認為其競爭是被設計出來的,而競爭的真正價值在于結果的不可知。因此,競爭的本質是“一種發現的過程”(a discovery procedure)。競爭無法對特定的事實作出預測。比如,傳統經濟學的核心假設是“稀缺品”的供應,但是何謂稀缺品呢?哈耶克認為,這個答案唯有通過競爭才能夠發現。
哈耶克在《作為一種發現過程的競爭》一文中談到:“每個個人的特定技藝和能力的組合——在很多方面來看都極為獨特——并不只是(甚或首先是)個人能夠詳細列舉出來或向某個政府機構匯報的那種技藝。我所意指的知識,毋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種探明特定情勢的能力構成的。只有當市場告訴人們需要何種物品或服務,以及這類需要有多么迫切的時候,這種能力才能被個人有效地使用。”
正是因為個人知識的重要性,在自生自發的秩序中,才會有個人之間的對立,而這種對立來自于個人目的的不同,這種差異恰恰就是競爭所要服務的內容。也就是說,在一個自生自發的秩序之內,通過競爭,參與者的分立目的都會得以實現。
因此,哈耶克認為“秩序”比“均衡”重要。均衡是經濟學上的經典概念,圍繞什么構成均衡和如何界定均衡,均衡分析始終占據經濟學的主導地位。從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瓦爾拉斯均衡”,到“阿羅-德布魯”均衡,一直到目前已融入當代主流經濟學的博弈論中的“納什均衡”及“演進博弈均衡”等,不一而足。
哈耶克從知識的角度理解均衡概念。在《經濟學與知識》中,他指出:“均衡狀態的意思無非是說,我們可以設想,在特定條件下,社會不同成員的知識和意圖越來越趨于協調,或者用較為泛化、不那么精確但更具體的話說,人們、尤其是企業家們的預期將變得越來越正確。”他強調了預知概念,即在市場中,“所有知識都是讓人預測的能力”(all knowledge is capacity to predict)。他說:“均衡概念僅僅意味著,社會不同成員的預見是正確的。預見正確就是判定是否屬于均衡狀態的基本特征。”
標準的均衡理論假定所有的參與者都享有同樣的客觀正確的知識,而在現實中卻存在著知識分工。世界上實存的知識是分散化的;不同的人獲取不同的部分。同時,均衡對最終狀態的強調等于是認定事先的經濟活動已經產生了結果,而哈耶克卻認為:第一,均衡不是發生在靜態經濟中,而存在于動態經濟中;第二,均衡不是發生在某個時間點上,而是存在于時間過程中。
以秩序取代均衡
到20世紀60年代末,哈耶克已決定拋棄均衡這一概念,轉而使用他后期社會經濟理論的核心概念“秩序”。什么是秩序?在《法律、立法和自由》第一卷中,哈耶克對秩序所下的定義如下:“秩序,我們將一以貫之地意指這樣一種事態,其間,無數且各種各樣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是極為密切的,所以我們可以從我們對整體中的某個空間部分或某個時間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學會對其余部分作出正確的預期,或者至少是作出頗有希望被證明為正確的預期。”
那么,均衡分析與秩序理論的建構,孰優孰劣?哈耶克當然認為是后者。韋森總結說,按照哈耶克及其理論詮釋者的分析進路,秩序與均衡相比,至少有如下三個優點。
首先,正如哈耶克在上面一段話中所表露的那樣,均衡實際上是指一種最終狀態,而秩序則可指一個過程。這也意味著,一個彰顯某種秩序的體系本身就蘊涵,它自身正在經歷著一種自我轉型過程。由此可以認為,秩序可以長期駐存,而均衡即使存在,也往往是瞬間的事。同理,我們也可以認為,均衡只是一種理想狀態,而秩序則是一種現實實存。從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秩序是一般,而均衡則是特殊。
其次,正是因為秩序本身并不是涵指一種最終狀態,而是一種過程,哈耶克的演進秩序理論也就并不像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那樣是一種“最優理論”或“效率理論”。演進秩序正是哈耶克經濟學進路的一種長處。其實從更廣泛的角度說,演進(進化)貫穿了哈耶克的心理學、經濟學和社會秩序理論中,它與自生自發秩序理論緊密相連。杰拉爾德·奧迪斯科爾(Gerald 0'Driscoll)和馬里奧·瑞佐(Mario Rizzo)兩位論者在1985年出版的《無知和時間的經濟學》中總結道:演進秩序理論“并不是要說明競爭會完成我們的預期要求它所做的事,而是告訴我們不要期望競爭會做我們的預期要它做的事”。
第三,“秩序”和“趨于秩序”概念與“均衡”和“趨于均衡”概念,有一個根本區別。這就是,前一種趨向并不是趨于任何一種“最終的(最優)狀態”,而是趨于一種更好的“協調預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看出,哈耶克社會理論的精粹就在于他認為,市場秩序與命令經濟相比,其長處并不在于前者本身具有一種趨向于一種“唯一”和“穩定”均衡(即“帕累托最優”和諸如此類的概念)的能力,而在于前者有利于應用人們的“分散知識”和“默會知識”,從而更好地協調人們的經濟活動。
哈耶克進路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它令均衡遠離作為一種靜止狀態或力量平衡態的物理維度,而為其進入人的大腦打下了一個牢固的基礎。換言之,哈耶克的均衡觀(均衡是人們計劃的兼容)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的供求相等。協調(coordination)和預期(expectation),這是哈耶克均衡觀的兩個關鍵詞。當代奧地利學派掌門人伊斯雷爾·柯茲納(Israel M. Kirzner)這樣解釋哈耶克的觀點:“均衡狀態就是一切行為完美協調的狀態,每位市場參與者的決策都與他人嚴密契合,他可以(完全精確地)預期其他參與者會作出何種決策。均衡狀態定義中所包括的知識完備性假設,能夠確保個人計劃實現完全協調。”柯茲納接著說:“從非均衡走向均衡,乃是從不完備知識(imperfect knowledge)趨向完備知識(perfect knowledge)、從不協調趨向協調的結果。”
計劃得以實現,預期被證明是正確的,在這里,哈耶克完成了將“均衡”改寫為“秩序”的工作。從非均衡趨向均衡是溝通信息的過程。因而,秩序本身是一個信息收集過程,它能夠使廣泛散布的信息公之于眾并得到利用。而這些知識不用說哪個個人,即使是任何中央計劃機構,也是無法全部知道、占有或控制的。人們沒有必要在統一目標上求得一致,因為廣泛分散的知識隨時可以滿足不同的目標。
放棄了中央控制,“配置資源的權力以可以變化的方式分散在許多能夠實際決定這些資源用途的個人手里——這種分散是通過個人自由和分立的財產做到的——才能使分散的知識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中如此說道。
鑒于知識的個人化,個體的差異化越大,通過合作讓其發揮力量的可能性就越大。讓結果發生的是知識,但不是一個中央控制的大腦,也不是某個具體的人,而是一個競爭性的過程,也就是在秩序之中。秩序中的構成要素越復雜,就會呈現出越大的多樣性,居間范疇的擴展就會越廣袤。哈耶克建議,“個人能夠加入復雜的合作結構之前,必須變得與眾不同。進一步說,他們還必須結成一個性質獨特的實體;它不僅僅是個總和,而且是一個結構。”
哈耶克順便諷刺了一下企圖追求已知的、可觀察的目標的群體,說他們是“小家子氣的倫理學的殘留物”。在管理學上,這句話恰好可以作為對所謂“戰略規劃”學派的反動。
在現實中,并非所有自生自發秩序都會成功,他們的失敗在哈耶克看來是因為遭到了干預。秩序一旦被誘發,就不可以被干預。所謂的“計劃經濟”是不合理的,個人知識隨著秩序的擴展而越發顯得渺小,任何人都不可能預知結局,更不要說做出合理規劃。知識之間進行組合,可以解決局部認知的問題,從而出現全新的經濟增長點。但是,這類組合是不可能長盛不衰的,因為知識始終處于分散和變化中,興亡更替不可避免。因此,均衡狀態是不可能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