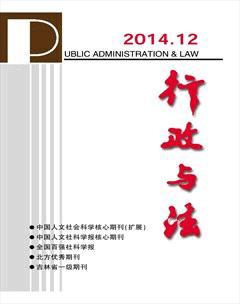監獄傳統政策目的之檢討
李蕾,于飛
摘 ? ? ?要:監獄是人類社會文明的鏡子,它既是文明產生的標志,也反映著社會最丑陋的現象。長期以來,監獄承載著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政策目的,但不斷上升的犯罪率和監獄的人滿為患促使社會開始反思:監獄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落實刑事政策目的;監獄面臨的現實困境;如何面對、認識和運用監禁刑等等。本文在對監獄所遭受質疑進行全面分析的基礎上,對監獄的傳統政策目的進行了反思。
關 ?鍵 ?詞:監獄;一般預防;特殊預防;行刑成本
中圖分類號:D926.7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7-8207(2014)12-0104-06
收稿日期:2014-09-20
作者簡介:李蕾(1985—),女,江蘇徐州人,復旦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國際刑事司法;于飛(1983—),男,遼寧本溪人,復旦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國際刑事司法。
刑罰是犯罪的邏輯結論。刑罰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任何對應于犯罪的刑罰都需要依托于一種特定的方法,體現特定的政策目的。早期的刑罰方法體現的是單純的報應與復仇,源起于人類對待罪惡的樸素的道德情感。隨著刑罰制度的不斷演進,在控制與預防犯罪的歷史環境之中,以剝奪人的行為自由為主要手段的監禁刑逐步演變成為主導性的刑罰方法。相應地,人類社會也賦予了監獄重要的政策目的:一方面,通過監獄對罪犯進行隔離和教育,實現特殊預防目的;另一方面,通過強化監獄的威懾功能,實現一般預防目的。然而,監獄在歷經幾百年的實踐后,全球范圍內的“罪與罰”問題陷入了一個“怪圈”,即監禁人數越多,犯罪人數就越多;犯罪人數越多,監禁人數也相應增加,監獄愈發人滿為患。有鑒于此,人們逐漸發現,過度依賴監獄的矯正預防作用、過度迷信監禁的威懾功能和改造能力,是一種陳舊理念引導下的政策失誤,其社會效果值得懷疑,因此應當重新加以認識。
一、監獄的一般預防功能面臨挑戰
一般預防論著眼于刑罰的痛苦性,認為刑法的基本功能是將刑罰的痛苦預先公告于社會,并且利用該公告的威懾作用形成社會的心理反射,從而達到普遍預防犯罪的目的。在長期的演變發展過程中,監獄逐步承載了一般預防的政策目的,成為對全社會進行心理強制的物理載體。令人遺憾的是,監獄的現實威懾效果卻與監獄的理論設計初衷背道而馳:按照樸素的觀念,如果監獄一般預防功能可以發揮作用,那么監獄關押人數越是龐大,其心理強制作用越明顯,犯罪率也理應降低。但現實的監禁實踐卻恰恰相反:1970年-1975年,全球平均犯罪率為900/100000;1975年-1980年,全球的平均犯罪率上升至1300/100000。[1]2000年-2010年,全球平均犯罪率已上升至3000/100000以上。[2]我國的刑事犯罪總數,1978年為50多萬起,1990年突破200萬起,2001年達400萬起,2005年犯罪總數為468萬多起。近5年來,犯罪總量雖出現過小幅下降趨勢,但總量均高于450萬起之上。[3]以上數據說明,一般預防理論和威懾刑思想“企圖以有限和不變的刑罰資源來應對無限和變化的刑事犯罪,這必將以失敗告終”。[4]對此,筆者認為,監獄對于絕大部分罪犯來說既沒有預防功能,也沒有鎮壓效力,這是監禁本身不完善以及錯誤的理論所形成的后果。也就是說,刑罰對社會的作用力存在著明顯區別,對監獄威懾功能的期待同面對威懾的社會公眾的價值觀念與規范意識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關聯系。就連當代最著名的一般預防論者安德聶斯也承認,“刑罰不可能對所有人都產生一般預防的效果”,“即使事先知道犯罪將遭受刑事制裁,在行動時也忘乎所以,不顧一切地犯罪”。[5]也就是說,在行為人的理性不足以使其通過合法行為規避刑罰的情況下,在行為人的價值觀念中還有比被判死刑更為重要的問題上,行為人唯一的途徑就是通過提高犯罪的惡性來得到心理上的補償。①更何況監獄中服刑的痛苦只能使直接受刑者受到威懾。換句話說,刑罰的直接作用并無直接針對非犯罪人的實際價值,希望通過刑罰的直接作用來預防非刑罰承受人的犯罪,只是邏輯上的推論,刑罰威懾的合理性無法得到科學的解釋,而刑罰威懾的真正效果則很難得到實踐的證明,并且沒有證實的有效途徑。
二、監獄的特殊預防功能遭受質疑
所謂的特殊預防,指的是通過刑罰的具體適用來防止犯罪人再次犯罪的特殊目的。特殊預防論特別關注犯罪人,將已經實施了犯罪并且已經接受刑罰宣告的行為人視為刑罰預防的唯一對象。具體到監獄的問題上,監獄較好發揮特殊預防功能的主要指標就是重新犯罪率②的下降。重新犯罪率的高低,體現著監獄特殊預防功能發揮的好壞,是監獄功能的“晴雨表”與“風向標”。但現實中,“再犯蔓延”的現象卻與監獄所承載的政策目的背道而馳。
(一)發達國家重新犯罪率的居高不下
根據美國司法統計局90年代的調查:罪犯刑釋后3年,美國重新犯罪率為46.9%,其中51.8%的人重返監獄。2006年,英國的重新犯罪率是57.6%,③法國為50%,日本為57.2%,原聯邦德國為62%。[6]1990年美國監獄中的罪犯是748000人,重新入獄人數是467000人;2000年監獄中的罪犯是l357000人,重新入獄人數是728000人。[7]另有數據顯示,全美2000年有600000名罪犯出獄,其中有67%的罪犯在釋放后3年被捕;有30%的罪犯在釋放后半年內被捕;有47%的罪犯在釋放后3年內因重新犯罪而被定罪;有25%的罪犯在刑滿釋放后3年內因新罪而重新被量刑。[8]據新西蘭懲教署1998-1999年度報告顯示:新西蘭罪犯釋放后24個月內重新犯罪及被判刑的比率為80%;加拿大57%;英格蘭56%;澳大利亞37%的罪犯獲釋后36個月內再犯重罪;日本(1990-1994年)42%的在押犯人為累犯。[9]由此,發達國家的重新犯罪率之高可見一斑。
(二)我國重新犯罪率的不斷攀升
據資料顯示,我國刑滿釋放人員的重新犯罪率,1982到1986年5年間平均為5.3%左右。[10]到上世紀90年代,我國重新犯罪率始終保持在8%左右。1992年《中國改造罪犯狀況白皮書》公布的重新犯罪率是6%-8%。有分析指出,1984到1990年重新犯罪比較增長了2.2%;1990到1996年重新犯罪比較增長了2.55%點,1996年重新犯罪率是11.10%。[11]1996年后,無全國范圍的權威統計,但從相關省份公開的數據看,近年來我國重新犯罪率仍持續走高。如湖北省1997-2000年重新犯罪比重分別為17.9%、21.1%、19%、23%,而山西省2000年重新犯罪率也上升到13.47%。[12]這些數據足以說明,監獄的威懾力越是強大,犯罪的惡性程度越是嚴重;監禁刑的覆蓋范圍越大、行刑時間越長,犯罪涉及的領域越是廣泛;監獄內有利于累犯的因素越被控制,重新犯罪率卻成反比增長。
(三)重新犯罪率與監獄功能
政策真正價值在于體現時代的要求。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累犯率迫使社會反思:監獄能否擔負起威懾犯罪和減少累犯的任務?刑罰的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功能能否有效發揮?理論上的經典假設和現實中犯罪的爆發性增長為何呈反比關系?監獄究竟應當承載怎樣的理論使命,又應該實現怎樣的現實目標?關于這一問題的答案,實證主義學派代表人物龍勃羅梭早在幾百年前就對監獄功能進行了論述:“監禁除了對偶發性犯罪人尚能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外,對于其他犯罪人來說則根本沒有什么意義。”
三、監獄服刑引發特定負面效果
監獄非但未能有效實現相關理論的期待,反而引發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這一系列的連鎖負面反應使監獄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人類社會“惡”的集散地,成為刑事司法不可忽視的因素。
(一)監獄引發罪犯之間的交叉感染
集中關押導致惡性觀念的傳播和犯罪技術的交叉。無論如何嚴格地貫徹分類制和累進制,監獄內的交叉感染是難以避免的。在監獄里,罪犯要么學會新的犯罪手段,要么強化實施犯罪的惡性,①要么增強反偵查能力,除非實施絕對單獨監禁。但絕對單獨監禁卻違背了監禁的最基本原則,因為監獄必須給罪犯留有一定放風和共同作業的時間。意大利犯罪學家龍勃羅梭認為:“應當弱化監獄在刑罰執行中的地位,監獄幾乎起不到矯正犯罪的目的。監獄是犯罪的學校,它教人實施最有害的犯罪和團伙犯罪。”[13]
從犯罪人的角度分析,高智能犯罪寥寥可數,監獄內絕大部分罪犯是社會底層,此類人員被監禁在一起,不可能討論具有積極意義的事。正如龍勃羅梭所言:“拘禁生活使犯罪人遠離了社會的良好事物,遠離了藝術、科學等人類高尚的東西,使得本來就比較惡劣的人更加滋生出做惡事的欲望”,僅能交流犯罪方法,提升反偵查能力。“監獄里,犯罪人充滿相互熟悉的機會,充滿學習和訓練自己還不甚熟悉的犯罪手段的機會。”[14]歷史上,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監獄都存在著交叉感染,監獄因此被龍勃羅梭稱為“犯罪的大學”。在某種意義上,這就是近代監獄的宿命。
從監獄角度分析,在獄內犯罪人這一特殊群體中,犯罪成為“合理”,對犯罪的恥辱感不復存在。相反,這一特殊的“場”會使場內的人對犯罪產生認同,普遍感到犯罪是社會造成的,而非其本身的問題,進而集體仇視社會。正如有學者指出,“把犯人帶出正常社會并將其置于到處是罪犯的異常社會中去,并以此希望他們(在釋放后)能適應社會,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邏輯的。”[15]此外,監獄管理者一般都漠視罪犯的尊嚴,罪犯人性將不斷麻木,這使得監獄成為社會中“惡”的源泉。
(二)監獄生活使罪犯難以順利回歸社會
對犯罪人而言,監獄帶來的最嚴重的負面傷害就是人格上的“監獄化”傾向。[16]監獄亞文化不可避免的會助推服刑人員監獄人格的養成。也就是說,“對監獄亞文化的適應程度會直接影響到犯罪人待遇。罪犯改造、監獄管理的各項制度準則在監獄亞文化的作用下,不僅不能矯正犯罪人,相反卻有可能成為更糟糕的人格的塑造平臺。”[17]這種人格是犯罪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比如獲得更高的服刑待遇或者為了縮短刑期而表現出的表里不一的虛假人格。日本監獄學據此將適應監禁生活、能夠獲得優越待遇的犯罪人戲稱為“刑務所太郎”。②從另一個方面講,監獄具備強大的“負面標簽作用”:一是刑滿釋放人員被社會公眾看做“異類”,存在著偏見、歧視的社會情緒;二是犯罪人自身的自我認同上由內而外的產生排斥,進而仇視且不愿融入社會。這種“標簽作用”使罪犯喪失了再社會化的基本條件,回歸社會后障礙重重,難以適應社會生活,更容易被社會淘汰。
總之,在監獄行刑始終面臨“獄中封閉式”和“獄后開放式”的矛盾、獄中“阻斷社會化”和出獄“再社會化”的矛盾。過度相信、依賴監獄的矯正功能是一種落后刑罰觀念指導下的政策偏差。正如有學者所指出:“將一個人關押在高度警戒監獄里數年之久,告訴他每天睡覺、起床的時間和每日每分鐘應該做的事情,然后再將其拋向街頭并指望其成為一名模范的公民,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18]
(三)“監獄等同于痛苦”的邏輯假設被獄內人群的替代功能所否定
監獄設計初衷是通過將罪犯與社會隔離,以此給罪犯帶來痛苦。這一設計本身在邏輯上沒有問題,但在行刑實踐中卻弊端盡顯。監獄切斷了罪犯固有的社會關系,但卻立即在獄內形成新的社會關系——獄友關系。這一特殊社會關系的替代性很強,使監獄的隔離功能大打折扣,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罪犯的痛苦。換言之,盡管獄內飲食起居條件較差,但罪犯既能享受充分的閑暇又能與同類相伴,“這就使監獄成了一部分犯罪人的安樂窩,成了犯罪的溫床”。[19]這一點再次驗證了龍勃羅梭的預測:“用監禁把犯罪人同家屬、親友等隔離的方法,對于本來就沒有正常的親友感情的人來說,并不意味著嚴厲的懲罰。”
人群的強大替代功能導致監獄教育、改造、懲罰功能的弱化,具體表現為:監獄服刑人員的再犯率、累犯率是所有刑罰中最高的。相比之下,財產刑的再犯率、累犯率極低,因為財產的剝奪使罪犯感覺到切膚之痛。
(四)監獄與社會容忍度之間的摩擦不斷加劇
從理論上說,監獄應建在城市的邊緣,而非遠離城市的郊外,以發揮監獄的威懾作用。但隨著當今監獄數量的不斷增加,政府面臨著監獄選址問題上的巨大難題。也就是說,在社會可容忍性的范圍內,單純依靠增設監獄的方式來解決監獄人滿為患弊端的傳統做法,面臨著迫在眉睫的變革。目前,監獄的擴容現象已經超出了社會的容忍度,監獄人數的增長與城市本身人口增長的比例已經明顯失調。對此,政府只能通過增加監獄監禁量來收容不斷龐大的服刑人員。如果說在中國,因為土地國有,政府平衡土地關系不會發生問題,因而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那么在美國、法國、德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民眾會提出嚴重抗議,而私權保障的嚴密法網使民眾的抗議訴訟很可能勝訴,這無疑給監獄建設帶來障礙。
四、監獄人滿為患,行刑成本較大
隨著監禁人數和判處刑期的不斷增加,監獄系統運行所需要的行刑成本居高不下,監獄給社會造成了極為沉重的財政負擔。一方面,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不能接受監獄過于巨大的行刑成本,另一方面,各國雖不能接受但又不能減少或回避這一開支。
(一)監獄羈押人數不斷增加
由于犯罪總量的持續攀升和監獄的過度使用,全球范圍內許多國家監獄在押犯人數持續增長。據統計,當前,全球范圍內監獄服刑犯共有920萬人。其中,美國在押的人數為230萬,占全世界在押人數的1/4。我國的在押人數占全世界的15%。[20]以上數據反映出一個極為龐大的監獄財政預算,監獄消耗已經并將繼續消耗大量的社會資源。
監獄人滿為患是許多國家監獄面臨的現實問題。例如,美國在1990年至1998年間,平均每年入獄人數比上年增長63144人,年增長率為6.7%。1998年底,已有30個州報告監獄人滿為患,共有24925名州罪犯被迫在當地看守所或其他機構關押。[21]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現有33所監獄只可關押約8萬人,但卻實際關押著15.6萬人,每名犯人平均生活面積僅為6平方英尺。[22]在英國,1950年至1980年間新建了24所監獄,1980年至今新建了22所監獄,監獄平均造價約為10萬英鎊,但仍跟不上罪犯數量的持續增長,2003年就有7.2萬人關押在137所監獄,達到關押飽和狀態,[23]人滿為患現象引發了1972年的布里克斯通監獄大騷亂。法國監禁數量同樣持續增長,1994年4月,法國在押犯人數首次突破57000人,在司法部向議會提交的法案中,把該問題視為監獄最嚴重的問題。[24]此外,意大利也面臨著監獄人滿為患的窘境,其205所監獄關押著6萬多名罪犯,但其監獄法定容量為4萬人。[25]在我國,1997年監獄羈押量已達142萬,當時超監禁負荷近40萬。[26]1997年第三季度,我監獄押犯總數為143.1萬人,而當時全國監獄的關押能力只有110萬人左右,超押33.1萬人,超押率為30.09%。[27]2000年底,全國720所監獄押犯為144萬人,超押24萬人,超押率為20%。2002年底,全國在押犯達到150萬人,監獄擁擠的狀況更加嚴重。[28]
(二)監禁單個犯罪人的高昂成本
隨著人權保障事業的不斷發展,《世界人權宣言》、《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囚犯待遇基本原則》等系一列國際法文件構筑了一整套囚犯權利保障體系,這一方面是囚犯待遇標準不斷向前推進,另一方面是獄內服刑犯人的監禁成本不斷提高。有統計指出,監獄關押一名罪犯的平均成本是偵查一個案件的10倍。①
根據聯合國在全球范圍的統計,監禁成本最高的是北愛爾蘭,關押一名罪犯的平均年開銷約為12萬美元;其次是荷蘭,為8.5萬美元。經聯合國統計,1994年平均每一個罪犯的監獄開支大約在3-4萬美元;①英國平均每個罪犯為2.77萬英鎊每年;西班牙平均每個罪犯為1.38萬歐元每年。我國監禁一名罪犯的平均費用接近2萬人民幣每年,[29]以我國在押犯150萬人計,[30]總監禁成本可想而知。正如意大利犯罪學家加羅法洛指出的:“罪犯們什么也沒有付出,而社會卻為他們支付生活費,納稅人也增加了一種新的負擔,增加了社會受到的侵害。”[31]
單個罪犯的監禁成本并非靜態的、統一的,而是不斷攀升且因人而異的。一方面,隨著人權保障水平的提升,單個囚犯的監禁成本也在不斷提升。以美國為例,1991年,每名在押犯每年約花費19萬,而2009年度每名在押犯每年花費上升至約29萬,上升率達53%,[32]其消耗的司法財政資源可見一斑;另一方面,隨著罪犯人身危險性和健康狀況的不同,不同監獄的安全警戒費用也存在明顯區別。以美國為例,一張最低警戒度監獄床位的平均建設費用為30752美元;中等警戒度監獄床位為51299美元;一張最高警戒度監獄床位為79770美元。[33]此外,老年犯、病殘犯的監禁保障費用更高。在美國,關押60歲以上犯罪人的費用平均為69000美元。[34]
(三)監獄系統整體運行消耗的巨大社會資源
承載龐大監禁人數及配套警戒、保障措施的監獄,其整體運行需要消耗巨大的財政資源。就近年來監獄行刑領域的財政支出而言,美國每年用于矯正罪犯的開支達200億美元,[35]法國司法部約為200億法郎,[36]英國2002年監獄經費預算高達20億英鎊;[37]西班牙監獄經費預算2002年增至7億歐元;[38]日本監獄系統的年開銷約為2100億日元至2500億日元。[39]在我國,2000年全國監獄系統總支出為122.33億元,財政撥款為88.23億元;2001年全國的財政收入是16000多個億,監獄決算是實際執行144億,[40]但仍遠遠不能滿足全國監獄運行所需。
監獄整體運行所需的財政資源并非固定不變,隨著監獄內人數的進一步擴大及監禁刑期的延長,大部分國家監獄的財政支出不斷提升。美國量刑改革委員會曾于2012年8月7日發布過一份報告,該報告顯示出近年來美國監獄整體費用的上漲趨勢。1991年,美國聯邦監獄人口數為71608人,監獄開支13.6億美元;2009年,監獄人數為208188人,聯邦監獄運行開支60.9億美金。2009年,美國總預算僅4萬余億美元;2009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為129903億。[41]
隨著監禁人數的不斷增加,監獄系統的整體運行還需支出巨大的新建、擴建費用。有統計顯示,德國近年來用于監獄建設的支出高達25億馬克(約12.5億美元),用于擴大監獄的容量;法國財政支出35億法郎(約8億美元)新建了7座監獄、擴容了5座監獄。[42]
(四)監獄消耗極大的機會成本
“在具有稀缺性的世界里做出的一個選擇要求我們放棄其他事情,實際上,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做其他事情的機會。”[43]這就是所謂的機會成本。一般而言,付出的機會成本越小,行刑效益越高。在行刑領域內,監禁刑的適用使得其他刑種無法得以適用;監獄建造費用的消耗使得其他公共事業無法開展;監獄的選址使得其他機構無法在特定地域發生社會效益。而當其他行刑方式、其他社會事業、其他統一地點的建筑得以發揮更大的社會效益時,監獄行刑的機會成本相應提高。
馬克思曾經說:“犯罪的概念本來就包含懲罰的意義。”這里的刑罰主要是指監禁刑。在傳統觀念中,罪和罰被看作是因果現象,被看作是相互作用的關系。但到了當代社會,特別是在惡性膨脹的犯罪率和新型犯罪層出不窮的治安形勢面前,監獄切切實實地存在著無能為力的弱點。在法現實主義看來,既然社會耗費巨大的代價所維護的監獄最后卻成了影響社會發展的障礙,那么否定這種刑罰的要求當然有益于社會,也就毫無疑問地有利于司法制度的健康發展。根據我國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中心統數字顯示,2000年,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對罪犯適用緩刑和假釋的比例達到全部被判處刑罰者的70%以上,其中加拿大為79.76%,澳大利亞為77.48%,新加坡為76.15%,法國為72.63%,美國為70.25%。即便是比率較低的韓國和俄羅斯,也分別達到了45.90%和44.48%。[44]
鑒于此,“犯罪的概念中本來就包含著監禁”的制度需要進行變革,因為其明顯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也就是說,以非監禁刑替代監禁刑是大勢所趨。換言之,非罪化、輕罪化、非監禁化和非刑罰化是當今國際社會降低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益的唯一出路。可以說,這一結論既是“人非手段”的道德底線的基本要求,又是法追求的增進人類自由的使命擔當;既是法經濟學對于有限司法資源最大化利用的必然要求,又是刑事政策遏制犯罪的理性選擇;既是寬容異端,體現刑法謙抑性的具體舉措,又是實現罪犯順利復歸社會這一行刑目的的必要手段。
【參考文獻】
[1]Mark Shaw,Jan van Dijk,Wolfgang Rhomberg,Determining Trends in Global Crime and Justice,Forum on Crime and Society,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Numbers 1 and 2,December,2003,p.40.
[2](德)漢斯·約阿西姆·施奈德.犯罪學[M].中國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240-241.
[3]陳屹立.中國犯罪率的實證研究:基于1978—2005年的計量分析[D].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08.
[4]陳浩然.反洗錢法律文獻比較與解析[M].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4.
[5](德)安德聶斯.刑罰與犯罪預防[M].鐘大熊譯.法律出版社,1983.65.
[6][11]劉玲玲,王嘉.略論重新犯罪原因[J].前沿,2005,(06).
[7]翟中東.關于出臺完善重新犯罪預防政策出臺機制的思考[J].犯罪研究,2010,(05).
[8][28][33][34]陳衛軍.論行刑成本控制[D].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03.
[9]2002年監獄工作取得重大進展[J].中國監獄,2003,(01).
[10]喜文.刑滿釋放回歸社會理論研討會文集[C].中國監獄學會,2000.28-29.
[12](意)龍勃羅梭.犯罪人論[M].黃風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349.
[13](日)寺田精一.ロンブロ﹢ゾ犯罪人鍝[M].巌松堂書店,1917.60.
[14][17][18](美)克萊門斯·巴特勒斯.矯正導論[M].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1.8,33,8.
[15][16]J.Reicher,Psychoanalytically Oriented Treatment of Offenders Diagnosed as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s, Law and Psychiatry,Vo1.2,1999,P.86,88.
[19]美國囚犯 世界第一[N].新快報,2011-10-09(B03).
[20]張文.人格刑法導論[M].法律出版社,2005.240-241.
[21][44]楊帆.我國監獄服刑人員權利保障研究[M].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51.
[22]王戌生,盂憲軍.英國西班牙監獄考察報告[J].犯罪與改造研究,2003,(03).
[23]陳正云.刑法的經濟分析[M].中國法制出版社,1997.1.
[24]周國強.社區矯正制度研究[M].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76.
[25]杜強.監獄行刑社會化:現實與必然[J].上海警苑,1998,(08):20.
[26]陳志海.監獄擁擠問題芻議[J].犯罪與改造研究,1998,(01).
[28][37][38]劉興華.基于監獄行刑效益和特殊預防視角的監獄循證矯正[J].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13,(06).
[29]2004年的國際矯正與監獄協會第六屆年會上司法部副部長范方平的講話[EB/OL].http://news.sohu.com/20041026/n222695241.shtml,2014-08-22.
[30]加羅法洛.犯罪學[M].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9.
[31]See The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Letter to Congress on Rising Costs of Incarceration[EB/OL].http://www.USSC.gov/Legislative_and_Public_Affairs/Congressional_Testimony_and_Reports/Submissions/20120807_StC_Prison_Costs.pdf, last visit on January 4,2013.
[34][35][36][39][42]于秉中.對輕罪犯非崎禁化——西方行刑制度的一個趨勢[A].夏宗素,朱濟民.中外監獄制度比較研究文集[C].法律出版社,2001.171-177.
[40]國務院第17次總理辦公會議紀要、國發[95]4號文件、2001年國務院《關于研究解決監獄困難有關問題的會議紀要》,轉引自.監獄學家與經濟學家對話[J].犯罪與改造研究,2003,(02).
[41]See The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Letter to Congress on Rising Costs of Incarceration,http://www.USSC.gov/Legislative_and_Public_Affairs/Congressional_Testimony_and_Reports/Submissions/20120807_StC_Prison_Costs.pdf, last visit on January 4,2013.
[43]薩繆爾森.經濟學[M].胡代光等譯.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1996.48.
(責任編輯:王秀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