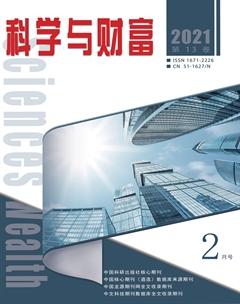淺談城市給排水工程施工及管理
陳亮
摘 要:在中國的城市建設中,確保城市經濟建設與人民群眾平常生活的基礎是城市給排水工程,城市基礎實施越來越完善的關鍵標志是給排水系統的合理規劃和建設。所以,在給排水項目施工的時候,管理就變得非常關鍵。在項目施工中,排水工程整體作用可不可以有效的發揮主要由可不可以達到施工管理的預期目標來決定的。所以,增強城市給排水工程施工的管理就變得非常重要。
關鍵詞:城市給排水;工程施工;管理要點
1、引言
在城市建設的時候,城市經濟建設和居民生活水平要通過市政給排水工程的建設來提高,城市基礎設施因為合理規劃和建設也漸漸的提高了。所以,在給排水項目施工的時候,最為關鍵的就是管理。在項目施工中,可不可以達到施工管理的預期目標,肯定會影響到給排水項目整體功能的有效發揮。所以,增強市政給排水項目施工的管理是特別重要的。
2 、市政給排水工程施工管理的必要性
在人們的生活中市政給排水項目占有非常大的作用,對于正常生活、日常辦公等都是市政給排水系統中關鍵的組成部門,很多都是在地下的位置,如果是無法合理的進行管理,就會發生較大的工程問題,如此就會關系到非常多行業的正常工作。相對嚴重點的影響就會有嚴重的后果,部分安全事故的出現也是有因素的。此外,在后期的維修中,也是比較繁雜的,需要相對長的時間去修復。建設市政給排水的項目是相對復雜的,而且具備必然的特殊性。如果是無法合理的管理,就會發生部分項目質量的問題,如此就會影響到人們正常的生活。所以,在市政給排水的質量問題中有效的控制是特別重要的,我們要嚴格的控制市政給排水項目的施工管理,而且實施有效的施工管理。
3、城市給排水工程施工管理要點
3.1圖紙的規劃和設計工作
施工圖紙的設計和規劃是進行工程建設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其是保證工程正常開展的先決條件。在進行給排水管道設計規劃時,首先要結合國家建設的具體要求進行現場的實地考核,保證設計圖紙的準確性和合理性;其次,對施工中所需的材料進行充分的了解和掌握,確保施工材料的質量與標準規范相符合;最后,對施工中涉及到尺寸和規格進行精確的測量和計算工作,確保其準確性,以提升工程建設的質量,加快施工的效率。
3.2放線測量與溝槽的開挖
對城市給排水工程施工而言,總體施工均應當給予測量。所以,測量數據的正確性成為確保工程施工品質的主要方面。如果在測量數據時具有誤差,則會令施工質量備受影響,甚至會產生倒坡的狀況,所以在施工前應當融合設計圖紙在施工現場給予數據測量,保護測量的數據點,確保工程能夠正常運轉。在施工當中,測量點不可以任意給予更改,謹防其會對管道的正常鋪設造成影響,在施工當中一旦具有建筑物,則應當盡可能規避,再通過設計人員給予修改。并且,在排水施工當中,溝槽開挖成為工程施工的關鍵工序,在施工中應當融合當地狀況挑選適宜的方式以及位置給予開挖。還應當測量周遭的土質以及水位,挑選適宜的位置給予施工。并且,土方與開挖處的間距應當控制在80cm區間,如此才不會發生地下水滲漏的情況。
3.3加強對檢查井施工的質量控制
在城市工程建設的過程中,檢查井是一項常規的設施,在給排水系統、電氣系統以及通信系統中都普遍使用。檢查井在使用的過程中,具有針對性強的特點,因此,給排水管道檢查井施工時需要和溝槽以及支護同時施工,對其尺寸進行嚴格的控制,保證其施工的質量。在檢查井施工的后期,根據工程的質量進行評估,保證符合工程施工的標準。
4、提高給排水工程施工安全和質量的措施
4.1建立健全給排水工程施工安全質量保障體系
落實管理責任制制定給排水工程建設的各項管理制度,對工程施工合同簽訂、材料選型定樣、項目人員確定、工程施工管理、工程竣工驗收等實施全方位、全過程管理。對各個環節的施工質量進行跟蹤管理。建立給排水工程的施工質量管理責任制,相關施工監督部門要派專業技術人員對給排水工程施工中的各環節質量進行監督,將各個環節的施工質量工作進行拆分,把施工質量的管理責任追究到個人。加強監督部門的質量監督及處罰力度。此外,在工程項目招標時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相關建筑招投標制度來進行,擇優選擇施工質量好,信譽好、價格合理的施工隊伍。
4.2加強施工單位的安全質量監督工作
施工單位本身要加強其在給排水施工過程中的安全質量監督和控制,通過制定自身施工安全質量控制制度,規范施工人員和管理人員的施工行為,保證給排水工程施工安全和質量的順利達標。同時,政府相關的監管部門要加大對施工單位在施工過程中的安全質量監督和檢測,對施工過程中的重點項目及綜合情況進行跟蹤監控,通過不定期的實地抽查和定期的項目檢測對工程的施工投入、施工合同、施工材料設備、施工機構設置和安全質量管理體系等相關方面進行監督和控制,及時的了解和掌控給排水工程的施工安全質量情況。
5、 增強市政給排水工程施工管理與控制的相關措施
5.1? 標準市政給排水的建設制度
市政給排水建設主管部門要嚴格遵守相關規定,而且規范給排水工程的施工單位,規范管理單位的施工資質和禁止項目分包、轉包等情況,管理單位要定期檢驗或者不定期的抽查市政給排水的施工現場,避免出現違規施工。此外,市政給排水項目工程要擬定工程法人制度、合同制度和監理制度,這樣就產生更加完善的施工管理系統,然后確保項目的質量。
5.2? 監督體制要構建完善
在市政給排水項目完成以后要實施驗收項目,這是一項非常繁雜的工作,其不但要依照項目技術,還要依照國家的有關規定實施審查,同時監督管理機制不但存在項目完工以后,監督管理機制還在項目的每一個階段中都存在,有關技術人員要實施具體的質量交接審查,并把記錄做好,質量安全問題一旦出現了要馬上終止項目,并監督違規人員實施及時的改正。另外,還要建立明確的賞罰方法,處罰違規操作的員工,對優異的員工要進行表揚與獎勵。
5.3? 把協調工作做好, 落實質量責任制度
給排水管線施工牽涉到相對多的單位,在之前的施工管理中,因為管線單位各自為政,它只接受管主單位的管理,在管理工作中沒有統一的納入。因此,在管線施工的時候,管線單位的施工質量與進度是管理人員要隨時監督,要嚴格的依照質量要求實施檢驗,在進度上監督施工單位,假如有拖延,則需要馬上使用相關的趕工方法,同時向管線主管單位通報狀況,甚至使用別的經濟、合同等方面的方法來監督施工單位實施。
6、結束語
總體來說,城市特別關鍵的基礎設施是給排水工程。城市給排水施工管理確保著給排水項目的成功運作,對保持正常的城市秩序,使城市內澇危害減少,都具備積極的意義。作為新時期背景下的城市給排水施工單位,唯有城市給排水項目每一個施工階段的每一項管理工作切實做好,才可以從基本上保證城市給排水項目質量的提高,進而推動企業的不斷發展。
參考文獻:
[1] 任強.論城市給水排水工程施工管理[J].山西建筑,2012,(24).
[2] 趙景麗,宿鴻鵬.談城市給排水工程施工管理[J].黑龍江科技信息,2014,02:254.
[3] 王超群,許濤.城市給排水工程施工管理要點分析[J].工程經濟,2014,04:29-32.
(遼陽縣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遼寧? 遼陽? 11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