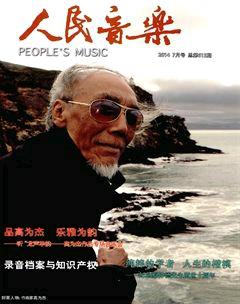勁兒該往何處使?
緣起
受作曲家郭和初教授的邀請,年初聆聽了以“嶺南歡歌”為主題的民族管弦樂新作品音樂會,有春風拂面的感覺。音樂會演奏了廣東省內作曲家們的十幾首新作。初略的印象是,作曲家們都在傾力、走心地創作,特別是盡力在體現嶺南的文化特色方面,每一首作品都能聽到南粵音樂的語言特點和氣韻。既有柔情雅致的《月夜》(房曉敏曲)、《小蠻腰隨想曲》(郭和初曲),富于客家風情的《飲酒燈》(嚴冬曲),也有大氣磅礴的《粵之歌》(藍程寶曲)等作品,頗為撩人耳膜,也蠻能體現“嶺南歡歌”的主題,無疑是廣東音樂界的一件大事,是新年期間文化舞臺上的高品位音樂會。如果從普通樂迷的角度欣賞一場新作品音樂會的新鮮感滿足感還是有的,甚而感佩藝術家們所付出的艱辛和努力。但如果從關心民族管弦樂發展的角度去聆聽這場音樂會,則不由生出許多感慨和思考。
本文不是對音樂會的評論,自然不會就具體作品的藝術品質發出議論,僅憑聆聽印象,從審美需求的層面討論一下民族管弦樂的創作中面臨的如何創新和突破,也就是勁兒該如何使的問題。
一
縱觀音樂會的所有新作品,一個突出的印象是作曲家都在一頭扎入廣東音樂的百花園,卻沒有輕松地走出來。因此,聽到許多密密麻麻的廣東傳統音樂主題,卻失落個性,沒有展現出音樂作品的獨立品格,加之演奏上的粗糙,很難留下深刻印象,審美上的回味和驚喜更是談不上了。據筆者的觀察,不僅此次音樂會的新作品,包括之前聆聽過的一些民族管弦樂新作品,明顯感覺到作曲家的著力點僅僅表面上拘泥于嶺南特色和新技法的運用等。
說到嶺南特色(往大里說是民族性),首先是地域音樂元素的運用,即民間音樂素材的采用。這些新作品集中采用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廣東音樂、粵曲、咸水歌、客家山歌、潮州鑼鼓等音樂素材。乍一聽,親切感就能油然而生,也能誘發豐富的想象。其次是音樂的表現內容,在嶺南歡歌的主題指引下,南粵的生活風俗、樂觀有趣的生活圖景躍然耳目,這些無疑是令人滿意的。可惜,音樂不是一種簡單的生活再現和認知,而是美的經驗和回味,僅僅這樣是不夠的。
于是,作曲家們在創新性上也做出了努力,而努力的著力點便是炫技性。也許本場音樂會的新作品有一定思想主題的創作要求吧,沒有特別突出的新技法運用,但也能聽到其中一些明顯的故意,這或許是某些作曲家的創作習慣。新音樂的創作,包括往常聽到的新音樂作品,常常為了求新而過多標新立異,祭出炫技的法寶。但是如果沒有顧及受眾的審美習慣,一味玩弄新奇怪異的技法,一廂情愿,猶如怪誕的行為藝術,容易讓人陷入一種審美的尷尬。
二
提起民族管弦樂,人們不禁將西方的管弦樂隊與之相類比。單就樂隊而言,其實二者的區別很大,前者的發展歷史很短,建制還缺乏穩定性,而后者是經歷了三四百年的發展,普及于全世界的、具有成熟穩定建制的管弦樂隊。雖然民族管弦樂隊在幾十年的發展中一直在借鑒甚至套用西洋管弦樂隊的建制,但是在音律、音色、音域等方面,樂器組之間,樂器組之內各種樂器都存在著演奏法、音準等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那么,為民族管弦樂創作新作品,必然會有不少讓作曲家犯難的困惑,如:該為什么樣建制的樂隊寫作呢?該如何擺脫先入為主的西洋管弦樂創作思維?如何體現民族管弦樂的交響性和戲劇性?等等。管弦樂的創作是復雜的工程,作曲家也有許許多多專業性的考量。但是,一個最實際的考慮因素應當是聽眾如何接受和欣賞的問題。音樂的審美跟其他藝術的審美不同,它很直接,不需要很多技巧和門道。對于聽眾的耳朵來說非常單純,也很實際,那就是期待著動聽的音樂來滿足其審美需求。從這個角度看,作曲家應當拿出來的是好聽的音樂,而不是提供學術研究的音響,那么,作曲家勢必在音樂的可聽性方面著力。而對于我國廣大聽眾,優秀的旋律無疑最能討好他們的耳朵,最具有可能性。
音樂旋律的寫作。旋律是音樂的靈魂,無論音樂風格如何變化,也無論是什么樣的樂種和體裁,旋律毫無疑問都是第一性的,然后才能談得上音樂的情感力度、和諧性、戲劇性和交響性等。寫不出優美動聽的旋律,諒你如何在其他方面耍出何等高妙的技巧和噱頭,音樂的內里都是蒼白的,經不起耳朵和心靈的考驗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民族管弦樂在幾十年的創作實踐中碩果甚豐,劉天華和劉文金等的創作便是成功的典范,從他們的音樂中我們留下印象的不就是不朽的旋律嗎?還有《彩云追月》(任光曲)、《金蛇狂舞》(聶耳曲)、《花好月圓》(黃貽鈞曲)等,人們何曾對它感到過厭煩。當今新作品的旋律寫作大多從民間音樂和傳統音樂中汲取主題動機,這是西洋音樂自古典主義以來屢試不爽的創作方式,逐漸成為我國作曲家常見的創作方式。只要能創作出優美的旋律,方法不是問題。問題是這種方法往往由于作曲家的技巧或者音樂視野所限,會產生很多雷同的作品來。像本場音樂會就有音樂主題的“撞車”,嶺南音樂幾個文化的版塊不可謂不豐富,可惜大家反復咀嚼的仍然是那幾個家喻戶曉的音樂主題,如《步步高》、《旱天雷》、《月光光》、《落雨大》等。更遺憾的是,有些作品在傳統音樂的曲調中徘徊、周旋,入乎其內,卻不能出乎其外,若隱若現的音樂動機未能形成獨立新穎的音樂語言,似乎是原來音樂的寄生物,沒有新的生命力,實在可惜。
要寫出脫俗的音樂旋律,這是無中生有的活兒,靈感來自何方,毫無規律可循。如果要植根于原來的音樂主題,必須充分消化,并有嫻熟的手段使其展現新的面貌,灌入新的血液,方得其成。與其依賴原有的音樂主題,不如撇開原有音樂主題這支拐杖又如何?原來的音樂不也是無中生有創作出來的嗎?音樂旋律來源于作曲家的天才創造,也來源于作曲家對生活的深刻體驗和心靈的直接傾訴。如果我們相信藝術的創作來源于生活,那么在這個時代里,人們的生活形態、價值追求、情智表現、審美要求等等,作曲家們應當有著比一般聽眾更加敏銳的感覺,音樂旋律如何孕育于作曲家的心靈和筆端,作曲家們自然會做出回答,音樂創作的勁兒首先應當往這兒使!當然,孕育優美的旋律固然是音樂創作的第一要義,但是對于民族管弦樂而言,還要適宜以樂隊的合理形式來表現。這包括使用樂器的發聲方式和技法,器樂化的旋律如何謀篇布局和發展進行,音色音區的適當運用和協調,以及旋律演奏當中的樂器組合等等。也就是說美麗的旋律需要有效的方式來表達,讓樂隊自如地發出屬于自己獨特品性的旋律聲音,否則會浪費美妙的旋律和樂思。endprint
不拘一格。追求多樣化的形式。管弦樂是追求交響性的,但是交響性在西洋交響樂隊和民族管弦樂隊中似乎不是同一回事,起碼存在差異。因為民族管弦樂隊的建制遠未形成成熟,功能分組、音響的平衡性、音色的融合性等還比較生硬,很難獲得穩定而理想的聲音效果。所以在創作上不要因循固定的模式,尤其是在交響性上謹慎對西洋交響樂隊的思維生搬硬套,弄不好還真是像一些樂迷所言,造成樂隊之間“自己吵自己”。因而,新作品的創作需要對樂隊的演奏形式作長期的錘煉,同時在形式上的多樣化探索才能擺脫西洋管弦樂隊先入為主的聲音標準的束縛。這是有巨大的發揮空間的,因為民族樂器的種類繁多,樂隊組合與聲音呈現的可能性是無窮的,新作品的創作不妨在這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或許是不錯的途徑。民族樂器在個性上有著很多優勢,譬如說笛子,其綺麗的聲音獨特魅力是無以比擬的。還有很多民族樂器如二胡、琵琶等在流行音樂的配器中運用得相當出色,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確實在這方面用心琢磨,管弦樂創作也不妨借鑒。不過,民族樂器的個性特征對管弦樂創作也是一種限制條件。民族樂器縱然種類繁多,選擇性多,也有很強的表現力,但是否在制作、改良、演奏、聲學研究上尚有怎樣的可能性和上升空間,這方面有沒有與時俱進?當然,這就不單純是作曲家,而是樂器改革家和演奏家的共同面臨的問題了。
承接傳統而不拘于傳統。對于傳統,很多現代的創作相當的不屑,主張拋開傳統、另辟蹊徑。表面上看,這樣可能會解放作曲家的創作思維,有利于大膽嘗試新的作曲技法。但是離開傳統必然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受眾對脫離傳統審美習慣的排斥,這是現實而不是可能性。也就是說,承接傳統和不拘于傳統需要辯證來看,二者要有調和。否則,不僅失去民族性,更會失去廣大的受眾。試想,普通的聽眾誰不是在傳統音樂的土壤中培養出對音樂的興趣?但是傳統的繼承不能成為創作思路的障礙,如果認為傳統會影響藝術的品質,不是對傳統的認識局限便是文化自信的缺失。
傳統音樂元素主要體現在音調節奏上的民族神韻和對華夏文化意象的美學追求。這在幾十年的創作實踐中不乏成功的范例,如:《歲寒三友——松·竹·梅》(顧冠仁曲)、《春秋》(唐建平曲)、《長城隨想》(劉文金曲)等。這種標題音樂的創作概念傳承于傳統古樂,對于音樂的傳播和理解是積極的,很能承接我們的審美傳統。但是全都是這樣的套路,未免落入流俗,風格單一。如果一味在美學意象上做文章,恐怕會走向另一極端。前些年開始流行一種將20世紀新潮音樂技法與中國遠古的意向嫁接,試圖呈現具有現代意識和審美價值的原始風韻。美學理念很是誘人,卻鮮有成功的范例。有些作曲家為了追求更深邃的意境,弄出一些生僻玄奧的標題來,讓人莫名其妙。不僅如此,為了表現某些玄妙的標題,在技法上無奇不有,制造出毫無章法、怪誕而刺耳的音響堆砌,那便是誤入歧途了。音樂創作的核心要義還是音樂性的美感,是純粹的精神愉悅。音樂不應當承擔過多的內容解釋,造成不堪負重。因此,作曲家不如將表現內容更寬泛一些,放棄小聰明而將心思投入對生活的真誠熱愛,對崇高心靈的追求,或許能進發創作的靈感和收獲純粹音樂美感的汩汩樂思。
三
誠然,藝術創作的創新追求和探索都是積極的,值得贊許的。然而,創新又是何等的困難,藝術家還要面對如何承接傳統的困惑。音樂文化的發展猶如長河奔流,傳承和創新是維持其發展的核心價值和動力。由于音樂文化基因的問題,我們必須堅守傳統,挖掘精髓,保持對傳統的適度自信。而在創新上,除了上述在旋律寫作和演奏形式的多元組合外,需要努力的方面還有很多,諸如樂器的改良研究、社會的關注評價和受眾群體的培養等,這些都應當視作對創作的有益幫助。但是無論如何,創作的內核和靈魂必須是音樂的美感,是與人們的心靈接壤的聲音。切忌一提起音樂創作總是諱莫如深的技術,以專業性自居,要拒一般聽眾以千里之外,一味地孤芳自賞,那不是音樂創作的正道。以作曲家的聰明才智和對聲音的敏感,創作有趣的音樂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但是優秀的音樂作品不能停留在表面的生動有趣和自然模仿,而是追求有內涵的表現和持久耐聽的審美價值。試想誰會僅僅是因為有趣去反復聆聽貝多芬的交響曲呢。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音樂會的主辦方雖是廣東民族樂團和星海音樂廳,但省委宣傳部和文化廳是重要的支持者,可見官方的鼎力支持難能可貴。藝術的創作由官方來組織策劃,提供創作條件和資源,或者集體采風等,而在創作題材和目的上又有諸多要求,類似命題作文。這在我國算是比較普遍的做法,這種創作方式的優點在于能及時產出作品,并在行政資源的支持下及時得以排練演出。但是,音樂作品非一般的工業品,需植根于人的心靈和生活情感。這樣“短平快”的藝術產生方式,往往缺乏作曲家的自由思考和深刻的生活體驗,作品的質量未必能得到保證,更遑論錘煉出藝術精品。再者,這種批量生產的作品,很少有機會重復演出,往往都是一次性的展演。人們常常感嘆新作品的創作匱乏,作曲家缺乏創作熱情,也許這并非實情。全國各類新作品創作比賽和委約創作在絕對數量上相當可觀,只不過在質量上、傳播方式上、受眾面上都存在問題,以至于沒有培育出適應時代發展的生命力罷了。麥瓊華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 榮英濤)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