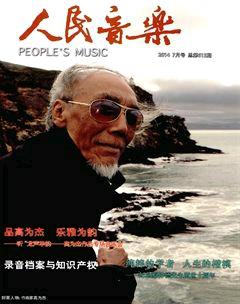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吳躍華
覃江梅的《當(dāng)代音樂教育哲學(xué)研究:審美與實(shí)踐之維》(上海音樂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簡稱“覃著”)是基于她博士論文而出版的專著。該書較為系統(tǒng)地梳理了當(dāng)代北美音樂教育審美哲學(xué)和實(shí)踐哲學(xué)的歷史發(fā)展脈絡(luò)并發(fā)表評論,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英文文獻(xiàn)”的同時(shí)也確實(shí)有利于拓寬“中國音樂教育哲學(xué)的視域”。但書的立場和某些觀點(diǎn)也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鑒于該書主體內(nèi)容主要來源于雷默與埃利奧特的代表性專著,且這些專著均有中譯本也易為國人所查找了解。因此,筆者僅就覃著評論值得商榷的地方發(fā)表看法以尋求對話。
對審美哲學(xué)的評價(jià)有失公允
不難看出,覃著具有較深的歷史感。這對于音樂教育哲學(xué)這一亟待開發(fā)的專門領(lǐng)域的深入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但覃著站在實(shí)踐哲學(xué)的立場進(jìn)行梳理,顯然,對審美哲學(xué)評價(jià)的不公已不可避免。就總體而言,“當(dāng)代音樂教育哲學(xué)”僅關(guān)注北美是不夠的,對于審美哲學(xué)的梳理連盛產(chǎn)哲學(xué)的德國都沒有提及是不合適的,尤其在研究現(xiàn)狀中對我國音樂教育哲學(xué)的交待更是顯得單薄而令人遺憾。就具體而言,對審美哲學(xué)的梳理主要集中在雷默著作上,以下,本文就這方面集中談?wù)擇械脑u價(jià)不公現(xiàn)象。
首先,覃著通過自上個(gè)世紀(jì)初以來的審美哲學(xué)探索軌跡的梳理指出雷默著作的代表性意義。但對其評價(jià)多用“缺乏邏輯”、“站不住腳”(第189頁)等否定性詞語,對埃利奧特的評價(jià)卻用更多的篇幅來贊美,即使批評也僅是用“面臨挑戰(zhàn)”、關(guān)注不夠、不足等(第177—207頁)來做簡短的委婉表達(dá)。對雷默來自內(nèi)部的批評描述成是內(nèi)部“倒戈”、“背叛”(第4頁)。對埃利奧特來自內(nèi)部的批評卻描述成對其理論是“興趣盎然”、“熱情高漲”(第157頁)。對雷默基于反思而推出的第三版著作做出的調(diào)整說成是“他自己意識到審美理論的不足”(第137頁),對埃利奧特自己發(fā)動的反思著述說成是“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第156頁)。作者認(rèn)為實(shí)踐哲學(xué)是建立在許多學(xué)科基礎(chǔ)上的,而對雷默一書豐富的參考文獻(xiàn)卻視而不見,做出“絕對不能單純地套用18世紀(jì)以來西方美學(xué)”(第145頁)的結(jié)論,并說雷默哲學(xué)存在的問題是因?yàn)樗拿缹W(xué)理論有“致命缺陷”(第191頁),讓人感覺實(shí)踐哲學(xué)的多學(xué)科理論基礎(chǔ)就沒有缺陷似的,難道此“多學(xué)科”可以不包括這有“缺陷”的美學(xué)嗎?對雷默吸取兩千多年以來的豐富美學(xué)實(shí)踐成果特別是20世界以來的美學(xué)新成果忽視不說,似乎認(rèn)定雷默只是在為有“缺陷”的舊美學(xué)“背書”。總之,覃著給筆者的感覺不是在公允地對審美哲學(xué)作為一個(gè)“維度”進(jìn)行歷史的梳理,而是把雷默找來給自己的立場實(shí)踐哲學(xué)“墊背”的。
其次,覃著一方面指責(zé)該書主要分析對象即雷默審美哲學(xué)是“沿襲了笛卡爾一康德以來的二元論”(第15頁),另一方面又強(qiáng)調(diào)“本書中提到的審美理論指的是新康德主義審美傳統(tǒng)”(第16頁)。一方面以實(shí)踐哲學(xué)范式的姿態(tài)指責(zé)審美哲學(xué)范式,不是用“狹隘”就是用“簡單”來形容并貶低。另一方面又聲明自己的研究采用里吉爾斯基“范式”概念主張,即認(rèn)為“范式無所謂‘好或者‘壞,只不過是‘起作用或‘不起作用的區(qū)別”(第19頁)。一方面在“緒論”中說自己的“研究方法”是采用“文獻(xiàn)分析法”、“歷史法”(第19頁)對兩個(gè)哲學(xué)范式進(jìn)行深入分析,給人感覺是在客觀研究。另一方面在“結(jié)語”中又著重強(qiáng)調(diào)“批判性”面目(第220頁),似在為自己的評價(jià)過于偏斜的“參與爭鳴”(第219頁)角色定位做“解說”。可見,立場傾斜不說許多地方還自相矛盾。事實(shí)上,對雷默哲學(xué)基礎(chǔ)作上述簡單化判斷正反映出作者的分析還不夠透徹。對雷默哲學(xué)產(chǎn)生的美國分析哲學(xué)時(shí)代背景以及當(dāng)時(shí)的“曼哈頓計(jì)劃”的要求、布魯納結(jié)構(gòu)主義課程觀的影響都缺乏應(yīng)有的分析(有的方面甚至只字未提),也對當(dāng)時(shí)學(xué)術(shù)界普遍重新發(fā)現(xiàn)鮑姆加通對美學(xué)的感性學(xué)本質(zhì)闡述的進(jìn)步意義的重視的運(yùn)用置若罔聞,甚至對雷默重視“體驗(yàn)”這樣帶有現(xiàn)象學(xué)、后現(xiàn)代課題的超前意識也忽略不計(jì),卻指責(zé)其“斷然不能在真空中進(jìn)行”(第145頁)。在筆者看來,雷默之所以要對審美做出嚴(yán)格限定主要是與當(dāng)時(shí)流行的分析哲學(xué)強(qiáng)調(diào)“概念澄清”主張、布魯納結(jié)構(gòu)主義課程觀和曼哈頓課程開發(fā)計(jì)劃對學(xué)科基本結(jié)構(gòu)的強(qiáng)調(diào)與要求是分不開的。雷默對審美體驗(yàn)的強(qiáng)調(diào)是對杜威的經(jīng)驗(yàn)主義教育學(xué)理論的借鑒和對現(xiàn)象學(xué)、后現(xiàn)代注重“意義”的體驗(yàn)研究的初步嘗試,顯然不能僅僅說成是傳統(tǒng)美學(xué)的二元論。
此外,還讓人納悶的是覃著對雷默哲學(xué)的批評不以作者認(rèn)為的“變化最大”的最近的第三版本為中心進(jìn)行梳理,卻把重心放在第一、二版本上,并簡單說其理由是因?yàn)槿齻€(gè)版本堅(jiān)持的基本觀點(diǎn)沒有變化,并引用別人話語認(rèn)定三個(gè)版本只是在“講三個(gè)故事”(第166頁)。對雷默第三版本的兼容哲學(xué)中留有多元文化哲學(xué)的空間僅僅說成是“承認(rèn)”了“文化多樣性的現(xiàn)實(shí)”,仿佛雷默是被逼得不得不向?qū)嵺`哲學(xué)讓步做出的不得已改進(jìn)一樣。事實(shí)上,“音樂”能用人類學(xué)視野,“審美”就不能進(jìn)行人類學(xué)思考嗎?恐怕審美人類學(xué)要比音樂人類學(xué)研究成果豐富多的多。撇開人類學(xué),如果我們把“審美”、“音樂”兩個(gè)詞放在平等的視野下比較的話,恐怕“音樂”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比“審美”更寬的詞。夸贊實(shí)踐哲學(xué)視野下“音樂”概念開闊、前沿卻要“審美”原地踏步、狹隘是何道理啊?這樣的評論與其說是在反對學(xué)術(shù)話語霸權(quán)不如說是在非理性層面的爭霸。
重現(xiàn)埃利奧特的誤讀
解釋學(xué)是允許個(gè)人偏見存在的。如果說對審美哲學(xué)評價(jià)不公還屬于個(gè)人偏見的話,那么對審美哲學(xué)的誤讀(即把審美哲學(xué)僅理解為情感教育)就實(shí)不應(yīng)該了。雷默在該書中專門用“音樂是情感的一種語言嗎”一節(jié)內(nèi)容來談這個(gè)問題,凡是具有閱讀能力的人都能看出雷默實(shí)際上是批評把音樂作為情感語言的。雷默說:“只要對音樂的感應(yīng)是對情感標(biāo)示的感應(yīng)就是非音樂的……這種教學(xué)也是非音樂的”。接著,雷默還不嫌啰嗦又用“音樂是自我表現(xiàn)的一種手段嗎”一節(jié)從前面對音樂客體的論述轉(zhuǎn)到主體進(jìn)行分析,說“如果一個(gè)藝術(shù)家真是在表現(xiàn)他在創(chuàng)作時(shí)的感受,他的作品很難具有藝術(shù)性”;“如果音樂就是被理解為發(fā)泄人在某個(gè)特定時(shí)刻感覺的自我表現(xiàn),音樂教育就很不相干了”“如果人文藝術(shù)是表現(xiàn)情感的途徑,這畢竟是任何人在任何時(shí)候都能自動做到的,我們又何以要認(rèn)為他們是一門學(xué)科呢”;“藝術(shù)教育貶值就是因?yàn)橐詾樗麄兏愕氖乔楦薪逃保弧坝捎诟杏X這個(gè)詞常常被認(rèn)為只限于情感,所以感覺這個(gè)詞和藝術(shù)用到一起時(shí),常常被認(rèn)為是意味著所有的藝術(shù)必須帶有感情色彩,我們的藝術(shù)體驗(yàn)只能是動情的。但是這是對藝術(shù)與感覺的關(guān)系的非常局限的概念:它不是我們這里所講的概念”;像這樣的論述在隨后的章節(jié)中還有筆者很納悶,覃著對此為什么視而不見非要僅僅認(rèn)定雷默哲學(xué)是情感哲學(xué)呢?接下來,雷默的分析啟發(fā)了我,雷默說:“打消了音樂是情感語言和一種情感表現(xiàn)的概念,順理成章就可以進(jìn)行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呢?雷默說:“人類的所有體驗(yàn)都充滿了主觀感應(yīng),充滿感覺,感覺對于人生猶如空氣對于人體”,也就是說“審美教育”就是“感覺教育”,這樣一來,實(shí)踐哲學(xué)要對“感覺”這個(gè)重要的“如空氣對于人”一樣的東西進(jìn)行批判恐怕就難了,進(jìn)而錯(cuò)誤地做出了雷著并沒有沿用審美原義“感覺”的判斷(第80頁)。是不是出于因?yàn)殡y以批評又要批評才能把自己的觀點(diǎn)立起來的考量,才故意對雷默哲學(xué)進(jìn)行誤讀或者作狹隘理解不重要,重要的是實(shí)踐哲學(xué)確實(shí)誤讀、狹隘了雷默審美哲學(xué)的本質(zhì)。而且,這樣的誤讀與其說是覃著的分析,還不如說是埃利奧特的觀點(diǎn)@。埃利奧特在自己的專著中還告誡我們:“有哲學(xué)思維的人還要努力去平衡系統(tǒng)性批判和系統(tǒng)性理解。因?yàn)槿绻麤]有真誠地去傾聽和相信別人的解釋,那么就很容易只懷疑別人的信念、而不去懷疑自己的信念”。真不知道埃利奧特等人是怎樣去真誠地傾聽別人的。當(dāng)然,雷默哲學(xué)也確實(shí)不完全排斥情感教育(他說的情感教育跟我們理解的情感教育有很大出入),但他認(rèn)為情感教育只是感覺教育這個(gè)茫茫大海中的一個(gè)很小的浮標(biāo)。把雷默哲學(xué)僅當(dāng)成情感哲學(xué)進(jìn)行批評進(jìn)而徹底否定,顯然是犯了“稻草人”邏輯謬誤。endprint
音樂教育哲學(xué)能擁有更開放的未來嗎
面對實(shí)踐哲學(xué)對審美哲學(xué)的洶涌批判,雷默在其著第三版用了很多篇幅進(jìn)行反駁,認(rèn)為實(shí)踐哲學(xué)者的批判是“過度簡單化,或者是過度夸大,或者是曲解”。中國學(xué)者也發(fā)出一些反對聲音。雷默一書翻譯者熊蕾認(rèn)為有些批判者是“為了在理論爭論上占上風(fēng)”而曲解,為了“趕時(shí)髦而對所謂新理論生吞活剝地引用”。王安國教授也撰文指出,音樂教育哲學(xué)由審美哲學(xué)轉(zhuǎn)向?qū)嵺`哲學(xué)不具有普遍性。不要動輒就說審美哲學(xué)過時(shí)了,也不要無保留推崇實(shí)踐哲學(xué)。廖家驊教授發(fā)文批評到,“照搬照套這些洋哲學(xué)顯然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如此情勢正如覃著描述到,這兩種哲學(xué)的爭論從20世紀(jì)后期起直至當(dāng)下還在繼續(xù),管建華教授在該書序言中也指出,“這兩種哲學(xué)爭論的熱潮也逐漸進(jìn)入中國”。筆者之所以要為審美哲學(xué)做一些辯駁是因?yàn)椋瑢徝勒軐W(xué)作為人類長期實(shí)踐的歷史積淀來之不易,它是一種人類創(chuàng)造,也是一種文化,不可能徹底清除,實(shí)踐哲學(xué)不能動不動就做出“從根本上否定它的理論基礎(chǔ)”(第137頁)的結(jié)論,讓人誤以為審美哲學(xué)毫無價(jià)值。對實(shí)踐哲學(xué)的批評也不是想徹底推翻它,希望我們能多一些冷靜的觀察,“不僅要看它怎么說的還要看他怎么做的”,這是國家外交部常用的言辭,我覺得用在這也比較合適。總之,運(yùn)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辨證的去分析和借鑒還是比較妥當(dāng)?shù)摹?/p>
遺憾的是,國內(nèi)簡單化思維還是存在的,不僅表現(xiàn)在實(shí)踐哲學(xué)對審美哲學(xué)的批評上(其實(shí),批評也沒有什么太多新意,有些文章甚至大量重復(fù)著國外的爭吵),而且還表現(xiàn)在對雷默哲學(xué)的盲目崇拜方面,如有研究者就聲稱,“美國雷默的思想幾乎構(gòu)建了新課標(biāo)制定的整個(gè)理論基礎(chǔ)”。在筆者看來,雷默審美哲學(xué)不能代表審美哲學(xué)全體,顯然也不能代表中國音樂教育的審美哲學(xué)。這一點(diǎn)音樂課程標(biāo)準(zhǔn)研制組組長王安國教授在最近的文章中已經(jīng)說的很清楚了。實(shí)踐哲學(xué)企圖用對雷默進(jìn)行否定而波及全體的簡單化思維,無視審美哲學(xué)多樣性現(xiàn)實(shí)不可取,作為中國音樂教育研究者也采用這么簡單的論斷,忽視幾代中國人對此付出的努力而做出如上簡單判斷也實(shí)不應(yīng)該。在筆者看來,中國的音樂教育審美哲學(xué)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人學(xué)理論指導(dǎo)下的,以“人”為邏輯起點(diǎn)構(gòu)建的全面發(fā)展觀視野下的審美哲學(xué)。它不同于雷默和埃利奧特完全從音樂本質(zhì)推論出的音樂教育哲學(xué)。
作為信仰實(shí)踐哲學(xué)的朋友,也不要把審美哲學(xué)當(dāng)成“狼”,似乎不“打倒”它自己這個(gè)“小羊羔”就沒法“活”了。事實(shí)上,雷默在他的書的第三版已經(jīng)提出了“兼容哲學(xué)”的構(gòu)想,可見,“狼愛上羊并不荒唐”,我們也希望看到實(shí)踐哲學(xué)能拿出“與狼共舞”的勇氣,不要動不動就說與之“水火不容”。如此下去,我們似乎應(yīng)該可以樂觀其成了。但就當(dāng)下的現(xiàn)狀來看,僅促使兩種哲學(xué)達(dá)到和諧共處好像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因?yàn)椴还苁菍徝勒軐W(xué)還是實(shí)踐哲學(xué),我們似乎都忽略了我們生產(chǎn)哲學(xué)服務(wù)于實(shí)踐最終必須依賴于作為實(shí)踐主體的教師這一核心環(huán)節(jié)。加拿大音樂教育哲學(xué)家鮑曼曾無奈地說到,北美音樂教師許多人根本不關(guān)心這些哲學(xué)(第4頁)。據(jù)筆者了解,中國廣大音樂教師又何嘗不是啊!金兆鈞曾在一篇文章中用“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來形容當(dāng)時(shí)國內(nèi)人們在剛接觸流行音樂時(shí)的狀況,我覺得挺形象的。借用來形容當(dāng)前中國音樂教育哲學(xué)存在狀況也很恰當(dāng),兩種哲學(xué)的支持者猶如兩岸的猿聲,“啼”個(gè)“不停”(爭論不休),但許多音樂教師猶如那位“劃船人”,在“啼鳴”中早已駛向前方。
兩種哲學(xué)之所以爭論不休恐怕主要在于我們的慣性思維還是存在音樂教育必須只有一種教育哲學(xué)的心態(tài)。實(shí)踐哲學(xué)及文化哲學(xué)(管建華先生概括埃里奧特說“他提出的……就是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哲學(xué)”表面上聲稱視野寬廣,但過度排斥、否定審美哲學(xué)也難逃“爭霸”嫌疑。事實(shí)上,被我們遺忘了的實(shí)踐主體——每個(gè)教師也都有自己的實(shí)踐智慧即個(gè)人哲學(xué)。即使再差的音樂教師也有自己的教育觀念在支配著自己的實(shí)踐。筆者認(rèn)為,合理的音樂教育哲學(xué)布局除了肯定既有音樂教育哲學(xué)范式存在的合理性外還應(yīng)該包含個(gè)人哲學(xué)維度。因?yàn)椋紫冗@是教師的個(gè)人哲學(xué),它直接影響教師的實(shí)踐,是教師的實(shí)踐智慧,也是教師真真切切在用的哲學(xué),不是我們承不承認(rèn)的問題。其次,當(dāng)前社會是全球化的社會,是商品社會,文化成了商品(消費(fèi)品),甚至理論也成了商品。學(xué)校教育也難逃這樣的后現(xiàn)代文化邏輯。商品社會的規(guī)則是由市場決定的。市場邏輯重心在于消費(fèi),再好的哲學(xué)構(gòu)想(文化消費(fèi)品)如果不被教師(消費(fèi)者)所選擇也只能僅是一種理論假設(shè)而已。就這一點(diǎn)來說,不管審美還是實(shí)踐哲學(xué)家們都需要轉(zhuǎn)變觀念,變“哲學(xué)指導(dǎo)實(shí)踐”那么一個(gè)威嚴(yán)的面孔為“哲學(xué)服務(wù)實(shí)踐”這樣一個(gè)平等友善的姿態(tài)。同時(shí)哲學(xué)家們還需要虛心接受來自實(shí)踐領(lǐng)域教師的檢驗(yàn)。也只有經(jīng)過實(shí)踐教師檢驗(yàn)的哲學(xué)才更具有活力和相對真理性。而且哲學(xué)家們獲得來自實(shí)踐的聲音也有利于進(jìn)一步改進(jìn)哲學(xué)的研究和創(chuàng)新去更好的服務(wù)實(shí)踐,變“哲學(xué)指導(dǎo)實(shí)踐”的傲慢姿態(tài)為“哲學(xué)來源于實(shí)踐”的謙卑情懷。再次,重視教師的個(gè)人哲學(xué)也有利于增強(qiáng)教師的力量,提高教師跟哲學(xué)家進(jìn)行對話的能力,使得教師更具有選擇能力。這既有利于促進(jìn)哲學(xué)服務(wù)實(shí)踐的落實(shí),也會減少不至于使教師僅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而孤芳自賞。同時(shí)提高教師的哲學(xué)學(xué)習(xí)與研究(也可以說叫反思)能力也符合當(dāng)下教師專業(yè)化發(fā)展的期待。
覃著在結(jié)語中提出“走向一個(gè)開放的未來”的展望,從其站在實(shí)踐哲學(xué)立場對審美哲學(xué)的充滿否定性評價(jià)來說,筆者看不出其聲稱的“包容性”、“對話”的“未來”(第220頁)的邏輯結(jié)論。如綜筆者上述分析,假在普遍性(暫時(shí)指審美哲學(xué))、特殊性(實(shí)踐哲學(xué)或者多元文化哲學(xué))、個(gè)體性(個(gè)人哲學(xué))三個(gè)維度上構(gòu)建一個(gè)多元音樂教育哲學(xué)合作平臺,中國的音樂教育哲學(xué)或許才能真正迎來更加開放的、具有全球意識的未來。(責(zé)任編輯 金兆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