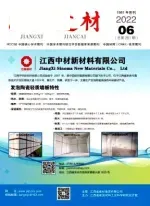《老老恒言》之古代健康居住思想釋讀及其對當代建筑設計的啟示
■趙曉峰,李澤欽,王 爽 ■河北工業大學,天津 300401
《老老恒言》又名《養生隨筆》,是清代文士曹庭棟撰寫的一部老年養生專著。曹庭棟,字楷人,號六圃,中年后,絕意仕途,于居處累土為山,曰“慈山”,故又號慈山居士。曹氏少嗜學,工詩文,勤奮博學,于經史、詞章、考據等皆有所鉆研,還是頗有造詣的琴學家、書畫家,尤精養生學,并身體力行,享壽近九旬。《老老恒言》共五卷,前二卷敘起居動定之宜,次二卷列居處備用之物,末附粥譜一卷,借為調養治疾之需。主張養生實踐要寓于日常生活起居瑣事之中,不可勉強求異。
1 《老老恒言》健康居住思想解析
《老老恒言》的健康居住思想主要表現在日常起居行為和居室家具器物兩大層面。日常起居行為主要表現在第一卷的安寢、晨興、盥洗、飲食、食物、散步、晝臥、夜坐,以及第二卷的燕居、省心、見客、出門、防疾、慎藥、消遣和導引等篇。日用家具器物主要表現在第三卷的書室、書幾、坐榻、杖、衣、帽、帶、襪、鞋、雜器,以及第四卷的臥房、床、帳枕、席、被、褥和便器等篇。下文將從以上兩大層面中挑選與居住理念關系緊密者進行討論。
1.1 日常起居行為
《老老恒言》認為老年人在日常起居行為中首先應做到睡眠安穩。而要做到睡眠安穩,必先進入消除雜念的心理狀態,這就是“先睡心,后睡目”的原則。如何才能達到這種狀態呢?曹氏認為有兩種方法,一是“操”,即控制心神內守;二是“縱”,即任由心神馳聘,這兩種方法都是進入睡眠狀態的好途徑。其次,是睡姿的問題,認為側臥是安寢的重要方法。如果左側臥,則左腿和左臂都要彎曲,而右腿要伸展開,同時用右手放置在右側大腿上;右側臥則于此相反。此外,還強調就寢時不燃燈、不蒙頭,更要注意夜間睡眠時的腹部保暖,其保暖方法采用內肚兜外加肚束的形式,頗似現今的腹帶。
其次,《老老恒言》很注重起居活動狀態,認為燕居需要“內觀養靜”和“寒暖得宜”。內觀養靜的方法類似于打坐,要于室內調息端坐,心沉氣海。寒暖得宜則要依據季節的變化進行調適,比如春季下半身要保持溫暖,上半身則可略減衣物;夏日可借助冰盤克制酷暑,冬季則可置爐抵御嚴寒。

事項 基本原則(筆者據原文歸納)主要方法(引自原文)安寢消念入寢寐有操縱二法,操者使心有所著,乃不紛馳,庶可獲寐;縱者任其心游思于杳渺無朕之區,亦可漸入朦朧之境。寢不尸(即不仰臥) 左側臥,則屈左足,屈左臂,以手上承頭伸右足,以右手置右股間,右側臥,反是。夜寢暖腹 辦兜肚,兜肚外再加肚束。寬約七八寸,帶系之,前護腹,旁護腰,后護命門。燕居內觀養靜 一室默坐,常以目視鼻,以鼻對臍,調勻呼吸;毋間斷,毋矜持,降心火入于氣海,自覺遍體和暢。寒暖得宜春冰未泮,下體寧過于暖,上體無妨略減,所以養陽之生氣。夏月冰盤,以陰乘陽也;冬月圍爐,以陽乘陰也,陰陽俱不可違時。
1.2 居室家具器物
《老老恒言》認為居室、家具與器物的合理設計也是影響健康居住的重要因素(詳見下表)。居室方面主要涉及書室與臥房,要求書室向陽,室前設寬大庭院,書室的門戶處設簾幕以障風;要求臥房應居于東側,以乘生氣(按照五行方位的說法,東屬木,主生),有更強的圍護性和私密性,符合“退藏于密”的基本原則。家具方面主要論述了床榻,強調床榻應在四周和上面以木板適度為何,具有良好的圍合性,圍合的木板材質宜選杉木,而且表面不宜上漆,這樣可以吸附墻壁的濕氣。器物方面述及了枕、被,建議使用長枕,并以通草作為囊枕內的填充材料;被子宜寬大舒適,如蠶繭之周密。

事項 基本原則(筆者據原文歸納)主要方法(引自原文)書室乘陽而居 室取向南,乘陽也。簾幕障風 室中當戶,秋冬垂幕,春夏垂簾,總為障風而設。室前寬庭 室前庭院寬大,則舉目開朗,懷抱亦暢。臥房居東獨臥 室在旁曰房。老年宜于東偏生氣之方,獨房獨臥。退藏于密 臥房為退藏之地,不可不密,冬月尤當加意。若窗若門,務使勿通風隙,窗闔處必有縫,紙密糊之。床榻圍合護體 上蓋頂板,以隔塵灰,后與兩旁,勿作虛欄;鑲板高尺許,可遮護汗體。杉木隔板安床著壁,須杉木板隔之。杉質松,能斂濕氣,若加油漆,濕氣反凝于外。頭臥處近壁,亦須板隔,否則壁土濕蒸,驗之有霉氣,人必受于不覺。枕被長枕去熱 老年獨寢,亦需長枕,則反側不滯一處。頭為陽,惡熱,即冬月輾轉枕上,亦不嫌冷。通草制枕囊枕之物,乃制枕之要。綠豆皮可清熱,微嫌質重;茶可除煩,恐易成末;惟通草為佳妙,輕松和軟,不蔽耳聰。被如蟬繭被取暖氣不漏,故必闊大,使兩邊可摺,且反側寬舒,腳后兼緝合之,錫以名曰“繭子被”,謂如蠶繭之周密也。
2 《老老恒言》核心理念對當代建筑設計的啟示
2.1 陰陽調適
《老老恒言》認為,影響健康居住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居室空間的陰陽屬性,要求做到陰陽調適。陰陽適中首先表現為室內有適宜的亮度,其引《洞靈經》之語曰“太明傷魂”,又引《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多陰則痿”。這告訴我們調節室內明暗的重要性,除了利用開窗調節之外,古人認為室內空間體積的大小也決定著室內的陰陽。也就是說,古人在評價室內陰陽暗藏著一個最基本的衡量指標,即窗面積與室內容積的比值,我們可以叫它“窗容比”。從某種意義上講,“窗容比”的理念比當今“窗地比”的概念在評價室內自然光照效果方面更為合理。
當然不同功能的居室對陰陽有不同的要求,如書室就要求明亮些,故多朝南以乘陽,而且室前庭院要寬大,以便“舉目開朗,懷抱亦暢”;而臥房則宜適當偏暗,以斂神聚氣,這樣可以符合《易傳》“君子以向晦入宴息”的原則。此外,即使是同一類居室還要有可調節性,如書室庭前要“樹陰疏布”,冬夏因樹冠濃密不同而獲得適宜季節的明暗效果。
2.2 引氣與障氣
在今天的居住建筑設計中,自然通風設計,尤其是“穿堂風”的設計一直倍受重視,在自然通風效果評價中,常常以通風換氣的效率作為很重要的指標,比較重視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一個居室空間的空氣更新。而《老老恒言》中卻呈現了古人不盡相同的評價方式,如何快速通風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整個通風過程中人如何避免氣流的傷害。換句話說,今天我們評價室內通風考慮的是純粹的物理環境,而古人始終把“人”作為關注的中心,是真正的以人為本。
以書室為例,要“秋冬垂幕,春夏垂簾,總為障風而設”。在這里,沒有太多關注通風反倒是關注“障風”。雖“南北皆宜設窗”,但“北則雖設常關”,只在“盛暑偶開,通氣而已”。開窗則宜采用“合窗”(即上下兩扇)的形式,當上扇開啟時,仍有下扇作障,這樣就可以“雖坐窗下,風不得侵”。坐榻如不靠墻壁,需“制屏三扇,中高旁下,闊不過丈,圍于榻后”,也是為了防止“賊風”(即有害氣流)的損害。
2.3 人性化設計
《老老恒言》中關于人性化設計的記述幾乎比比皆是。如建議書室前庭院東西墻高度適當下降以納入早晨和下午更多的日光,以“紅日滿窗,可以永晝”;書室南窗與庭前的樹木位置要距離適中,太近則“陽光少而陰氣多,易滋濕蒸入室之弊”;冬天的時候要“以毯鋪幾”,“使著手不冷,即覺和柔適意”;冬日臥床下四面“板密鑲之,旁開小門”,并“置爐于中”,以保持床體溫暖,夏天則可將板去掉,符合可變性設計的理念。
3 結語
《老老恒言》中的健康居住思想有很多合理的內容,其中一些理念甚至對今天的建筑設計依舊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簡賅地說,古人關注設計始終是以人為核心的,而我們今天的各種評價更多的是從建筑物理環境相關指標或者舒適度的角度進行評判的。孤立地評判建筑物理環境是有缺失的,而舒適度卻不一定能帶來健康。因此,探討古代健康居住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較高的實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