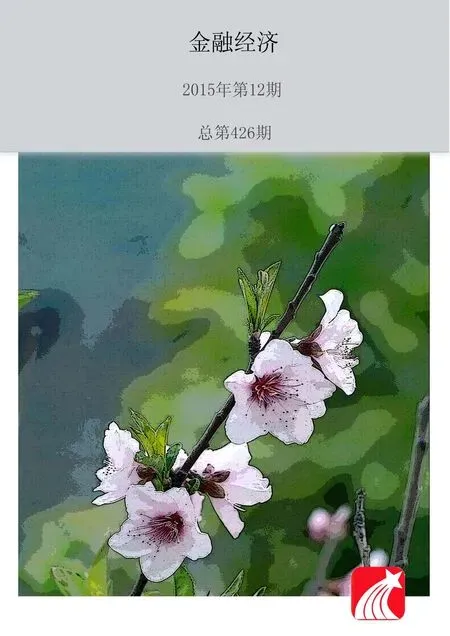民間金融發(fā)展背景下完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芻議
趙永剛
(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廣東 廣州 510120)
一、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立法演變路徑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納入我國法律調(diào)整范圍有一個發(fā)展過程,從行政法規(guī)、單行刑法再到納入刑法典的過程。
(一)行政法規(guī)階段
最早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進(jìn)行規(guī)制的法規(guī)是國務(wù)院1992年頒布的《儲蓄管理條例》,其中第八條規(guī)定:“除儲蓄機構(gòu)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辦理儲蓄業(yè)務(wù)”。第三十四條規(guī)定,“擅自開辦儲蓄業(yè)務(wù)的”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法律責(zé)任,其中構(gòu)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儲蓄管理條例》雖然從行政法規(guī)層面對“擅自開辦儲蓄業(yè)務(wù)”進(jìn)行了禁止性規(guī)定,并規(guī)定了應(yīng)追究刑事責(zé)任,但是此時“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還尚未納入刑事法規(guī)中。這一時期,隨著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出現(xiàn)了一系列關(guān)于非法集資的案件,如當(dāng)時轟動一時的“沈太福”案件,該案中,沈太福以公司名義與投資者簽署“技術(shù)開發(fā)合同”,向社會公眾集資,以高息為誘餌,集資金額高達(dá)10億多元,但當(dāng)時我國刑法尚未有關(guān)于非法集資的規(guī)定,最終,沈太福以貪污罪和行賄罪被定罪。
(二)單行刑法階段
1995年頒布出臺的《商業(yè)銀行法》首次出現(xiàn)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概念,其第七十九條規(guī)定:“未經(jīng)中國人民銀行批準(zhǔn),擅自設(shè)立商業(yè)銀行,或者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并由中國人民銀行予以取締。”
《商業(yè)銀行法》頒布不久,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出臺了《關(guān)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其中第七條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進(jìn)行了明確規(guī)定,規(guī)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shù)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yán)重情節(ji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直接負(fù)責(zé)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zé)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guī)定處罰。”這是我國以單行刑法的形式首次規(guī)定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這一罪名。
(三)刑法典階段
我國1997年《刑法》修訂后首次規(guī)定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這一罪名,與“集資詐騙罪”、“擅自發(fā)行股票、公司、企業(yè)債券罪”等同屬于“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刑法》明確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侵犯犯罪客體是“金融秩序”,自然人或單位均可以構(gòu)成本罪,但并未具體明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含義。
1998年,國務(wù)院頒布的《非法金融機構(gòu)和非法金融業(yè)務(wù)取締辦法》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變相吸收公眾存款”進(jìn)行了解釋,指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是指未經(jīng)中國人民銀行批準(zhǔn),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出具憑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nèi)還本付息的活動;所稱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是指未經(jīng)中國人民銀行批準(zhǔn),不以吸收公眾存款的名義,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但承諾履行的義務(wù)與吸收公眾存款性質(zhì)相同的活動。”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非法集資解釋》”)規(guī)定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四個構(gòu)成要件,即“未經(jīng)有關(guān)部門依法批準(zhǔn)”、“向社會公開宣傳”、“承諾還本付息”、“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頒布的《關(guān)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就“社會公開宣傳”、“社會公眾”的認(rèn)定等問題進(jìn)行了進(jìn)一步的明確。
二、關(guān)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存廢的爭議
自我國《刑法》規(guī)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以來,由于法律規(guī)定不夠明確,導(dǎo)致學(xué)術(shù)界、司法界對該罪犯罪構(gòu)成等問題爭議較多,如孫大午案的承辦律師在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上書中指出:“刑法第176條未能清楚界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有關(guān)法律法規(guī)未能明確區(qū)分該犯罪行為與合法的民間借貸的界限,增加了中小企業(yè)主在融資過程中的人身自由的風(fēng)險,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經(jīng)濟發(fā)展。”
同時,就是否要廢除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也引發(fā)了廣泛的爭議。一種觀點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廢除“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如全國政協(xié)委員朱征夫提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自1997年刑法規(guī)定以來,已經(jīng)不適應(yīng)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需要,甚至可以說,該罪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建議盡快廢除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對一些在民間融資過程中采取欺騙手段騙取他人財物的行為,司法實踐中可以適用刑法中規(guī)定的集資詐騙罪、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進(jìn)行處罰。另一種觀點則認(rèn)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雖應(yīng)修改但缺不能取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雖然與經(jīng)濟發(fā)展發(fā)生沖突,但是這種沖突只是調(diào)整性的,不能因為出現(xiàn)了與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不適應(yīng)而取消,如果任由企業(yè)吸收資金,脫離有關(guān)金融管理機構(gòu)的監(jiān)管,既有可能導(dǎo)致國家不能及時掌握貨幣的流向,從而沖擊國家的金融秩序。
三、民間金融發(fā)展背景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之再審視
(一)民間金融發(fā)展背景下“非法吸收公眾罪”面臨的挑戰(zhàn)
從1995年我國首次以單行刑法的形式規(guī)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以來,迄今為止已經(jīng)二十年。這二十年來,我國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環(huán)境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民間金融日益活躍,規(guī)模日益擴大,形式也日益豐富。2014年西南財經(jīng)大學(xué)發(fā)布的《中國民間金融發(fā)展報告》顯示“22.3%的家庭有民間負(fù)債。中國家庭民間金融市場規(guī)模為5.28萬億元人民幣。”從民間金融的發(fā)展情況看,現(xiàn)行關(guān)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刑法規(guī)定已呈現(xiàn)出與現(xiàn)實不相適應(yīng)的地方。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與民間金融發(fā)展所需要的財產(chǎn)自由和契約自治不相適應(yīng)。從憲法的角度看,民間金融體現(xiàn)了公民對自己財產(chǎn)權(quán)的自由支配,以及合同雙方當(dāng)事人的契約自治,其本質(zhì)上體現(xiàn)了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內(nèi)在要求,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存在的邊界不清晰問題使之很容易淪為“口袋罪”,這就可能妨害公民的財產(chǎn)自由權(quán)和意思自治,進(jìn)而阻礙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實踐中絕大多數(shù)中小企業(yè)都有過民間借貸的經(jīng)歷,現(xiàn)行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顯然已經(jīng)不適應(yīng)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要,也會不適當(dāng)限制公民的財產(chǎn)自由和意思自治。以孫大午案件為例,孫大午因長期無法從銀行獲取貸款,采取向親朋好友、員工甚至附近村民打借據(jù)的方法籌集資金,被法院認(rèn)定構(gòu)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從孫大午案件,我們可以汲取很多反思,“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邊界到底在哪里?如果為生產(chǎn)經(jīng)營吸收社會資金被認(rèn)定為犯罪行為,那么是否會導(dǎo)致對民間金融的不適當(dāng)壓制呢?
二是與進(jìn)一步推動金融業(yè)深化改革不相適應(yīng)。吸儲放貸是商業(yè)銀行的主營業(yè)務(wù)和基本營利方式,維護(hù)吸儲放貸的權(quán)力實際上維護(hù)的是銀行的壟斷利益。我國傳統(tǒng)金融業(yè)向來“門禁森嚴(yán)”,受政府牌照限制,準(zhǔn)入門檻極高,市場化程度低下,存在競爭不充分的問題。而隨著我國金融改革的深入,必要要求打破銀行業(yè)壟斷發(fā)展的局面,充分引入民間資本,大力發(fā)展民間金融,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罪與非罪的模糊化,在實踐中適用的擴大化無疑對我國金融業(yè)深化改革發(fā)展產(chǎn)生不利的影響。
三是與大眾創(chuàng)新、萬眾創(chuàng)業(yè)的時代要求不相適應(yīng)。由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本身存在的模糊化,導(dǎo)致不能給予民間金融參與者穩(wěn)定的預(yù)期,限制了民間金融從業(yè)者的大膽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是一個民族進(jìn)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fā)達(dá)不竭的動力,創(chuàng)新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明確的規(guī)則,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就像懸在民間金融參與者頭上的達(dá)摩克里斯之劍,在一定程度制約了民間金融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成為民間金融發(fā)展中繞不開的一道坎。
(二)完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相關(guān)建議
對于是否要廢除“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筆者認(rèn)為,在我國當(dāng)前的經(jīng)濟環(huán)境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應(yīng)當(dāng)予以修改完善。
現(xiàn)階段保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必要性在于,目前,從我國金融現(xiàn)有發(fā)展情況看,現(xiàn)階段經(jīng)營存款、放貸業(yè)務(wù)的權(quán)力仍有特許經(jīng)營之必要,需要保持一定門檻,只有經(jīng)過行政許可的商業(yè)銀行等機構(gòu)才可以從事此類業(yè)務(wù),未經(jīng)批準(zhǔn)從事此類業(yè)務(wù),則可能會產(chǎn)生擾亂國家金融秩序的后果,甚至帶來嚴(yán)重的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因此,對于非法吸收存款、放貸的違法行為仍有必要保留刑法規(guī)制,但同時要給合法的民間借貸一定的空間,明確有關(guān)邊界,在自由和秩序之間保持適當(dāng)?shù)钠胶狻?/p>
同時,從上文探討的情況看,目前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確有修改之必要。筆者認(rèn)為,通過修改“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進(jìn)一步明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犯罪構(gòu)成,合理界定民間借貸罪與非罪的界限,將合法的民間借貸排除在刑法調(diào)整范圍之外,避免罪狀模糊帶來的定罪隨意化、泛化等問題,為民間金融發(fā)展提供穩(wěn)定的法律預(yù)期。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修改完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一是在刑法謙抑性原則下修改“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又稱必要性原則,指立法機關(guān)只有在該規(guī)范確屬必不可少——沒有可以代替刑法的其他適當(dāng)方法存在的條件下,才能將某種違反法律秩序的行為設(shè)定成犯罪行為。陳興良教授認(rèn)為,運用刑法手段解決社會沖突,應(yīng)該具備兩個條件:其一,危害行為必須具備相當(dāng)嚴(yán)重程度的社會危害性。其二。作為對危害行為的反應(yīng),刑罰應(yīng)當(dāng)具有無可避免性。根據(jù)刑法謙抑性原則,由于民間金融是為彌補正規(guī)金融體系不足,適應(yīng)和滿足不斷發(fā)展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需要而產(chǎn)生的,具有產(chǎn)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那么刑法對以這一領(lǐng)域的介入就要采取謹(jǐn)慎的態(tài)度,避免不適當(dāng)?shù)剡^度介入這一領(lǐng)域給民間金融發(fā)展帶來不適當(dāng)?shù)母深A(yù),對于這一領(lǐng)域的規(guī)范應(yīng)當(dāng)更多地通過完善民商事法律法規(guī)、行政法規(guī)的方式引導(dǎo)民間金融的健康發(fā)展,而不應(yīng)當(dāng)過度使用刑罰手段介入。正如法學(xué)泰斗江平教授所言,現(xiàn)在許多正常民事法律關(guān)系和民事行為經(jīng)常會被刑法學(xué)家認(rèn)為是刑事犯罪問題而予以對待,從而擴大刑法的解釋范圍,傷害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則,增大了公權(quán)力對私權(quán)利的干預(yù)與制約。從長遠(yuǎn)看,這不利于崇尚“契約自治”的法治社會的健康良性發(fā)展。
二是進(jìn)一步明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犯罪構(gòu)成要件。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罪狀規(guī)定不夠明確是導(dǎo)致司法實踐中該罪不適當(dāng)?shù)財U大化的重要原因,筆者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進(jìn)一步明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犯罪構(gòu)成要件,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所懲罰的行為限定為以放貸為目的吸收公眾存款,擾亂國家正常的金融秩序。而將以合法生產(chǎn)經(jīng)營為目的吸收資金,并且主要用于合法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的行為明確規(guī)定為無罪行為,為合法的民間金融活動留下充分的空間。《非法集資解釋》規(guī)定:“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能夠及時清退所吸收資金,可以免予刑事處罰;情節(jié)顯著輕微的,不作為犯罪處理。”從《非法集資解釋》看,仍然將為從事正常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界定違法犯罪行為,這種解釋難以回答對合法與非法劃分的依據(jù)在哪里。
三是修改完善相關(guān)民商事、行政法規(guī),引導(dǎo)民間金融健康發(fā)展。刑法是保障社會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只有迫不得已時才能使用,而要引導(dǎo)規(guī)范民間金融健康發(fā)展,從法律角度講,主要還是依靠完善相關(guān)的民商事、行政法規(guī),保障正常的民間借貸行為健康有序發(fā)展。我們欣喜地看到,這方面的法律保障越來越健全完善。2015年7月央行等10部委發(fā)布《關(guān)于促進(jìn)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健康發(fā)展的指導(dǎo)意見》提出了一系列鼓勵創(chuàng)新、支持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穩(wěn)步發(fā)展的政策措施。201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關(guān)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法釋[2015]18號)對民間借貸案件中熱點、難點問題進(jìn)行了明確的解釋,為民間借貸健康發(fā)展提供了良好的司法保障。同時,也應(yīng)看到,目前我國關(guān)于民間金融發(fā)展的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中仍然還有一些需要根據(jù)時代發(fā)展與時俱進(jìn)予以修改完善的地方。只有進(jìn)一步建立健全民間金融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在堵住金融犯罪缺口的同時,注意疏通民間金融發(fā)展的渠道,才能真正促進(jìn)民間金融的健康發(fā)展。
[1]陳勇等.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研究報告(2015)[M].中國經(jīng)濟出版社,2015.
[2]郭華.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犯罪概說[M].法律出版社,2015.
[3]袁愛華.民間融資合法化趨勢下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立法完善[J].云南大學(xué)學(xué)報法學(xué)版,2010(1).
[4]劉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擴張與限縮[J].政治與法律,2012(11).
[5]趙星、張曉.論廢除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J].河北學(xué)刊,20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