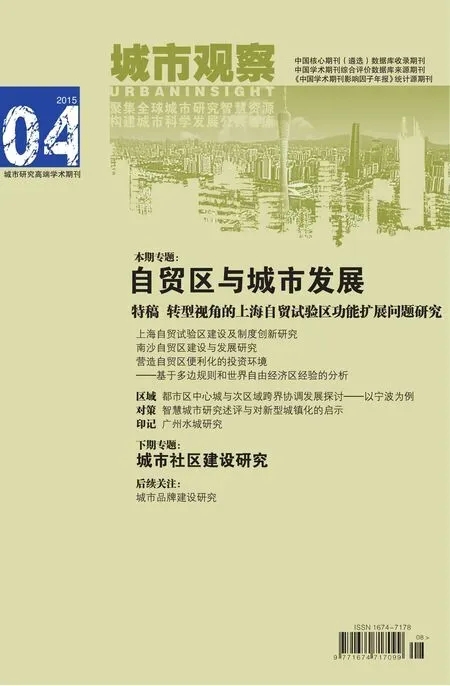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理論、實(shí)踐及其未來(lái)研究方向
◎ 劉 濤
一、引言
2015年6月27日,國(guó)務(wù)院正式批復(fù)同意設(shè)立南京江北新區(qū),至此,我國(guó)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數(shù)量已經(jīng)達(dá)到13個(gè),在傳統(tǒng)的四大板塊區(qū)域都有分布,開(kāi)始成為新一輪拉動(dòng)中國(guó)區(qū)域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引擎。目前關(guān)于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研究,集中在早期相對(duì)成熟的幾個(gè)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如最早成立的浦東新區(qū)(1992年)、濱海新區(qū)(2006年)、兩江新區(qū)(2010年),包括新區(qū)的總體發(fā)展情況[1-2]、管理體制[3]、發(fā)展戰(zhàn)略[4-5]、規(guī)劃實(shí)踐[6-7]等方面的研究,然而尚缺乏關(guān)于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研究進(jìn)展的系統(tǒng)性綜合論述。在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緊密成立的近幾年,加強(qiáng)對(duì)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理論和規(guī)劃實(shí)踐研究顯得尤為必要。因此,本文嘗試對(duì)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相關(guān)理論內(nèi)容和實(shí)踐發(fā)展進(jìn)行綜述研究,以期為今后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進(jìn)一步研究提供基礎(chǔ)。
二、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理論研究
(一)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概念
官方在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批復(fù)的文件中很少定義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目前可供參考的為國(guó)家發(fā)展改革委員會(huì)的部門(mén)文件,認(rèn)為“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是由國(guó)務(wù)院批準(zhǔn)設(shè)立,承擔(dān)國(guó)家重大發(fā)展和改革開(kāi)放戰(zhàn)略任務(wù)的綜合功能區(qū)”[8]。
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于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概念多是從其功能作用進(jìn)行描述的。彭建等人認(rèn)為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作為國(guó)家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總體戰(zhàn)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特殊的政策新區(qū),其成立乃至于開(kāi)發(fā)建設(shè)均上升至國(guó)家戰(zhàn)略,新區(qū)的總體發(fā)展目標(biāo)、發(fā)展定位等由國(guó)務(wù)院統(tǒng)一進(jìn)行規(guī)劃和審批,因而也往往被賦予先行先試的特殊權(quán)限及相關(guān)優(yōu)惠政策,已逐漸成為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重要的“增長(zhǎng)極”,其快速、高效的發(fā)展關(guān)系到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總體戰(zhàn)略部署和安排[9];吳昊天等人認(rèn)為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是由國(guó)務(wù)院批復(fù)的新區(qū),其成立、開(kāi)發(fā)建設(shè)體現(xiàn)國(guó)家戰(zhàn)略,總體發(fā)展目標(biāo)、發(fā)展定位等由國(guó)務(wù)院統(tǒng)一進(jìn)行規(guī)劃和審批;相關(guān)特殊優(yōu)惠政策和權(quán)限由國(guó)務(wù)院直接批復(fù),在轄區(qū)內(nèi)實(shí)行更加開(kāi)放和優(yōu)惠的特殊政策,鼓勵(lì)進(jìn)行各項(xiàng)制度改革與創(chuàng)新的探索工作, 是我國(guó)參與經(jīng)濟(jì)全球化、參與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的一種空間決策,是國(guó)家核心增長(zhǎng)極和區(qū)域戰(zhàn)略發(fā)展支點(diǎn)[10];彭小雷等人認(rèn)為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是根據(jù)國(guó)家發(fā)展戰(zhàn)略需要,由國(guó)務(wù)院批準(zhǔn)設(shè)立的新建城區(qū)。新區(qū)的總體發(fā)展目標(biāo)、定位由國(guó)務(wù)院主導(dǎo),相關(guān)特殊優(yōu)惠政策和權(quán)限由國(guó)務(wù)院直接批復(fù),在轄區(qū)內(nèi)實(shí)行更加開(kāi)放和優(yōu)惠的特殊政策,鼓勵(lì)新區(qū)進(jìn)行各項(xiàng)制度改革與創(chuàng)新的探索工作[11]。
(二)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特征
梳理當(dāng)前我國(guó)已經(jīng)成立的13個(gè)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基本情況,總結(jié)出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具有以下幾個(gè)特征:
1.從沿海到內(nèi)陸梯度開(kāi)發(fā)。目前已批復(fù)的13個(gè)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按時(shí)間先后呈現(xiàn)出“東部—西部—東北—中部”的特點(diǎn),體現(xiàn)出從沿海到內(nèi)陸梯度開(kāi)發(fā)的趨勢(shì)。
2.依托城市群輻射帶動(dòng)。已有的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都是依托城市群或特大城市[9],如浦東新區(qū)依托上海,濱海新區(qū)依托京津冀,南沙新區(qū)依托珠三角,兩江新區(qū)和天府新區(qū)依托成渝城市群,湘江新區(qū)依托長(zhǎng)株潭城市群等。
3.空間規(guī)模普遍較一般的新區(qū)大。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規(guī)模一般在800-2000平方公里,相當(dāng)于一個(gè)中等面積的縣域規(guī)模,比一般的城市新區(qū)、開(kāi)發(fā)區(qū)規(guī)模都要大。
4.行政架構(gòu)由管委會(huì)+行政區(qū)向完全的行政區(qū)過(guò)渡。目前已批復(fù)的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中,大部分在成立初期采用管委會(huì)+行政區(qū)(市)雙重管理模式,等到新區(qū)成熟后逐漸過(guò)渡到完全的行政區(qū)(市)管理模式[10],如浦東新區(qū)、濱海新區(qū)走過(guò)的就是以上路徑。
(三)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功能
根據(jù)國(guó)家發(fā)改委出臺(tái)的《關(guān)于促進(jìn)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健康發(fā)展的指導(dǎo)意見(jiàn)》,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功能是全方位擴(kuò)大對(duì)外開(kāi)放的重要窗口、創(chuàng)新體制機(jī)制的重要平臺(tái)、輻射帶動(dòng)區(qū)域發(fā)展的重要增長(zhǎng)極、產(chǎn)城融合發(fā)展的重要示范區(qū)[8]。
葉姮等人利用潛力評(píng)價(jià)方法,將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分為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型、全國(guó)中心型、區(qū)域中心型和特殊戰(zhàn)略型等4種功能模式[12]。吳昊天等人將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功能分為改革紅利釋放區(qū)、改革探索試驗(yàn)區(qū)、區(qū)域核心增長(zhǎng)極、產(chǎn)城融合示范區(qū)、綠色生態(tài)宜居地[10]。王禮剛和覃思認(rèn)為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功能主要是增長(zhǎng)極作用[13-14]。
(四)小結(jié)
根據(jù)前人的研究,本文認(rèn)為“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是由國(guó)務(wù)院批準(zhǔn)設(shè)立,承擔(dān)國(guó)家重大發(fā)展和改革開(kāi)放戰(zhàn)略任務(wù)的一種特殊的政策新區(qū);它享有更加開(kāi)放的特殊權(quán)限和優(yōu)惠政策,其發(fā)展方向和遠(yuǎn)期目標(biāo)等由國(guó)務(wù)院統(tǒng)一規(guī)劃和審批,是區(qū)域發(fā)展的戰(zhàn)略性空間和平臺(tái),體現(xiàn)國(guó)家戰(zhàn)略意圖”。

表1 我國(guó)的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基本情況

(續(xù)表)
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特征體現(xiàn)為:從沿海到內(nèi)陸梯度開(kāi)發(fā),依托城市群或特大城市輻射帶動(dòng),空間規(guī)模普遍較一般的城市新區(qū)大,行政架構(gòu)由管委會(huì)+行政區(qū)向完全的行政區(qū)過(guò)渡,具有先行先試的體制優(yōu)勢(shì)。
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功能是:全方位擴(kuò)大對(duì)外開(kāi)放的重要窗口、創(chuàng)新體制機(jī)制的重要平臺(tái)、輻射帶動(dòng)區(qū)域發(fā)展的重要增長(zhǎng)極、產(chǎn)城融合發(fā)展的重要示范區(qū)。
三、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規(guī)劃實(shí)踐研究
(一)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規(guī)劃研究
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規(guī)劃研究,主要從功能定位、發(fā)展目標(biāo)、空間布局、土地開(kāi)發(fā)模式等總體規(guī)劃和專(zhuān)項(xiàng)規(guī)劃層面進(jìn)行研究,特別強(qiáng)調(diào)產(chǎn)城融合、生態(tài)智慧等理念的融入。如浦東新區(qū)從規(guī)劃布局優(yōu)化、用地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綜合交通設(shè)置等方面對(duì)新區(qū)總體規(guī)劃修編實(shí)現(xiàn)產(chǎn)城融合,促進(jìn)轉(zhuǎn)型發(fā)展進(jìn)行了研究[15];南沙新區(qū)規(guī)劃設(shè)計(jì)實(shí)踐探討生態(tài)、智慧和休閑等城市發(fā)展理念, 在不同空間尺度中落實(shí)這些理念指導(dǎo)下的空間范式, 并在各種城市系統(tǒng)中如何進(jìn)行系統(tǒng)導(dǎo)控, 形成功能集、空間集、系統(tǒng)集三大集合相互匹配的新型發(fā)展范式的規(guī)劃實(shí)踐[16];四川天府新區(qū)規(guī)劃在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優(yōu)先的理念基礎(chǔ)上,融入產(chǎn)城融合思想,創(chuàng)新產(chǎn)城單元規(guī)劃理念,建立解決交通擁堵、城市內(nèi)澇、環(huán)境污染三大問(wèn)題的支撐體系[7]。此外,晁恒等人以尺度重構(gòu)為視角,基于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成立、發(fā)展的邏輯演變,探討“多規(guī)合一”的空間規(guī)劃對(duì)于新區(qū)發(fā)展的作用機(jī)理和規(guī)劃路徑選擇[17]。
(二)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
單個(gè)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也是學(xué)術(shù)界研究的熱點(diǎn),從借鑒早前成立的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經(jīng)驗(yàn)入手,同時(shí)結(jié)合自身的實(shí)際條件。如重慶兩江新區(qū)借鑒浦東新區(qū)和濱海新區(qū)的經(jīng)驗(yàn),提出了六大開(kāi)發(fā)開(kāi)放戰(zhàn)略[18];西咸新區(qū)從城市發(fā)展形態(tài)、產(chǎn)業(yè)布局、生態(tài)保護(hù)、城鄉(xiāng)統(tǒng)籌和社會(huì)建設(shè)等方面探討了西咸新區(qū)在創(chuàng)新城市發(fā)展方式,建設(shè)中國(guó)特色新型城鎮(zhèn)化的創(chuàng)新和實(shí)踐[19];天府新區(qū)借鑒我國(guó)已有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建設(shè)模式和經(jīng)驗(yàn),并結(jié)合天府新區(qū)所面臨的客觀實(shí)際進(jìn)行探索與創(chuàng)新,形成適合天府新區(qū)的建設(shè)模式和路徑[20];蘭州新區(qū)以國(guó)家發(fā)改委發(fā)布的《蘭州新區(qū)建設(shè)指導(dǎo)意見(jiàn)》為基礎(chǔ),從六大方向提出了發(fā)展戰(zhàn)略[21];舟山群島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基于對(duì)“中央、地方”不同訴求的分析來(lái)判斷其戰(zhàn)略地位,并從發(fā)展戰(zhàn)略中理清國(guó)家戰(zhàn)略和地方戰(zhàn)略,從而協(xié)調(diào)好二者的關(guān)系,更好地做好戰(zhàn)略判斷和方向引導(dǎo)[22];青島西海岸新區(qū)則從青島在國(guó)家發(fā)展總體格局中的戰(zhàn)略地區(qū)和海洋強(qiáng)國(guó)戰(zhàn)略出發(fā),研判新區(qū)的發(fā)展戰(zhàn)略[23]。
(三)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對(duì)國(guó)家重大戰(zhàn)略的響應(yīng)研究
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是國(guó)家戰(zhàn)略在空間上的部分體現(xiàn),其與國(guó)家重大戰(zhàn)略的響應(yīng)關(guān)系也成為學(xué)術(shù)界研究的對(duì)象。彭小雷等人從新型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角度解析西部地區(qū)的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發(fā)展對(duì)國(guó)家戰(zhàn)略的作用[11];蘭州新區(qū)針對(duì)“一帶一路”所形成的開(kāi)放新體系,從功能定位、開(kāi)放視野、開(kāi)放層次、開(kāi)放方向及極化帶動(dòng)等方面做出積極的適應(yīng)性調(diào)整,并通過(guò)戰(zhàn)略協(xié)同、空間優(yōu)化、要素集聚、溝通協(xié)調(diào)四個(gè)途徑,實(shí)現(xiàn)與“一帶一路”的全面對(duì)接[24]。
(四)小結(jié)
目前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規(guī)劃實(shí)踐研究主要集中在規(guī)劃研究、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對(duì)國(guó)家重大戰(zhàn)略的響應(yīng)研究等幾個(gè)方面。然而,由于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成立歷史較短,大部分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成立于近5年,因此關(guān)于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規(guī)劃建設(shè)大都處于初期階段,缺乏對(duì)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深入和系統(tǒng)性研究。
從加強(qiáng)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理論和實(shí)證研究的系統(tǒng)性方面看,諸如關(guān)于“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在全國(guó)國(guó)土開(kāi)發(fā)空間的綜合布局如何?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最優(yōu)空間規(guī)模和區(qū)位選址如何?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與其所依托的城市(群)的相互作用、空間互動(dòng)關(guān)系如何?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產(chǎn)業(yè)發(fā)展路徑如何?”等問(wèn)題都還處于空白研究狀態(tài)。在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密集批復(fù)的近幾年,為更好地指導(dǎo)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規(guī)劃建設(shè),發(fā)揮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對(duì)區(qū)域發(fā)展的帶動(dòng)作用,上述問(wèn)題應(yīng)該受到學(xué)術(shù)界的重視,成為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未來(lái)研究的方向之一。
四、結(jié)語(yǔ)
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作為我國(guó)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區(qū)域發(fā)展的新興開(kāi)發(fā)開(kāi)放平臺(tái),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性和前瞻性。由于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在我國(guó)的發(fā)展歷史較短(除浦東新區(qū)外),使得當(dāng)前關(guān)于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成熟經(jīng)驗(yàn)和模式不多,但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于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功能定位和戰(zhàn)略目標(biāo)還是基本達(dá)成一致的:即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是那些依托城市群,具有特殊功能,代表國(guó)家或區(qū)域,實(shí)現(xiàn)特定目標(biāo)的,具有戰(zhàn)略性的區(qū)域空間發(fā)展平臺(tái)。
目前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規(guī)劃實(shí)踐研究主要集中在規(guī)劃研究、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對(duì)國(guó)家重大戰(zhàn)略的響應(yīng)研究等幾個(gè)方面。在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如火如荼發(fā)展的當(dāng)前,近5年就有十余個(gè)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先后成立,而且未來(lái)將會(huì)有更多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成立。因此,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有關(guān)理論和規(guī)劃實(shí)踐研究已經(jīng)刻不容緩,將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新常態(tài)下區(qū)域發(fā)展研究的新主題,為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的健康、可持續(xù)發(fā)展提供科學(xué)支撐。
[1]余典范.上海浦東新區(qū)與天津?yàn)I海新區(qū)、深圳特區(qū)的比較研究[J].上海經(jīng)濟(jì)研究,2007(3):13-20.
[2]孟廣文,杜英杰.天津?yàn)I海新區(qū)建設(shè)成就與發(fā)展前景[J].經(jīng)濟(jì)地理,2009(2):193-199.
[3]王佳寧,羅重譜.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管理體制與功能區(qū)實(shí)態(tài)及其戰(zhàn)略取向[J].改革,2012(3):21-36.
[4]俞樹(shù)彪.舟山群島新區(qū)推進(jìn)海洋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戰(zhàn)略思考[J].未來(lái)與發(fā)展,2012(1):104-105.
[5]彭勃.舟山群島新區(qū)港口區(qū)位勢(shì)評(píng)價(jià)及其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基于舟山、寧波、上海三港區(qū)位勢(shì)的實(shí)證分析[J].經(jīng)濟(jì)地理,2013(6):114-118.
[6]吳志鵬.三大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現(xiàn)行政策比較及對(duì)浙江舟山群島新區(qū)建設(shè)的啟示[J].發(fā)展研究,2011(12):56-58.
[7]邱建.四川天府新區(qū)規(guī)劃的主要理念[J].城市規(guī)劃,2014(12):84-89.
[8]國(guó)家發(fā)改委.關(guān)于促進(jìn)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健康發(fā)展的指導(dǎo)意見(jiàn)(發(fā)改地區(qū)[2015]778號(hào))[EB/OL].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504/t20150423_689064.html
[9]彭建,魏海,李貴才等.基于城市群的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區(qū)位選擇[J].2015(1):3-14.
[10]吳昊天,楊鄭鑫.從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戰(zhàn)略看國(guó)家戰(zhàn)略空間演進(jìn)[J].城市發(fā)展研究,2015(3):1-10.
[11]彭小雷,劉劍鋒.大戰(zhàn)略、大平臺(tái)、大作為——論西部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發(fā)展對(duì)新型城鎮(zhèn)化的作用[J].城市規(guī)劃,2014,(增刊2):20-26.
[12]葉姮,李貴才,李莉等.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功能定位及發(fā)展建議——基于GRNN潛力評(píng)價(jià)方法[J].經(jīng)濟(jì)地理,2015(2):92-99.
[13]王禮剛.基于增長(zhǎng)極理論的重慶兩江新區(qū)發(fā)展研究[J].重慶交通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科版),2012(4):61-64.
[14]覃思.基于增長(zhǎng)極理論的蘭州新區(qū)發(fā)展探究[J].企業(yè)技術(shù)開(kāi)發(fā),2013(2):19-20.
[15]許健,劉璇.推動(dòng)產(chǎn)城融合,促進(jìn)城市轉(zhuǎn)型發(fā)展——以浦東新區(qū)總體規(guī)劃修編為例[J].浦東規(guī)劃建設(shè),2012:13-17.
[16]盧慶強(qiáng).轉(zhuǎn)型時(shí)期國(guó)家新區(qū)規(guī)劃實(shí)踐——以南沙新區(qū)為例[C].2012年中國(guó)城市規(guī)劃年會(huì)論文集.
[17]晁恒,林雄斌,李貴才.尺度重構(gòu)視角下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多規(guī)合一”的特征與實(shí)現(xiàn)途徑[J].城市發(fā)展研究,2015(3):11-18.
[18]田代貴.重慶兩江新區(qū)開(kāi)發(fā)開(kāi)放戰(zhàn)略——借鑒浦東新區(qū)和濱海新區(qū)經(jīng)驗(yàn)[J].重慶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2011(1):34-42.
[19]王軍.西咸新區(qū)創(chuàng)新城市發(fā)展方式的思考[J].城市規(guī)劃,2014(6):73-76.
[20]民盟成都市委課題組.我國(guó)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建設(shè)模式比較及對(duì)天府新區(qū)的借鑒和啟示[J].四川省社會(huì)主義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2(4):39-43.
[21]張建君.蘭州新區(qū)的政策轉(zhuǎn)化及開(kāi)發(fā)研究[J].開(kāi)發(fā)研究,2013(2):30-33.
[22]鄭德高,陳勇,王婷婷.舟山群島國(guó)家新區(qū)發(fā)展戰(zhàn)略中的“央、地”利益權(quán)衡分析[J].城市規(guī)劃學(xué)刊,2012(7):1-5.
[23]陳維民.青島西海岸新區(qū)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J].城市,2015(3):21-27.
[24]滕海峰.蘭州新區(qū)對(duì)接一帶一路的戰(zhàn)略響應(yīng)與路徑選擇[J].學(xué)術(shù)縱橫,2015(4):7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