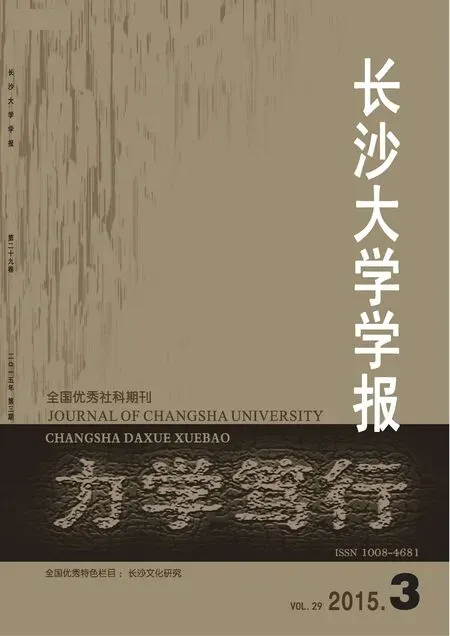框架視角下的翻譯推理過程——以《古文觀止》英漢對比為例
李慧敏
(安徽大學外語學院,安徽合肥230601)
一 作為一種認知結構的框架
框架(frame)這個概念最早出現于心理學。Minsky最早把框架定義為表征某一固定情景的事實結構[1]。Fillmore將框架理論引入語言學領域,提出了框架語義學,他認為框架是能與場景的原型實例建立聯系的一系列語言選擇[2]。后來框架逐漸向認知語言學的方向發展。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是人類的一種認知能力,與人們感知和認識世界的認知過程聯系緊密。1985年Fillmore將框架定義為“知識的特定統一框架或對經驗的連貫圖解”[3]。1992年Fillmore說框架是認知結構,“對文字蘊涵概念所預設的知識”[4]。框架可以用來描寫認知環境,是關于特定類型的場景知識的概念系統。系統中的概念相互聯系,一個概念會激活其他相關概念和認知視角以及背景知識。
作為一種認知結構,框架概念與語境和文化分不開。Ungerer和Schmid認為框架存在于真實世界多種多樣的情景中,是人類共有的普遍認知現象。Talmy提出了事件框架(event-frame)。事件框架被Talmy定義為:“被一起激活或相互激活的一組概念成分及其相互關系,存在于一個事件框架中或構成了一個事件框架”[5]。Tamly的位移事件框架主要包含這幾個認知成分:主體、路徑、位移、背景以及原因和方式。事件框架中特定部分得到凸顯的過程被稱為“開啟注意力視窗”,沒有得到凸顯的成分則被背景化,稱作“隔斷”。注意力視窗同樣適用于致使鏈事件框架。致使事件包含一系列階段,由更基本的次事件組成。其中某些階段可能會開啟注意力視窗,某些階段則被隔斷。
框架是一種認知結構,反映了人們感受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為語篇的分析和解讀提供了一種重要工具。我們需要以外部世界的各種知識為基礎進行推理,從已有的知識結構出發去觀察和預測。框架內包含了基于經驗并存儲在記憶中的預期知識,在特定的語境下激活所需要的認知范疇,使得推理能夠順利展開。本文選擇《古文觀止》英文版(由羅經國翻譯)中的部分篇章,運用事件框架的理論來分析譯者在解讀原文過程中所做的推理。文言文的語言凝煉、濃縮,因此在解讀原文時更加需要一定的推理。通過對比原文和譯文中構建的事件框架,本文試圖發現譯者對原事件框架做出了哪些改變和什么類型的改變,并探討這些改變反映出的推理過程。
二 位移事件框架分析
(一)對位移路徑的改變
例1.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出自《滕王閣序》)
Ranges upon ranges of green mountain rise as high as the sky.The red glow in the water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richly painted tower that seems hovering in the air.

a.原位移事件框架

b.改變后的位移框架事件
該句總共涉及了兩個位移框架事件。第一個位移框架事件在原文中如下:主體是蔥翠的山巒,“上”和“出”激活了位移的方式和路徑,“重霄(天空)”作為背景。英語版本里對這一位移事件的解讀基本遵循了這一框架,位移主體和背景均相同,“rise”表示的位移動作是對“出”的具體化呈現,“as high as”表明位移的路徑是“向上”。
第二個位移框架事件相對較為復雜,在原文中表現為一個虛構路徑,即用想象的動態路徑來表達靜態兩者間的位置關系。在這個事件中里,“飛閣流丹”作為位移的主體,“下”表示了虛構路徑的方向,“臨”傳達出位移的動作:“reach(downward)to go near”;“無地”的“無”雖然表面上是個否定詞,卻沒有起到真正否定的效果,反而引出了后面的“地”,“地”就是整個位移的背景,沒有被否定掉。樓閣向下延伸,仿佛接觸不到地面似的:這是用夸張的手法突顯樓的高聳,以俯瞰的視角描繪了一個從樓閣到底層地面的虛擬路徑。地面和樓閣均為靜態,移動的是視線。所以原框架中的位移路徑是虛擬的、自上而下的,參照的背景是大地。
上面的位移框架事件在譯文中進行了大幅度的改變。首先,主體中加入了“倒影”的因素,由水面上閃爍流動的倒影引出實物,也就是位移真正的主體樓閣。這樣的引申建立在對原文“流丹”的推理上,“丹漆”原本不會流動,譯者在分析文本時從“流”字出發,展開聯想引入了“倒影”。雖然“流丹”本身不會流動,但它的倒影在水中可以隨著波紋起伏晃動,滿足“floating”一詞達到的效果。
再看位移。其實原框架中為位移的動作提供了幾個潛在的選項,“飛”、“流”以及“臨”,原文是以“臨”作為被凸顯的位移動作的,“飛”和“流”只是簡單地用作修飾成分,在整個位移事件中不占主導地位。然而譯者卻更換了原位移事件中的位移動作,從幾個可能的選項中選取“飛”作為他所要構建的框架中最主要的位移,并進一步細化成“hover”;由“hover”所激活的路徑是“upward”,與原框架中向下的路徑相反,參照的背景也隨之改變,由“大地”變為了“高空”。可見,原框架中由俯瞰視線構建的虛擬路徑在這里正好被反了過來,變成由下往上,“下”由前面的“倒影”可以間接推出來。從倒影向上看去,樓閣仿佛直升入天,這是新的框架里構建的位移路徑所帶來的畫面感。
兩個框架中的位移事件都是為了描寫樓閣的高聳入云,通過改變后的位移框架,我們可以看出譯者在分析原文時的推理過程。譯者主要改造的是第二個位移事件,從位移的動作開始,后面所涉及的路徑和背景為了與其匹配,均與原文形成反向對照。譯者選擇將俯瞰視角變為仰視視角,將參照背景由大地變為天空,這樣構造出的虛擬路徑同樣能表現樓的“高”。原框架中的兩個位移呈相反方向;而改寫后框架中的兩個位移路徑一致,達到視角一致的流暢效果。這可能也是譯者變更的原因之一。
(二)對位移背景和主體的改變
例2.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出自《滕王閣序》)
A solitary wild duck flies alongside the multi-colored sunset clouds,and the autumn water is merged with the boundless sky into one hue.

a.原位移事件框架

b.改變后的位移事件框架
原文中只有一個位移事件框架,主體是落霞和孤鶩,位移由動詞“飛”表示,后面的秋水和長天作為大的背景,路徑沒有具體給出。這個位移事件被譯者分解成了兩個單獨的位移事件。在譯文的框架里,譯者為第一個事件選取的主體是“solitary duck”,而原先同樣享有主體地位的“sunset clouds”則虛化作背景。譯者的處理反映了他的推理:孤鶩飛符合常理,落霞不能“飛”,但可以作為背景襯托飛的動作并突出飛的路徑:在大片的晚霞中,孤獨的野鴨沿著晚霞的蹤跡飛去。這樣的處理使得位移事件更加趨向邏輯化。
而原先作為背景的“秋水長天”則出現在新的框架中構成新的位移事件。“秋水”作為主體,位移的動作體現在動詞“merge”上,即與“boundless sky”融為一體,“into”表明了“融”的方向。譯者把原文中的背景成分單獨分化出來,以其為主體構成另外的位移事件,增加了整個畫面的動態感。而且新框架中的兩個位移正好形成對應,“云”和“天”作為浩瀚的大背景,主體分別為體積較小的“鶩”和“水”,于是兩個位移事件,一前一后,都是用大背景襯托和突出小主體,增添了開闊感。由此可見,譯者在原框架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展開和補充,完善了原文中不具備的一些細節。這些原本沒有得到呈現的細節完全具有存在的潛能,譯者可以選取某一背景將其前景化,也可以運用推理為原位移動作補充具體的路徑。
三 致使鏈事件框架分析
(一)對事件框架注意力視窗的擴充
例3.(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光。(出自《后赤壁賦》)
You are striking the crystal clear water lit by the bright moon and pushing our boat ahead against the shimmering currents.

a.原致使事件框架中開啟的注意力視窗
原致使鏈框架中僅僅開啟了施事和結果兩個注意力視窗,中間的視窗都被隔斷了。這種不連續的視窗開啟一般情況下不會影響理解,因為被隔斷的一系列事件都可以經由推理得出,即初始引發事件和事件的最終目標實現之間沒有得到凸顯的步驟是可以通過推理還原的。譯者顯然采取了這種做法。首先看原文中的致使鏈事件。施動者采取的動作“擊空明”,即用船槳擊打澄凈、空靈的水面,這個動作的目的是“溯流光”。譯者在處理這個事件時,在主事件和結果之間增添了一些次事件,把原先被隔斷的注意力視窗重新開啟。

b.改變后的致使事件框架中開啟的注意力視窗
施動者采取動作“striking”后,順帶引出了一個不是很重要的次事件來解釋“空明”中的“明”,即水面是被月光照亮的。這是譯者根據語境所做的推測,因為前文有提到月亮的出現,所以晚上的江水在月光的照射下顯得通透明亮也不足為奇。接著,“push the boat”是致使鏈當中的中間環節,船槳劃過平靜的水面,所形成的作用力推動著小船。這個推動力帶來的一個結果,同時也是倒數第二個次事件,就是使小船在推力的作用下逆著水流而行。譯者通過一個“ahead”又開啟了新的結果視窗,前面所有中間事件導致的最終結果是小船(迎著水流)前進。
譯者在新構建的事件框架里開啟多重注意力視窗,將省略的中間環節的次事件一一展開呈現,使原文里的事件得到了細致化的擴充和豐富。這個致使鏈框架的完善和細化需要一個推理的過程。原文呈給譯者的僅是兩個分開的階段,譯者通過“劃槳”這一動作所激活的認知框架和相關常識,能夠把先前沒有得到突顯的各個階段表現出來。這些隱含在整個劃槳事件里的過程可以通過選擇性的彰顯,使事件得到更明晰化的描述。
(二)對事件框架的合成
例4.煙光凝而暮山紫。(出自《滕王閣序》)
At dusk the rays of the setting sun,condensed in the evening haze,turn the mountains purple.

a.原事件框架

b.改變后的致使鏈事件框架
原文中的框架為兩個簡單獨立的事件,煙光凝結,暮山變紫,它們之間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因果關系,但是譯者顯然從中推測出這種潛在的關系,把因果關系施加在這兩個事件上,構成一個致使鏈框架。施動者是“煙光”,施動的條件背景由“落日”給出,即在黃昏的特殊背景下,落日產生的光線才能營造出后面的效果。落日是施動者“rays”存在的原因。施動者“rays”通過在暮色的模糊煙氣中凝結這一動作,引發了后面的事件。這個主事件得到了細節上的補充,譯者從“煙”當中推測出“evening haze”的存在,(光線凝結)形成一層朦朧的薄紗。
倒數第二個次事件的關鍵詞是“turn”,譯者引入“turn”這個詞,立刻明確了施動者“rays”和受事者“mountains”之間的關系:光線改變了山的顏色,最后的結果就是山變紫。這個致使鏈事件是譯者在推理的基礎上把兩個獨立事件合成而來,以第一個事件中的主體為施動者,第二個事件中的主體為受事,并選擇性地開啟了一些中間次事件的注意力視窗,補充了因果事件的過渡階段,為事件提供了邏輯合理性。
(三)對事件框架的重新組合
例5.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出自《前赤壁賦》)
I let the boat drift freely as it continued its motion across the vast expanse of the river.

a.原致使事件框架

b.原位移事件框架

c.改變后的致使位移事件框架
原文中包含了兩個事件框架,“縱一葦之所如”表現為致使事件框架,“凌萬頃之茫然”表現為位移事件框架。致使事件框架中開啟了兩個注意力視窗,“我”是施動者,采取的行動是“縱”,即任由、放任,結果為小船隨意飄蕩。在位移事件框架中,小船是主體,“凌”表示了位移的動作和路徑:“rise above”,“萬頃茫然”作為位移的背景。這兩個事件框架彼此之間有潛在的聯系,在譯文中得到了更明晰的表達,譯者把致使事件和位移事件結合在一起,表現為一個致使位移事件框架。在這個框架中,原致使事件中的施動者“我”成為了致使位移事件的原因,小船是主體,介詞“across”激活了路徑,背景未變,仍然為“expanse of water”,位移的動作是“drift”。
原位移框架中的事件更偏向靜態的呈現,“above(凌)”表示的路徑更偏向一種位置上的說明,而在后來的致使位移框架中,動態的位移得到了更突出的展示,位移的動作和路徑都更加具體化,“drift”和“across”表現出小船飄過茫茫無際水面的畫面。致使事件和位移事件組合起來,形成一個整體的框架,加深了因果的邏輯性,能夠更加連貫地表達場景。框架的組合也反映出譯者對原文中兩個事件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所做出的推理。
本文采用框架理論,通過兩個主要的事件框架,即位移事件框架和致使鏈事件框架,對《古文觀止》中選取的篇章進行分析。將原文中的事件框架和經過譯者改變后的事件框架進行對比后,可以得出譯者在理解原文的過程中所做的推理。譯者運用推理,把原文中沒有明確呈現的潛在成分和隱含關系表達出來,這種擴充和改變可以體現在框架事件中,比如對位移事件框架的路徑、位移、背景和主體等成分的改寫,以及對致使鏈事件框架中注意力視窗的更改、對事件的合成和組合等。
[1]Minsky Marvin.A framework for representing knowledge[A].P H Winston.The psychology of computer vision[C].New York:McGraw-Hill,1975.
[2]Fillmore Charles C.An alternative 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A].Cogen C,Thompson H,Thurgood G,et al.Proceedings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C].Berkeley: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1975.
[3]Fillmore Charles C.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J].Quaderni di Semantica,1985,(6).
[4]Fillmore Charles C,Beryl T,Atkins.Toward a frame-based organization of the lexicon:The semantics of RISK and its neighbors[A].Lehrer A,Kittay E.Frames,fields,and contrast:New essays in semantics and lexical organization[C].Hillsdale: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2.
[5]Talmy Leonard.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M].Cambridge:MIT Pres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