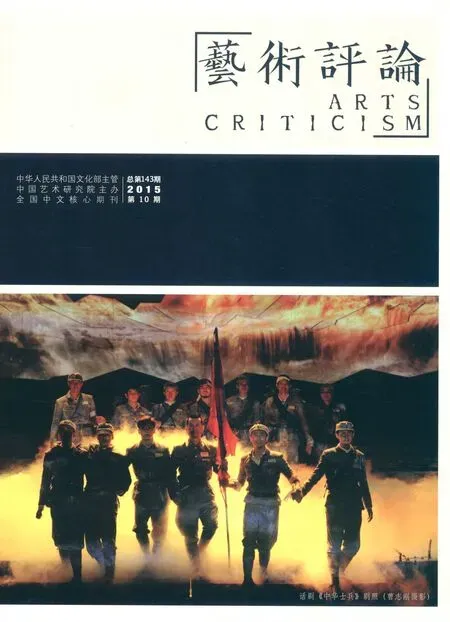《三體》:我們時代的隱喻和精神史詩
徐 勇
《三體》:我們時代的隱喻和精神史詩
徐 勇

劉慈欣
最近一段時間,隨著劉慈欣的《三體》(即《地球往事》三部曲:《三體》《黑暗森林》和《死神永生》,俗稱《三體》,下同)獲得世界科幻文學大獎雨果獎,《三體》也逐漸進入學術研究的殿堂(所謂登堂入室),而不僅僅被視為亞文學或類型文學的代表。這當然是中國科幻文學的極大成功,但若僅僅把它視為科幻文學的崇高經典,或是通過納入純文學的范疇以抬高其地位,則又是歧途誤區。因為顯然,《三體》的出現及其提出的問題,早已超出了科學范疇本身,也非科幻文學或者說純文學所能涵蓋。對于《三體》,其內容的豐富和駁雜,以及視野的宏闊,是任何一種單一的文類所不能比肩的。但也是這駁雜,常常使得我們顧此失彼、左右徘徊。這就有必要采取抽絲剝繭的方法。就《三體》而言,它的核心問題在于,它提出一系列帶有根本性的終極問題,但又借助于科幻這一文體形式表現出來,其中的悖論和矛盾為我們進入此一文本提供了便捷且行之有效的角度。
一
《三體》的出現,無疑與中國作為大國崛起有著某種時間上同步性的特征,這從其中拯救世界和人類文明的英雄主人公汪淼、羅輯和程心等皆為中國人即可以看出。這一時代性征反映了作者對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充分信心及其因之而來的世界政治格局必然重整的期望,但另一方面我們從小說中又感到一種作者所特有的對人類的深深的絕望以及因之而來的深刻反思。有意味的是,這一反思,早已超出人類中心主義的高度,也非民族國家的本位主義立場,這一反思,因其借助于科幻文學這一文類和形式,毋寧說帶有宇宙的視角,因而也更具有終極性和根本性。
就歷史的角度看,自近現代以來,中國的先賢們(諸如梁啟超、魯迅等)一直都在崇尚科學的旗幟下呼喚科學幻想小說的到來;“五四”前后,乃至80年代初,皆曾出現過科幻文學寫作的浪潮。但我們很快會發現,中國科幻文學的寫作與科學的發展之間始終存在某種若即若離的關系。換言之,它雖借助于科學的想象而發展壯大,但也存在著對科學的反思乃至批判。這一情況表明中國的科幻文學還未充分發展就已表現出反現代性的“審美現代性”的面向,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中國作為后發展國家所不得不面對的:我們在“向科學進軍”的時候,科學在西方也已顯示出不可化解的矛盾。這是我們理解《三體》的重要前提。
事實上,在《三體》之外,劉慈欣一直都在展開對科學技術本身的思考。《時間移民》通過設計一個面向未來不斷展開的時間旅行的結構,以表明機器文明具有“非人”或“反人類”的特征;但劉慈欣并沒有停留于此,而這,也是他區別于中國其他科幻作家的地方。與王晉康、韓松、何夕等都表現出對科學技術的“異化”作用的反思和批判不同的是,劉慈欣以此為起點,通過把諸如人道主義、愛與美及其人性之惡等等人類哲學命題置于宇宙的高度和層面展開,從而在根本上表現出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質疑和對人類諸命題的反思。
《三體》的反思性首先表現在其特有的結構和文體中。這從其書名《地球往事》即可以看出,這是把地球的故事放在宇宙的層面加以表現,地球的故事因而具有了宇宙社會學的含義,而小說時空結構關系上的“將來過去時”,也賦予《三體》整體上的反思總結之意。所謂“將來過去時”,這是劉慈欣獨創的一種時態,其得來顯然有賴于科幻文學的文體本身及其想象的力量。這里所謂的“往事”并不是今天之前的“往事”,而是從將來的角度回溯中的“往事”,這一“往事”發生在今天(當下)之后地球毀滅(即將來)之前。時間在這里是以“今天—過去—將來”的邏輯演變的。換言之,這樣一種敘述,是在今天和將來之間的兩端游移,這是一種立足于當下且以將來為起點,從將來的角度對當下展開的反思。當下意識、將來視角和反思立場的結合使得這一系列小說具有了某種超出一般科幻文學和純文學的高度。
但《三體》并非僅僅意在反思科學,它把對科學的反思糅合進對歷史和人性的反思之中,其后來進入到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某種程度上也正源自于此。如果說敘述的起點并非無關緊要的話,那么我們會發現,人類的一系列災難皆源自于人類自身:人性的惡是人類毀滅自身的根源。通過閱讀《地球往事》第一部《三體》,我們知道,人類文明的一系列災難皆肇始于葉文潔向外太空發送的地球文明信號,由此引發了三體文明同人類文明的宇宙大戰,以及隨之而來的太陽系的毀滅。表面看來,這是葉文潔的一次極其偶然的行為而引發的人類危機,她是人類的罪魁禍首;但通過梳理她的人生經歷便會看到,是人性之惡與歷史(“文革”)之痛使她產生對人類文明的懷疑和絕望,只不過,她所期盼的解決之道不是己疾自醫,而是寄希望于更高級的文明的介入:“到這里來吧,我將幫助你們獲得這個世界,我的文明已無力解決自己的問題,需要你們的力量來介入。”她在發向飛向太陽的信息中如是說。
但更高級的文明就真地能夠拯救地球文明嗎?顯然這是劉慈欣在這部系列小說中始終思考的核心問題所在。確乎,人類自身的瘋狂、邪惡與非理性已使得人類文明對地球犯下了滔天罪行,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兩次世界大戰、“文革”、發展主義的殺雞取卵,等等,盡皆如此。對于這些罪愆,顯然,僅僅寄希望于主或上帝的懲罰與救贖是不能夠的,那么,寄希望于更高級的文明呢?劉慈欣在另兩部短篇《詩云》和《鄉村教師》中已表現了對這一命題的思考。前者告訴我們,科學再發達,技術再先進,在面對人類的藝術創作如詩歌寫作時,仍舊是無效且無能的。這無疑是想告訴我們科技并非萬能。而后者則通過中國貧困山區一名鄉村教師意外地拯救了人類這一行為,向我們暗示,其雖極其偶然,但這當中愛與責任的力量的偉大卻不容忽視。這樣來看《三體》就會發現,愛與責任雖在面臨生存危機時顯得柔弱無力,但并非毫無價值,同樣,三體文明的科學技術縱使強大到所向披靡,在面對太陽系的維度災難時仍舊束手無策,更不用說它在面對人類復雜的內心世界時是那樣的恐懼無奈。
二
《詩云》中的命題恰好可以對照《三體》加以解讀。不惟藝術創作,人類內心世界的深邃也同樣是先進技術所不能窺探的。智子是三體世界發射(或派遣)到人類文明的密探,它無所不能,在它面前任何東西都是透明的,單向度的和簡單的,但恰恰是這樣一個高級的文明形態,在面對人類內心世界的隱秘和豐富復雜時卻是無力無能的。究其原因,是因為人類的內心世界,往往是理性和邏輯思維所不能把握的,小說主人公取名“羅輯”似也包含這一層含義。他所能震懾三體文明的,除了他掌握了宇宙中極具邏輯推理的“森林法則”之外,還在于他那非邏輯的內心及其行為。理性和感性在他身上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并存著。這樣來看就會發現,如果說三體文明代表或象征的是一個理性的、平面的和科學的文明的話,那么三體文明同人類文明的沖突,某種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理性和感性之間的二律背反這一人類永恒命題的投射。科學的發展與人類的感性之間并不總是成正比的,人類控制得了科學,卻控制不了自己的內心。三體世界對人類世界的恐懼,正是這一恐懼的表征。“人”的情感的豐富,造成了“人”的形象的難解,其一方面創造了人類藝術的燦爛,一方面也暗藏著人性的無底“黑暗”,而這,恰恰是三體文明對人類所既羨慕又恐懼的,也是人類對自身矛盾態度的根源。小說借三體文明對人類文明的復雜態度表達了劉慈欣對這一人類悖論式命題的思考和困惑:理性和科學雖能掌握外在世界,卻不能把握人類的內心世界,兩者間的矛盾,某種程度上制約著人類在發展的道路上能走多遠。
但劉慈欣又不僅僅止于此。劉慈欣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沒有僅僅從人類的角度,而是把理性和感性的悖論置于“宇宙社會學”的層面考量。這時,有關愛和美的人類命題,也重新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小說通過對程心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試圖告訴我們,愛與美的局限,及其效應。程心當然是愛與美的化身,但當她掌握著決定人類生存命運的按鈕的時候,她其實是最為脆弱的。這也就意味著,愛與美的有效性正體現在它們同生存問題的脫節中,一旦彼此纏繞一起,它們的蒼白無力便顯示出來。科學雖不能控制或窺探人心,但科學可以毀滅人。這正是理性與感性的辯證法。但劉慈欣又試圖告訴我們,生存法則雖關乎科學技術,但又不僅僅如此。因為很明顯,三體文明的科學技術再先進發達,難保整個宇宙就沒有比它更高的文明。以此類推,最終又繞回到哲學上來,即“人類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宇宙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地球往事·三體》,第92頁)之類的終極問題。換言之,也就是所謂的“來”和“去”的哲學命題。只不過,劉慈欣在這里所思考的不僅僅是人類的“來”和“去”的問題,它還是宇宙的“來”和“去”的問題,是兩者的結合。其中一個事實很明顯,即,文明世界即使能制造出光速飛船,逃脫得了維度災難(太陽系的坍塌),也終逃不脫宇宙在無限膨脹中的毀滅。這也就意味著,包括人類在內的宇宙發展到最后,并不是科學技術的問題,而是哲學命題,也即所謂的終極意義上的“來”和“去”的辯證與平衡問題:宇宙的質量守恒。這就又回到了愛與美的人類命題上來。
小說發展到結尾,雖然整個銀河系都毀滅了,但關于愛與美以及責任之類的人類命題仍舊存在,小說以程心和關一帆這兩個僅存的人類成員的在宇宙中漂流表明了這一傾向。小說中《時間之外的往事》之《責任的階梯》就是例證。這是程心以“漂流瓶”的形式留給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文明的信息,也是她的對文明世界的思考和對宇宙生存命題——責任的最高階梯——的徹悟:每個文明發展到 “最后與宇宙的命運融為一體”,這就要求一種最高階梯的“責任”。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命運和責任呢?科學理性的高速(或勻速)發展,到最后會導致宇宙在膨脹中毀滅,但如果能自覺地把自己的命運同宇宙的命運融為一體,這樣的責任感卻可以在終極意義上讓宇宙永生。這是一種最高意義上的人類的愛與美的表現,也是作為理性化身的智子所始終不能理解的(“你還是在為責任活著”,這是她對程心所說的話)。從這個角度看,這是一場宇宙層面的“傾城之戀”,銀河系的毀滅正是為了成就其人類的感性及其道德的偉大。
三
這樣來看,小說其實是從終極意義上,重新思考了科學、愛與美、人性之善、惡等一系列人類命題。就美的命題而言,其最為集中地體現在三體文明向地球艦隊發起攻擊的水滴,以及智子的形象上。這都是美的極致的體現,但這兩個事物卻是理性與科學的最極致的結晶;這樣的美的形象,雖具有無比完美的線條和黃金比例,但卻是毫無感情極端冷漠的。美如果沒有感性而僅成為理性之光的表現,這樣的美雖具有審美的價值,對于人類卻只能是災難。同樣,人性的愛、善及其惡,也是如此。當所有這些命題,在遭遇人類的毀滅與生存這樣的宏大命題時,如果僅僅糾纏于純粹抽象的倫理學與道德感的層面,而不考慮它的具體的歷史的語境規定性,這樣的人性與善往往也會成為毀滅人類的引線。
當然,劉慈欣并不是反對愛與美,他只是讓我們看到,這中間的先后秩序和辯證關系。在他看來,人性的善、美及其惡,它們之間的界限,乃至價值,很多時候都是雜糅一起很難區分的。愛與美,以及人性的善,只有在生存的問題解決之后才有其意義,同樣,人性的惡,當它是為了人類的生存問題時,也并不一定是惡。小說中的托馬斯·維德和章北海就是例證。同時,劉慈欣也試圖告訴我們,雖然人類毀于自身的人性之惡,但也浴火重生于它的愛與善以及責任。這就是所謂宇宙終極命題的人類學內涵,也即所謂的“來”和“去”的辯證法。科學如果不能圍繞或以這些問題作為它的思考的起點和終點,這樣的科學便不會有任何意義和價值。
這樣就可以回到文章的開頭所提出的問題,即《三體》提出一系列帶有根本性的終極問題卻又借助于科幻這一形式表現出來這一悖論上來。就《三體》而言,科幻文學的“形式的意識形態”表現在,它通過設置一個宇宙主義的視角,而能拋開所謂人類中心主義的限制,從而使我們能很好地重新審視以人類的主體性建構為基礎的一系列命題及其諸如真善美與假丑惡、主與奴、自我與他者等等之類的二元對立范疇。對于這些范疇,僅僅從解構主義的角度是很難有深刻的發現的,因為畢竟,解構主義在顛覆這些二元對立時很有效,但在重申這些命題的價值時卻是蒼白無力的。而如果立足于主體性的立場又只能陷于不可解脫的二元對立的悖論,就像抓住自己的辮子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離開地球一樣。科幻文學及其宇宙主義視角的好處正在于,它讓我們找到了擺脫地球引力的方式方法,但又不是徹底“逃出母宇宙”(王晉康科幻小說名)。從這個角度看,《三體》就是一個“問題域”,它通過把這一系列命題置于人類面臨毀滅的境遇中重新考量,讓我們看到了這一系列命題的致命的局限,但又不是完全的否定。它從宇宙的角度和哲學的高度重新賦予這些命題以重生的價值,太陽系和銀河系雖可能毀滅,但人類的普遍命題卻可以永生。這就是劉慈欣和他的《三體》所能給予我們的最大的信心,同時也是一種警示。
徐 勇: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李松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