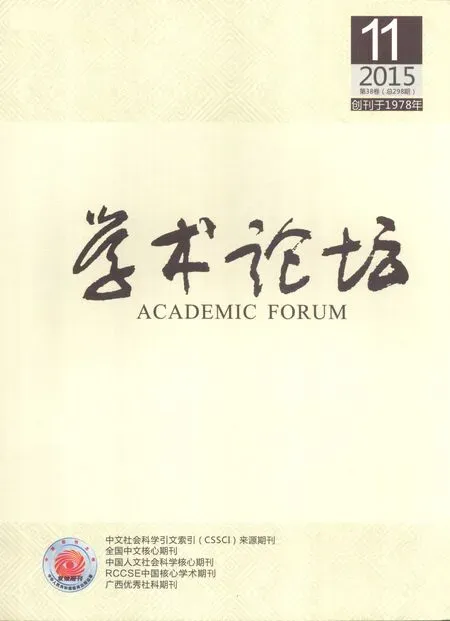戰(zhàn)略管理范式的演進:危機與轉換
劉紅葉,揭筱紋
一、引 言
自20 世紀50 年代戰(zhàn)略管理產生以來,企業(yè)戰(zhàn)略管理范式的演進經歷了三個發(fā)展階段:20 世紀50-80 年代的早期范式、20 世紀90 年代的資源基礎觀范式和21 世紀以來新范式的凸現。 研究戰(zhàn)略管理范式的演進,對于探索和總結管理理論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從事管理實踐活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現有的研究文獻來看,戰(zhàn)略學者比較關注對范式的概括和總結, 例如通過對20 世紀60 年代戰(zhàn)略理論考察提出的 “戰(zhàn)略行為”(Strategic Behavior)范式[1]以及對“結構-行為-績效”范式和“效率”(Efficiency)范式的比較研究[2]等。 近年來,國內學者也比較關注戰(zhàn)略管理范式的研究, 例如基于網絡經濟提出的“戰(zhàn)略生態(tài)管理”范式[3]以及從剛性視角和柔性視角對范式進行比較研究[4]等。 本文的研究重點是結合戰(zhàn)略管理理論的新發(fā)展, 考察戰(zhàn)略管理范式演進中的危機及其轉換,以期揭示戰(zhàn)略管理范式演進的內在邏輯。
二、范式與管理范式
范式(Paradigm)一詞,來自希臘文,含有“共同顯示”的意思,由此引申出模式、模型、范例等含義。庫恩認為,范式是與“科學家集團”或“科學共同體”密切相關聯的一個概念,它是“某一科學家集團在某一專業(yè)或學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這種信念規(guī)定了他們共同的基本理論、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為他們提供了共同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框架,從而形成為該學科的一種共同的傳統(tǒng),并為該學科的發(fā)展規(guī)定了共同的方向”。[5](P508)當一門學科出現統(tǒng)一的范式后,就進入漸進發(fā)展的“常態(tài)科學”(Normalscience)時期,科學家集團用范式去解決科學研究中的各種問題,并積累知識。但是,隨著常態(tài)科學的發(fā)展,科學研究不斷地揭示出既有范式所不能解釋的反常現象(Anomaly),于是引起常態(tài)科學的危機,危機迫使科學家集團尋求另外更有說服力的解釋。 在這個過程中,新的定律、概念、假設、價值、技術和解決問題的范例出現,科學研究的新范式就形成了[6]。庫恩將這種范式轉換稱為科學革命。
管理范式是關于管理事實的一整套基本假設,包括對管理原則的假設和管理實踐的假設。 德魯克認為,對于管理學這樣的社會科學來說,基本假設的重要性實際上比自然科學的范式重要性大得多,因為無論范式聲稱太陽繞著地球轉,還是說地球繞著太陽轉,太陽和地球都不會受到影響。 他認為,在20 世紀80 年代之前,大多數學者、作家和管理實踐者都認同兩套關于管理事實的假設。第一套假設構成管理原則的基礎:管理是企業(yè)管理;企業(yè)應該具有或必須具有一種恰當的組織形式;企業(yè)應該采取或必須采取一種管理人的恰當方式。第二套假設奠定了管理實踐的基礎:技術和最終用戶是一成不變和已知的;管理的范圍是由法律決定的;管理是對內部的管理;按國家邊界劃分的經濟體是企業(yè)和管理依托的“生態(tài)環(huán)境”。 現在,上述假設由于與現實相差得太遠,以至于成為阻礙管理理論發(fā)展的障礙,更有甚者,它們還嚴重地妨礙了管理實踐。 因此,德魯克提出,我們需要一個全新的管理范式[7](P2)。 下面,本文將通過對戰(zhàn)略管理理論的梳理,探討戰(zhàn)略管理的范式危機及其轉換。
三、早期范式的形成
從20 世紀50 年代到80 年代,是戰(zhàn)略管理早期范式的形成階段。 從研究文獻來看,戰(zhàn)略設計學派對于戰(zhàn)略管理范式的最初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戰(zhàn)略設計學派強調設計出一個戰(zhàn)略制定的模型以尋求內部能力和外部環(huán)境的匹配。 1957 年,塞茲尼克引入了“特色競爭力”(Distinctive competence)的概念,探討了將組織的“內部狀態(tài)”和“外部期望”進行整合的必要性,認為應當將戰(zhàn)略深入到“組織的社會結構中”, 這一行為后來被稱為 “戰(zhàn)略執(zhí)行”[8](P19)。 隨后,錢德勒基于對美國企業(yè)史的考察,創(chuàng)建了設計學派有關經營戰(zhàn)略以及組織結構追隨經營戰(zhàn)略的思想體系[9](P442)。 安德魯斯構建了設計學派的戰(zhàn)略分析模型,該模型著重強調對外部與內部環(huán)境的評價:前者要揭示潛在的機會和威脅,后者要總結組織的優(yōu)勢與劣勢。 該模型同時列出了其它兩個被認為在戰(zhàn)略制定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一個是管理價值,即組織中正式領導者的信仰與偏好;另一個是社會責任,特別是組織在社會道德中(至少是經理們所能感知的社會道德)中所發(fā)揮的作用[8](P20)。 安德魯斯重點闡述了如何把商業(yè)機會與公司資源有效匹配, 并從中發(fā)展出了著名的SWOT 分析工具[10](P1)。安索夫認為范式是一把“科學之傘”, 他把先前提出的明顯相互矛盾的理論整合成一體。 基于這樣的思路,安索夫將早期的戰(zhàn)略管理范式總結為“環(huán)境-能力-戰(zhàn)略”三角模型[1]。
產業(yè)組織經濟學的結構-行為-績效范式,對于戰(zhàn)略管理的早期范式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它不僅為戰(zhàn)略管理提供了分析技術,而且?guī)砹诵碌姆椒ㄕ搨鹘y(tǒng)[11]。 20 世紀70 年代以來,在結構-行為-績效范式的影響之下,產生了PIMS 原則和競爭戰(zhàn)略理論。 巴澤爾和蓋爾提出的PIMS 原則,揭示了在不同市場和競爭環(huán)境中戰(zhàn)略與績效之間的重要聯系,其研究認為企業(yè)所處的市場結構和競爭地位對于企業(yè)績效起決定性作用[12](P30)。 邁克爾·波特的競爭戰(zhàn)略理論認為企業(yè)成功是兩個因素的函數:產業(yè)吸引力和企業(yè)在該產業(yè)的相對位勢,企業(yè)戰(zhàn)略的核心是選擇有吸引力的、潛在利潤高的產業(yè)或在已選擇的產業(yè)中確立自己的競爭優(yōu)勢[13]。波特提出了一個五力分析框架,從現有企業(yè)間的競爭、潛在進入者、替代品生產廠家、賣方、買方五個方面來分析產業(yè)結構的主要特點,從而確定企業(yè)的戰(zhàn)略選擇空間[14]。波特的戰(zhàn)略分析方法建立在結構-行為-績效傳統(tǒng)之上,其基本結論是產業(yè)結構而不是市場力量最終決定企業(yè)在該產業(yè)中的定位、運行以及經營績效[15]。
四、資源基礎觀范式
20 世紀90 年代是戰(zhàn)略管理研究的艱難時期。放松規(guī)制、組織結構的變化、過剩生產能力、并購、環(huán)境保護意識、變化的顧客期望、技術的非連續(xù)性、國際競爭等要素成為影響競爭格局的重要力量。 這些影響競爭格局的力量正在改變著公司優(yōu)勢的來源和產業(yè)的經濟狀況。 為什么處于同一產業(yè)中的企業(yè)會有不同的績效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實踐課題。 新的競爭形勢驅使戰(zhàn)略學者重新審視傳統(tǒng)的戰(zhàn)略管理范式。 傳統(tǒng)戰(zhàn)略分析的假設包括戰(zhàn)略是在給定的產業(yè)結構中為企業(yè)定位、戰(zhàn)略工具和分析的焦點是現有產業(yè)、戰(zhàn)略分析的基本關注點是單個企業(yè)、戰(zhàn)略產出可以在經濟分析的基礎上闡釋。 戰(zhàn)略學者日益認識到,為了給新思想鋪平道路,在1965-1985 年建立起來的主導戰(zhàn)略分析工具和概念需要重新評估[16]。認識到戰(zhàn)略領域需要一個新范式是關鍵的第一步。 戰(zhàn)略學者們遵循由外而內的思維邏輯重新思考競爭優(yōu)勢的來源,逐漸形成了資源基礎觀范式(RBV),從而走出了早期范式的危機。
早在1984 年,沃納菲爾特就提出資源分析與產業(yè)分析至少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他認為企業(yè)是各種資源與能力的組合,企業(yè)的成長戰(zhàn)略需要尋求現有資源利用與新資源開發(fā)之間的平衡[17]。杰伊·巴尼則從企業(yè)資源的異質性和不可轉移性出發(fā),分析可持續(xù)競爭優(yōu)勢的來源。 資源與能力能否為企業(yè)帶來持久競爭優(yōu)勢,取決于其能否滿足價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等特點。 企業(yè)資源難于模仿的原因在于資源是在獨特的歷史環(huán)境中形成的,資源和能力與競爭優(yōu)勢之間存在因果模糊性,以及資源具有社會復雜性[18]。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爾奠定了核心競爭力理論的基礎。 核心競爭力是指組織中的累積性學識,特別是協調各種生產和整合各種技術的學識。 核心競爭力具有提供進入更廣闊的市場的潛力,應當為實現可覺察的顧客價值作出重要貢獻,并且競爭對手難以模仿。 企業(yè)的核心競爭力難以模仿的原因在于它融入了許多不可逆轉的專用性投資,是個人技術與生產能力的復雜集合體[19]。
提斯等學者在對企業(yè)資源和能力細分的基礎上提出了動力能力理論,認為動力能力是企業(yè)保持可持續(xù)競爭優(yōu)勢的源泉。 企業(yè)的資源可以分為如下層次:(1)生產要素,如土地、非熟練勞動力、資本等。(2)資源,指難以模仿的公司專有資產。商業(yè)秘密、某些特殊的生產工藝和設備是典型例子。(3)組織的競爭力/程序。包括質量、微型化、系統(tǒng)集成。 (4)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力的獨特程度取決于公司相比于競爭者的資源稟賦和競爭者模仿其競爭力的困難程度。 (5)動力能力。 動力能力定義為公司整合、構建、重新配置內外部競爭力以適應迅速變化的環(huán)境的能力。 (6)終端產品,是公司基于利用自身所擁有的競爭力提供的最終產品和服務。 在任何時點上,公司產品的績效(價格、質量等)要超過競爭者,決定于其競爭力(并最終依賴于其能力)。 企業(yè)的獨特能力或動力能力依賴于三個方面:程序、定位和路徑。 能力的本質是嵌入于組織的各種程序中的。 但是這些程序的內容及其提供的開發(fā)組織競爭優(yōu)勢的機遇是由組織擁有的資產(內部的和市場的)及其所繼承的演化路徑塑造的。 因此,動力能力反映了在既定的路徑依賴和市場定位條件下獲取競爭優(yōu)勢創(chuàng)新形式的一種組織能力[20]。
資源基礎觀范式基于內生視角研究競爭優(yōu)勢的來源,將企業(yè)看成是一系列異質資源的組合,而不是同質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黑箱”,持續(xù)性的競爭優(yōu)勢來源于資源的價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異質資源的獲取與管理主要來自于學習,企業(yè)通過保持自身內生優(yōu)勢來獲得績效的持續(xù)改進。
五、21 世紀以來戰(zhàn)略管理新范式的凸現
進入21 世紀以來,經營環(huán)境的巨大變化導致戰(zhàn)略管理領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 首先,戰(zhàn)略管理的空間在擴展。 信息技術的發(fā)展打破了固定的行業(yè)界限和企業(yè)邊界,不同企業(yè)間、不同行業(yè)的企業(yè)間的聯合、合作成為戰(zhàn)略管理的重要發(fā)展趨勢。 其次,企業(yè)經營環(huán)境的變化對企業(yè)戰(zhàn)略的彈性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 比如新技術的出現,可能會使企業(yè)精心培育和構筑起來的卓越能力一夜之間變得一文不值,因而要求企業(yè)具有快速反應市場變化的能力,不斷地創(chuàng)新產品和服務。 再次,企業(yè)戰(zhàn)略不僅限于考慮企業(yè)內部所擁有的資源,而且要著眼于創(chuàng)造性地通過各種途徑來整合資源以克服自有資源的局限。 如浙江的綠盛集團和天暢網絡兩家企業(yè)將兩種完全不相關的產品互相植入,綠盛把天暢的《大唐風云》游戲形象作為主體形象印刷在“綠盛QQ 能量棗”的包裝封面上,而天暢則將“綠盛QQ 能量棗”植入《大唐風云》游戲中,作為游戲中的最高能量補充劑。 企業(yè)通過跨行業(yè)的整合資源,創(chuàng)造新的資源結構,以期獲得最佳的戰(zhàn)略績效[21]。最后,制定戰(zhàn)略的主體趨于多元化。信息技術的發(fā)展使組織結構日益扁平化,信息傳播手段和渠道日益大眾化和多樣化,這使更多的利益相關者有機會參與企業(yè)戰(zhàn)略的制定,利益相關者被納入組織的“戰(zhàn)略管理程序”[22](P100)。
如何在動態(tài)、開放的環(huán)境條件下保持可持續(xù)的競爭優(yōu)勢,成為戰(zhàn)略管理面臨的新問題。 資源基礎觀范式的困難在于并沒有充分闡釋在快速、難以預測的變化環(huán)境中,為什么有企業(yè)獲得競爭優(yōu)勢以及他們是怎樣獲得的。 資源基礎觀范式不僅缺少變化的邏輯,而且在預測現有優(yōu)勢的長度和未來優(yōu)勢的源泉方面陷于困境。 對資源基礎觀范式的批評包括概念模糊、對獲得競爭優(yōu)勢的機制不在意以及缺乏實證基礎。 在高度變化的市場環(huán)境下,資源基礎觀范式強調長期競爭優(yōu)勢是不現實的。 因為短期的、難以預測的優(yōu)勢更為常見,而且成長是比利潤更有用的績效特征。 而且,資源基礎觀范式忽略了時間的戰(zhàn)略意義[23]。戰(zhàn)略管理的新問題和新情況,需要一種新范式來解釋。 20 世紀90 年代后期,商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理論、戰(zhàn)略網絡理論的形成和發(fā)展,標志著一種新范式的凸現。
穆爾認為,商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是“以組織和個人的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經濟聯合體”。 這種經濟聯合體生產出對消費者有價值的產品和服務,消費者是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成員。 有機體成員還包括供應商、主要的生產者、競爭者和其他風險承擔者[24](P18)。 企業(yè)必須同相關企業(yè)共同進化,和諧地將網絡成員各自的貢獻結合起來,為顧客和生產者創(chuàng)造利益,形成一個開放的、抗風險能力強的商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
戰(zhàn)略網絡觀點認為,將企業(yè)看作利用外部產業(yè)資源或內部資源和能力來尋求競爭優(yōu)勢的自治實體已經不合時宜了。 企業(yè)嵌入于社會的、專業(yè)的、交換關系的網絡之中,包括企業(yè)與供應商、顧客、競爭者或跨產業(yè)、跨國實體的縱橫交錯關系。企業(yè)嵌入于其中的戰(zhàn)略網絡對于企業(yè)行為和企業(yè)績效具有重要影響。 戰(zhàn)略網絡由那些持久的、對組織有戰(zhàn)略意義的產業(yè)間節(jié)點構成,包括戰(zhàn)略聯盟、合資、長期的買賣伙伴關系和一群相似的節(jié)點。 租金驅動的資源不僅包括品牌、技術能力、管理能力,也包括公司的網絡資源或社會資本。 公司的社會關系是獨特或不可模仿的資產。 公司的專有網絡和其在網絡中的相對地位都是重要的。 公司的社會關系允許他們在戰(zhàn)略網絡中占據一個更核心的位置,由于比那些處于邊緣的公司獲得了更好的信息和機會,使得它們享有更高的回報[25]。
不僅企業(yè)認識到以不同方式組織企業(yè)間關系可以導致競爭優(yōu)勢,顧客也認識到社會網絡的力量。 公司間網絡和個人間網絡成為競爭優(yōu)勢的來源。 在一個動態(tài)的環(huán)境下,網絡是與利益相關的。在網絡中,節(jié)點通過時間可以被創(chuàng)造并且被打破。網絡不僅在知識產生和知識共享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企業(yè)創(chuàng)新中具有核心作用[26](P86-87)。
以商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戰(zhàn)略網絡等理論為代表的新范式吸收和借鑒了復雜性科學的理論假設、基本概念和方法論,將企業(yè)組織視為一個“開放的復雜巨系統(tǒng)”[27],它具有耗散結構,即企業(yè)組織存在同復雜環(huán)境交互作用的自組織、自適應過程,強調企業(yè)通過學習性和創(chuàng)造性活動與環(huán)境共同進化,從而形成可持續(xù)的競爭優(yōu)勢。

表1 戰(zhàn)略管理范式的演進
六、結論與討論
通過對戰(zhàn)略管理范式演進的討論可以看出,在某個時期內居于主導地位的穩(wěn)定范式,如果不能提供解決問題的適當方式,它就會陷入危機,導致范式轉換。 按照庫恩的定義,范式轉換就是一場科學革命,新的范式取代舊的范式,科學據此對某一知識和活動領域采取全新的和變化了的視角。
如表1 所示,早期的范式假設環(huán)境是穩(wěn)定的、組織具有同質性、戰(zhàn)略管理是線性系統(tǒng)。 產業(yè)結構的特點決定了企業(yè)的戰(zhàn)略選擇空間,從而決定了企業(yè)在該行業(yè)中的定位、運行以及最終的經營績效。但是,早期范式無法解釋,為什么處于同一產業(yè)中的企業(yè)會有不同的績效。資源基礎觀范式擺脫了古典經濟學的企業(yè)“黑箱”論,基于內生視角研究組織競爭優(yōu)勢的來源。資源基礎觀范式假設競爭優(yōu)勢源于企業(yè)的異質資源、異質資源的獲取與管理主要來自于學習、企業(yè)應從自身內生優(yōu)勢來獲得績效的持續(xù)改進,從而走出了早期范式的危機。進入21 世紀以來,信息技術的迅猛發(fā)展和市場環(huán)境的高度不確定性,導致資源基礎觀范式無法解決如何在動態(tài)、開放的環(huán)境條件下保持可持續(xù)的競爭優(yōu)勢。商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戰(zhàn)略網絡等理論突破了資源基礎觀范式的局限性,它們以環(huán)境具有不確定性、組織是復雜系統(tǒng)且具有耗散結構、戰(zhàn)略管理是非線性系統(tǒng)為基本假設,形成了強調非均衡與不確定性的戰(zhàn)略管理新范式,有效應對新的管理實踐課題。 從戰(zhàn)略管理范式的演進歷程來看,通過后一種范式對前一種范式的突破和完善,克服了范式危機,推動了企業(yè)戰(zhàn)略管理理論的不斷發(fā)展。
[1] H. Igor Ansoff. The Emerging Paradigm of Strategic Behavior [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7,Vol.8.
[2] Abagail McWilliams and Dennis L. Smart. Efficiency v.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for Strategy Reearch and Practice [ J]. Journal of Management,Vol.19,1993,(1).
[3] 聶銳,張燚.戰(zhàn)略管理新范式:戰(zhàn)略生態(tài)管理[ J].中國礦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3).
[4] 魏強, 陳傳明, 李行鍵. 企業(yè)戰(zhàn)略管理的研究范式轉變——從剛性視角到柔性視角[ J].山東社會科學,2013,(11).
[5] 夏基松.現代西方哲學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 張展,鄧楠.管理學的學科屬性與范式紛爭:對管理學學科發(fā)展的幾點認識[ J].現代管理科學,2007,(2).
[7] 彼得·德魯克.21 世紀的管理挑戰(zhàn)[M].朱雁斌,譯.北京: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09.
[8] 明茨伯格,阿爾斯特蘭德,蘭佩爾.戰(zhàn)略歷程[M].魏江,譯.北京: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07.
[9] 小阿爾弗雷德·D. 錢德勒.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yè)的管理革命[M].重武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10] 周三多,鄒統(tǒng)釬.戰(zhàn)略管理思想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11] Michael. E Porter. The contribution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o strategy management [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1, Vol. 6, No 4.
[12] 羅伯特D·巴澤爾, 布拉德利T·蓋爾. 戰(zhàn)略與績效——PIMS 原則[M].吳冠之,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13] Michael. E Porter. From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Corporate Strategy [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87,May-June.
[14] Michael. E Porter. How Competitive Forces Shape Strategy [ 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79, March-April.
[15] Richard P Rumelt, Dan Schendel and David J. Teece.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1,Vol.12.
[16] C. K Prahalad and Gary Hamel. Strategy as A Field of Study: Why Search for A New Paradigm? [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Vol.15.
[17] Birger Wernerfelt. 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4, Vol.5.
[18] Jay Barney.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 J ].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Vol.17,No. 1.
[19] C. K Prahalad and Gary Hamel.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 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1,May-June.
[20] David J. Teece, Gary Pisano and Amy Shuen.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 J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Vol. 18:7.
[21] 張鋼,倪旭東. R&V 非競爭性戰(zhàn)略聯盟:一個案例研究[ J].研究與發(fā)展管理. 2007(4).
[22] 弗里曼. 戰(zhàn)略管理——利益相關者方法[M].王彥華,梁豪,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23] Kathleen M.Eisenhardt, Jeffrey A.Martin. Dynamic Capability:What are the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
[24] 詹姆斯·弗·穆爾. 競爭的衰亡——商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時代的領導與戰(zhàn)略[M].梁鈞,等,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5] Ranjay Gulati, Nitin Nohria and Akbar Zaheer. Strategic Network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
[26] Duncan A. Robertson and Adrián A. Caldart. The Dynamics of Strategy: Mastering Strategic Landscapes of the Firm [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27] 任佩瑜,張莉,宋勇.基于復雜性科學的管理熵、管理耗散結構理論及其在企業(yè)組織與決策中的作用[ J].管理世界,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