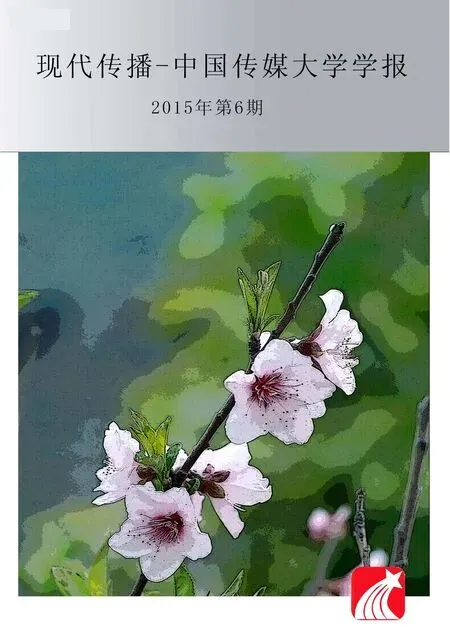公眾信任格局中的科學(xué)家:一項(xiàng)實(shí)證研究*
■ 向倩儀 楚亞杰 金兼斌
公眾信任格局中的科學(xué)家:一項(xiàng)實(shí)證研究*
■ 向倩儀 楚亞杰 金兼斌
在當(dāng)今中國(guó)“科學(xué)”與“民意”不斷發(fā)生沖撞的背景下,科學(xué)家群體是否正在面臨“信任危機(jī)”?本研究從實(shí)證出發(fā),通過網(wǎng)絡(luò)問卷調(diào)查(N=1507)發(fā)現(xiàn),公眾對(duì)科學(xué)家的社會(huì)信任仍然處于高位,在整體信任格局中占據(jù)特殊的位置。進(jìn)而本研究對(duì)這種社會(huì)信任產(chǎn)生的“認(rèn)知模型”做出初步回應(yīng),認(rèn)為以教育程度為代表的“認(rèn)知模型”不能有效解釋科學(xué)家信任產(chǎn)生的機(jī)制。最后,研究還提出若干值得進(jìn)一步探討的研究議題和方向。
信任格局;科學(xué)家;科學(xué)傳播
科學(xué)與公眾的“相遇”存在諸多節(jié)點(diǎn),有政治的、經(jīng)濟(jì)的、也有關(guān)乎職業(yè)和休閑方式的。近年來,中國(guó)社會(huì)“民意”與“科學(xué)”的沖突屢見不鮮,PX事件、PM2.5話題、轉(zhuǎn)基因爭(zhēng)論、垃圾填埋、核電站安全等,無不凸顯科學(xué)觀點(diǎn)與公眾認(rèn)知在公共政策上的緊張與交鋒。在現(xiàn)代國(guó)家政治和社會(huì)治理中,民意通常是執(zhí)政合法性和政策取舍的終極考量依據(jù)。由此,伴隨互聯(lián)網(wǎng)、社交媒體等新信息傳播技術(shù)的崛起,網(wǎng)絡(luò)輿論與公眾力量會(huì)同政府主管部門、相關(guān)領(lǐng)域?qū)<业葌鹘y(tǒng)決策者一起,日益成為影響各種涉及科學(xué)問題或科學(xué)原理的公共決策的重要力量。
一、研究緣起:科學(xué)遭遇“信任危機(jī)”?
1.信任研究引入科學(xué)傳播
早期科學(xué)傳播研究建立在所謂的“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假設(shè)之上。這一假設(shè)認(rèn)為,雖然科學(xué)有利于社會(huì)文明進(jìn)步,有利于公眾擁有更高質(zhì)量的生活,但公眾在一些涉及其福祉的與科學(xué)相關(guān)的議題上,其知識(shí)和技能方面是有欠缺的,需要專業(yè)知識(shí)和技能的擁有者即科學(xué)家和科技媒體進(jìn)行普及和傳播。在這樣的模型中,公眾是科學(xué)知識(shí)和觀念的被動(dòng)接受者。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這一假設(shè)的合理性遭到眾多研究的質(zhì)疑。其中,建構(gòu)主義學(xué)者采用互動(dòng)視角重新審視公眾與科學(xué)、科學(xué)家的關(guān)系,包括動(dòng)態(tài)性地考察專家與外行的區(qū)別,避免將科學(xué)知識(shí)和科學(xué)素養(yǎng)視為固定不變之物等。研究者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公眾并非是高度同質(zhì)的抽象體,他們圍繞不同社會(huì)議題的聚散離合,具有某種偶然性或不確定性;公眾科學(xué)知識(shí)的獲取,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他們當(dāng)下的動(dòng)機(jī)和所處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就科學(xué)知識(shí)的應(yīng)用而言,也常常與其他知識(shí)交織在一起。①這些新視角極大拓展了原有研究的理論、方法及范式,特別是像信任這樣比較成熟的社會(huì)科學(xué)概念的引入,更激發(fā)了科學(xué)傳播研究領(lǐng)域的活力。
作為存在于主體間的信任,是個(gè)體對(duì)他者可能行為的一種積極性預(yù)期。②社會(huì)科學(xué)領(lǐng)域的信任研究始于20世紀(jì)50年代的社會(huì)心理學(xué)領(lǐng)域,代表性研究有Deutsch對(duì)囚徒困境中人際信任的實(shí)驗(yàn)③,Hovland對(duì)人際溝通中信源可信度的研究④等。20世紀(jì)80年代以后,隨著歐美社會(huì)相繼進(jìn)入后工業(yè)社會(huì),社會(huì)的復(fù)雜性增強(qiáng),信任作為消減社會(huì)交往中的不確定性、成本與風(fēng)險(xiǎn)、以及穩(wěn)定社會(huì)秩序的基本因素,再一次獲得西方社會(huì)學(xué)者的關(guān)注。⑤信任對(duì)社會(huì)的作用和價(jià)值已經(jīng)得到眾多研究者的肯定,例如政治學(xué)者福山認(rèn)為,社會(huì)信任有助于減少社會(huì)沖突、增進(jìn)不同群體間的合作、提升政府治理效率等,甚至與國(guó)家經(jīng)濟(jì)繁榮、社會(huì)進(jìn)步相關(guān)。⑥
同樣,科學(xué)傳播領(lǐng)域中,信任被視為公眾和科學(xué)之間的橋梁。對(duì)科學(xué)共同體而言,科學(xué)知識(shí)的建立依靠信任,科學(xué)信念的傳播也依靠信任;同樣在公眾接受科學(xué)知識(shí)時(shí),這樣的信賴也至關(guān)重要。⑦
作為連接科學(xué)與公眾的紐帶,科學(xué)與科學(xué)家需要具有可被信任的特征。有關(guān)這種可信度或曰“權(quán)威”的來源,研究者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與科學(xué)知識(shí)有關(guān)。在Luhmann看來,對(duì)科學(xué)的信任包含著一種抽象的信心,即認(rèn)為某些第三方擁有專業(yè)化的知識(shí),能夠理解世界的復(fù)雜性。⑧Barber則提出科學(xué)的公信力,不僅在于科學(xué)家所具有的知識(shí)與能力,還在于它們?yōu)樵黾庸怖娑患挠璧呢?zé)任。⑨
這種對(duì)科學(xué)的信任在高度分工的現(xiàn)代社會(huì)顯得極為重要。Barber認(rèn)為,在某種程度上,科學(xué)與現(xiàn)代社會(huì)、理性-合法權(quán)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存在一種特殊的疊合。⑩基于這一論斷,有研究者預(yù)測(cè),伴隨著公眾對(duì)權(quán)力、權(quán)威的普遍性不信任,公眾對(duì)科學(xué)的信任程度也會(huì)隨之降低。(11)科學(xué)及科學(xué)家甚至可能成為替罪羊。特別是21世紀(jì)初人類面臨諸如氣候變化、食品污染、有毒廢料等一系列災(zāi)難性風(fēng)險(xiǎn),在公眾眼中這些工業(yè)化惡果的造成,科學(xué)和科學(xué)家通常難辭其咎。(12)
2.科學(xué)信任危機(jī)之謎
盡管我們經(jīng)常聽到各種科學(xué)信任危機(jī)的警示,也經(jīng)常目睹科學(xué)與民意在新舊媒介上演的沖突,但整體上科學(xué)及科學(xué)家的社會(huì)信任程度仍然穩(wěn)居高位,諸多有關(guān)科學(xué)的調(diào)查和相關(guān)經(jīng)驗(yàn)研究都證實(shí)了這一點(diǎn)。(13)如何理解這種不一致?
首先我們需要承認(rèn),公眾接觸科學(xué)總是囿于具體的語境,他們并非懷著一種事不關(guān)己的心態(tài)面對(duì)科學(xué)。特別在科學(xué)遭遇質(zhì)疑、其不確定性顯著時(shí),信任問題會(huì)被放大。當(dāng)科學(xué)家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和判斷結(jié)論與公眾的經(jīng)驗(yàn)、直覺或流行的看法乃至傳說不一致時(shí),公眾非常容易產(chǎn)生猜想或者被引導(dǎo),懷疑科學(xué)家所給出的判斷背后可能的“陰謀”或妥協(xié)。在這種情況下,信任可能瞬間坍塌,而信任一旦失去或被侵蝕,重建通常是困難重重、遙遙無期的事情,一如創(chuàng)傷一旦形成,很難完全愈合或被遺忘。
接下來我們繼續(xù)思考,是否存在科學(xué)的“信任危機(jī)”?假如存在,危及科學(xué)的社會(huì)信任的因素有哪些?這種威脅來自內(nèi)部還是外部?在不同的社會(huì)語境中是否相同?本研究使用的數(shù)據(jù)來自清華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中國(guó)公眾對(duì)科學(xué)家群體信任狀況調(diào)查”項(xiàng)目組(2014),委托清華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媒介調(diào)查實(shí)驗(yàn)室執(zhí)行問卷調(diào)查,數(shù)據(jù)收集時(shí)間為2014年10月1-7日。本次調(diào)查目標(biāo)樣本量2000份,通過網(wǎng)絡(luò)問卷調(diào)查平臺(tái)的大型panel庫,共發(fā)送21226個(gè)邀請(qǐng),參與填答的問卷為2886份(包含中途放棄作答),經(jīng)甄別被舍棄的無效問卷數(shù)為848,實(shí)際回收合格問卷
1507份,響應(yīng)率為7%。
二、研究發(fā)現(xiàn):信任格局中的科學(xué)家
1.社會(huì)信任的差序格局
為何要把對(duì)科學(xué)家的信任放在整體信任格局中加以考察?首先,著眼于中國(guó)社會(huì)特定的文化情境。不少經(jīng)驗(yàn)研究已經(jīng)證實(shí),處于現(xiàn)代化進(jìn)程和社會(huì)轉(zhuǎn)型中的中國(guó),其信任格局并非完全如韋伯、福山等假設(shè)的那樣以血緣關(guān)系為基礎(chǔ)次第展開。交往雙方的情感連接同樣發(fā)揮重要作用,朋友在人際信任中的特殊性得到凸顯。更重要的是,中國(guó)公眾對(duì)組織、制度的信任也與之前的假設(shè)存在顯著差異。(14)因此,本研究希望在整體格局中定位公眾對(duì)科學(xué)家的信任所處的位置和水平。
一些經(jīng)驗(yàn)研究顯示,華人社會(huì)里公眾對(duì)不同主體的信任確實(shí)存在差序結(jié)構(gòu)。(15)這種差序格局不僅存在于以自然人為對(duì)象的人際信任之間,也存在于以抽象關(guān)系為對(duì)象的制度信任之間。發(fā)生于自然人之間的人際信任,建立在直接互動(dòng)或間接互動(dòng)的基礎(chǔ)之上;而對(duì)組織及其代表的制度信任,則建立在個(gè)體對(duì)制度承諾的信心上。(16)顯然,從概念上看,信任和信心是天然糾結(jié)在一起的。
如表1所示,在本研究中剔除對(duì)“社會(huì)上大多數(shù)人”的信任后,經(jīng)過主成分提取,所有15項(xiàng)清晰地區(qū)分為3個(gè)因子,分別命名為“首屬信任”“次屬信任”和“制度信任”。在此,首屬信任指的是對(duì)“家人”

表1 三類社會(huì)信任因子:首屬信任、次屬信任、制度信任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具有Kaiser標(biāo)準(zhǔn)化的正交法旋轉(zhuǎn)矩陣。的信任,次屬信任包括對(duì)同學(xué)或朋友、同事、鄰居的信任,制度信任則包括對(duì)組織(如政府、法院)、組織的代表人(如法官、政府官員、居委干部)及職業(yè)角色等的信任。
Luhmann將信任區(qū)分為人際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和制度信任(institution trust)(17),人際信任既包含了家庭這樣的首屬群體,也包含了同事這樣的次屬群體。首屬群體中的信任以情感信任為主,次屬群體關(guān)系中的信任則以認(rèn)知為主。中國(guó)以血緣為基礎(chǔ)的家庭信任,一直被視為區(qū)別于西方社會(huì)的顯著特征,信任程度與人際關(guān)系的密切程度成正比。(18)
需要說明的是,早期研究認(rèn)為首屬群體是個(gè)人成長(zhǎng)所在社區(qū)中首要接觸的群體,包括家人和鄰居等。隨著社會(huì)的分化和家庭模式的演變,首屬群體的構(gòu)成也發(fā)生變化,反映不同社會(huì)、不同的社會(huì)發(fā)展階段、不同時(shí)代的風(fēng)尚和社會(huì)生活的某種深刻變遷。在本研究中,我們發(fā)現(xiàn)早期被歸為首屬群體的“鄰居”,成為與同學(xué)、朋友、同事同歸一類的次屬群體。
2.科學(xué)家信任的高位
本研究將被訪者對(duì)“社會(huì)上大多數(shù)人”的信任水平(M=5.72,SD=1.656)作為參照線(圖1橫線所示),總體上看,三類不同的信任呈現(xiàn)出遞減的格局:首屬信任>次屬信任>制度信任。

圖1 對(duì)科學(xué)家的信任處于高位
具體地說,個(gè)體對(duì)家人信任程度最高(M=9.25,SD=1.114),遠(yuǎn)高于次屬信任(M=7.06,SD=1.256)和制度信任(M=5.99,SD=1.627),其中唯一的例外是公眾對(duì)科學(xué)家的信任(M=7.17,SD=1.766)。在三類所有項(xiàng)目的排序中,對(duì)科學(xué)家的信任僅次于對(duì)家人、同學(xué)或朋友,且高于對(duì)同事以及對(duì)鄰居的信任。這顯示了科學(xué)家群體在社會(huì)信任中的特殊地位,事實(shí)上這種對(duì)科學(xué)家的高信任度在世界范圍內(nèi)廣泛存在。(19)
次屬信任中,對(duì)同學(xué)或朋友的信任(M=7.74,SD=1.316)高于對(duì)同事(M=6.80,SD=1.563)和鄰居(M=6.63,SD=1.633)的信任。在制度信任(組織及代表)整體偏低的情況下,公眾對(duì)科學(xué)家的信任程度遙遙領(lǐng)先,高于醫(yī)生(M=6.55,SD=1.932)、法官(M=6.44,SD=2.081)等。位于一般信任水平線以下的依次為:對(duì)媒體從業(yè)者、對(duì)本地政府官員以及對(duì)商人的信任。
本研究呈現(xiàn)的格局與鄒宇春等對(duì)中國(guó)城市居民信任格局的發(fā)現(xiàn)一致。該研究表示,個(gè)體對(duì)自然人(家人、鄰居、陌生人等)的信任存在強(qiáng)弱差異,家人最強(qiáng);對(duì)各項(xiàng)制度代表(如警察、醫(yī)生、法官等)的信任也存在差異,對(duì)商人信任度最低,對(duì)科學(xué)家信任度最高。(20)
如何理解這種普遍的高信任度?對(duì)科學(xué)及科學(xué)家這種普遍高信任度,既來自于科學(xué)知識(shí)在應(yīng)對(duì)社會(huì)復(fù)雜性、不確定性的優(yōu)勢(shì),也來自科學(xué)的中立性,及服務(wù)人類福祉的公益性等。研究者還指出,這種普遍的高信任度,即便在科學(xué)與民意就具體議題發(fā)生沖突的背景下依然存在。(21)
總體上看,科學(xué)共同體內(nèi)部所遵循的倫理規(guī)則并未發(fā)生動(dòng)搖。所謂的“信任危機(jī)”更多的是一種感知(perception)。這種感知的背后,更多的是社會(huì)的結(jié)構(gòu)性變動(dòng),包括科學(xué)與政治的關(guān)系、公眾科學(xué)知識(shí)和反思能力的提高等。因此,我們有必要進(jìn)一步區(qū)分對(duì)科學(xué)家的普遍高信任度與具體科學(xué)爭(zhēng)議中公眾的信任或質(zhì)疑的區(qū)別。
三、信任格局產(chǎn)生的原因
1.“認(rèn)知”模式
長(zhǎng)期以來,包括社會(huì)心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政治學(xué)、管理學(xué)等在內(nèi)的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者,試圖從各個(gè)角度探尋信任的本質(zhì)特征、產(chǎn)生的根源及其動(dòng)力機(jī)制。跨文化比較研究中也常常將不同國(guó)家地區(qū)的信任格局作為重要的研究對(duì)象。影響社會(huì)信任的宏觀因素,除表現(xiàn)為社會(huì)系統(tǒng)的變動(dòng),還體現(xiàn)在文化規(guī)范上。而微觀層面對(duì)信任的影響因素,則包括社會(huì)關(guān)系的性質(zhì)(22)、人格特征(23)等。
就個(gè)體而言,已有研究認(rèn)為,建立在知識(shí)和個(gè)體經(jīng)歷基礎(chǔ)上的認(rèn)知能力是認(rèn)知信任發(fā)生的主要依據(jù),而個(gè)體與他者的情感關(guān)系主要影響了情感信任的發(fā)生。(24)我們已經(jīng)看到,首屬關(guān)系中的信任以情感信任為主,次屬群體關(guān)系中的信任則以認(rèn)知信任為主。基于這一觀點(diǎn),不同類型的信任背后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機(jī)制和動(dòng)力。
與以親身接觸為基礎(chǔ)的人際信任相比,制度信任差異格局的形成和變化,向研究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戰(zhàn)。原因之一在于,人們尚不清楚是個(gè)人因素抑或制度本身的差異,對(duì)這種制度信任差異格局的形成影響更大。其二,信任測(cè)量本身成為難以深入研究的障礙。一般來講,信任的測(cè)量通過使用定序量表,無法進(jìn)行加減乘除的運(yùn)算;同時(shí),這種測(cè)量的限制也難以將大量已有的信任數(shù)據(jù)進(jìn)行整合,進(jìn)而無法進(jìn)行制度信任格局的趨勢(shì)分析。
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相比于人際信任的感情紐帶,個(gè)體對(duì)制度信任程度的差異,在于個(gè)體對(duì)制度承諾的相關(guān)信息的了解程度以及對(duì)這些承諾實(shí)現(xiàn)程度的判斷。個(gè)體對(duì)不同制度的信任程度,會(huì)因個(gè)人對(duì)制度承諾內(nèi)容、制度承諾實(shí)現(xiàn)情況等信息的掌握程度,而出現(xiàn)類似人際信任一樣的差序格局。(25)
2.“教育程度”的預(yù)測(cè)力
這種“認(rèn)知模式”與此前科學(xué)信任研究的發(fā)現(xiàn)也較為吻合,不少研究使用“教育程度”這樣的人口學(xué)變量作為認(rèn)知模型的預(yù)測(cè)變量。來自不同國(guó)家的經(jīng)驗(yàn)研究均證實(shí),教育程度與對(duì)科學(xué)的信任呈現(xiàn)顯著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26)不少經(jīng)驗(yàn)研究的發(fā)現(xiàn)也支持了科學(xué)素養(yǎng)或教育水平與科學(xué)社會(huì)信任之間的聯(lián)系,但這種統(tǒng)計(jì)上的關(guān)系相當(dāng)微弱,并且只能解釋抽象的科學(xué)態(tài)度。(27)科學(xué)素養(yǎng)和教育水平不能預(yù)測(cè)具體科學(xué)爭(zhēng)議的態(tài)度(例如人們對(duì)氣候變化的態(tài)度)。
本次調(diào)查也呈現(xiàn)了教育程度與制度信任之間的關(guān)系。如表2所示,教育程度與科學(xué)家信任、政府官員(中央和地方)、政府、居委干部以及對(duì)社會(huì)上大多人的信任在統(tǒng)計(jì)上相關(guān)。但如何解釋教育程度與法院、警察、法官、醫(yī)生、媒體從業(yè)人員之間在統(tǒng)計(jì)上關(guān)聯(lián)的不顯著?

表2 制度信任、一般信任與教育程度
正如已有研究發(fā)現(xiàn)提醒我們的,試圖破解科學(xué)家信任“高位之謎”時(shí),有必要從多個(gè)維度切入。個(gè)體層面的影響因素,除人口學(xué)變量外還需要考察多種社會(huì)性變量。例如,社會(huì)學(xué)家MacKenzie曾就此提出過“信任槽”(certainty trough)概念,試圖從個(gè)體與科學(xué)知識(shí)生產(chǎn)之間的關(guān)系視角考察信任問題。(28)這種非線性的關(guān)聯(lián)也促使研究的關(guān)注點(diǎn)從教育程度等一般性預(yù)測(cè)指標(biāo),轉(zhuǎn)移到更具社會(huì)性的變量上。同時(shí),對(duì)制度信任涉及的對(duì)象也需要謹(jǐn)慎辨析。例如,比較基于專業(yè)聲望的信任與職業(yè)角色信任的差異、個(gè)體對(duì)制度失靈風(fēng)險(xiǎn)評(píng)估所形成的信任差異等。
四、結(jié)論
本研究有兩個(gè)研究目的:一是呈現(xiàn)中國(guó)整體信任格局中,公眾對(duì)科學(xué)家的信任狀況,力圖重新認(rèn)識(shí)這種高信任度(或抽象信任程度)的存在及意義;二是考察教育程度與科學(xué)家信任、信任格局、一般信任之間的關(guān)系,并試圖對(duì)此前的觀點(diǎn)做出回應(yīng)。
總的來說,首先本研究發(fā)現(xiàn),我國(guó)公眾對(duì)科學(xué)家的信任程度在各項(xiàng)制度信任中遙遙領(lǐng)先,且僅次于對(duì)家人、同學(xué)朋友這樣以情感為紐帶的人際信任。對(duì)科學(xué)家的高信任度是跨文化的顯著現(xiàn)象,盡管研究者稱其為抽象的信任,并認(rèn)為這種信任不能預(yù)測(cè)某一具體科學(xué)爭(zhēng)議中公眾的態(tài)度。(29)但我們認(rèn)為這種抽象的信任具有重要的意義,特別在社會(huì)變動(dòng)加劇、各種風(fēng)險(xiǎn)叢生的社會(huì)情境下,公眾對(duì)科學(xué)家的抽象信任是必要且關(guān)鍵的。這并不意味著科學(xué)家及決策者可以完全利用這種高信任感。正如在各國(guó)已經(jīng)發(fā)生和正在發(fā)生的科學(xué)爭(zhēng)議中看到的那樣,這種高信任度無比珍貴的同時(shí)也非常易碎。如何在具體科學(xué)爭(zhēng)議中善加利用這種信任感是需要進(jìn)一步討論的問題。
其次,本研究對(duì)教育水平與科學(xué)信任關(guān)系的討論做出了初步的回應(yīng)。持批評(píng)觀點(diǎn)的研究者認(rèn)為,教育程度與科學(xué)的社會(huì)信任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是建立在缺失模型基礎(chǔ)上,并認(rèn)為這種模型假設(shè)科學(xué)共同體及科學(xué)知識(shí)超越普通人所擁有的其它知識(shí),具有文化上的優(yōu)越地位。(30)而這種偏見或傲慢,將妨害公眾參與科學(xué),不利于科學(xué)爭(zhēng)議的解決。加之教育水平與科學(xué)社會(huì)信任之間的關(guān)系,在時(shí)間維度也錯(cuò)綜復(fù)雜,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確保科學(xué)社會(huì)信任水平的提高。研究者認(rèn)為,一個(gè)可能的解釋是,除了知識(shí)和教育水平,其它社會(huì)因素,例如種族、收入、宗教狂熱、社會(huì)資本、政治身份等,在預(yù)測(cè)科學(xué)的社會(huì)信任上同等重要。(31)因此,本研究?jī)H僅是有關(guān)科學(xué)家公信力系列研究的起步,后續(xù)研究將繼續(xù)探討科學(xué)素養(yǎng)、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政府信任等的影響。
注釋:
① 埃德納·F·艾因西德爾:《理解公眾理解科學(xué)與技術(shù)中的“公眾”》,載[德]德爾克斯、馮·格羅特編:《在理解與信賴之間:公眾,科學(xué)與技術(shù)》,田松等譯,北京理工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149頁。
② Hardin,R.Conceptions and Explanations of Ttrust.In Cook,K.(ed.)Trust in Society,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1,pp.3-40.
③ Deutsch,M.Trust and Suspicion.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58,(2):265-279.
④ Hovland,C.,Janis,I.&Kelley,H.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Opinion Chang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
⑤ 張?jiān)莆洌骸恫煌?guī)模地區(qū)居民的人際信任與社會(huì)交往》,《社會(huì)學(xué)研究》,2009年第4期。
⑥ Fukuyama,F(xiàn).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
⑦(29) [英]史蒂文·耶利:《“公眾理解科學(xué)”中的科學(xué)是什么意思?》,載[德]德爾克斯、馮·格羅特編,《在理解與信賴之間:公眾,科學(xué)與技術(shù)》,田松等譯,北京理工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164頁。
⑧(17) Luhmann,N.Trust and Power.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79.
⑨ Barber,B.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0.
⑩ Barber,B.Science and the Social Order.Glencoe,IL:Free Press,1952.Barber,B.Toward a New View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In Coser,L.A.(ed.)The Idea of Social Structure:Papers in Honor of Robert K.Merton.New York:Harcourt,1975.Barber,B.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0.
(11) Gauchat,G.Politicization of Science in the Public Sphere:A Study of Public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1974to2010.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2,77(2):167-187.
(12) Beck,U.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1992.
(13) Allum,N.,Sturgis,P.,Tabourazi,D.&Brunton-Smith,I.Science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Across Cultures:A Meta-analysis.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08,17(1):35-54.
(14) 李偉民、梁玉成:《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中國(guó)人的信任結(jié)構(gòu)與特征》,《社會(huì)學(xué)研究》,2002年第3期。
(15) 如張苙云和譚康榮對(duì)臺(tái)灣社會(huì)的研究,以及鄒宇春、敖丹、李建棟對(duì)中國(guó)城市居民的分析。張苙云、譚康榮:《制度信任的趨勢(shì)與結(jié)構(gòu):“多重等級(jí)評(píng)量”的分析策略》,《臺(tái)灣社會(huì)學(xué)刊》,2005年刊。鄒宇春、敖丹、李建棟:《中國(guó)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會(huì)資本影響——以廣州為例》,《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12年第5期。
(16) Barber,B.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s.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3.
(18) 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機(jī)制:關(guān)系運(yùn)作與法制手段》,《社會(huì)學(xué)研究》,1999年第2期。
(19)(21) Barnes,B.The Credibility of Scientific Expertise in A Culture of Suspicion.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s,2005,30(1):11-18.
(20)(25) 鄒宇春、敖丹、李建棟:《中國(guó)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會(huì)資本影響——以廣州為例》,《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12年第5期。
(22)(24) Lewis,J.&Weigert,A.Trust As A Social Reality.Social Forces,1985,63(4):967-985.McAllister,D.Affect-and Cognition-based Trust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1):24-59.
(23) Wrightsman,L.Interpersonal Trust and Attitudes Toward Human Nature.In Robinson,J.,Shaver,P.&Wrightsman,L.(eds.).Measures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San Diego:Academic Press,1991.Wrightsman,L.(1992).Assumption about Human Nature: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Newbury Park:Sage Publications,1992.
(26) 例如Allum等的研究以及Inglehart的發(fā)現(xiàn)。Allum,N.,Sturgis,P.,Tabourazi,D.&Brunton-Smith,I.Science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Across Cultures:A Meta-analysis.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08,17(1):35-54.Inglehart,R.Cultural Shift in Advanced Societ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27) Gauchat,G.The Politicization of Science in the Public Sphere.PhD 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Sociology,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2010.
(28) MacKenzie,D.The Certainty Trough.In:Dutton,W.H.(ed).Society on the Li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43-46.
(29) Wynne,B.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In Jasanoff,S.,Markle,G.,Petersen,J.&Pinch,T.(eds.).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1995.
(31) 例如Gauchat、Sturgis與Allum、Yearley等的研究。Gauchat,G.The Politicization of Science in the Public Sphere.PhD 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Sociology,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2010.Sturgis,P.&Allum,N.Science in Society:Re-evaluating the Deficit Model of Public Attitudes.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04,13(1):55-74.Yearley,S.Making Sense of Science.London:Sage,2005.
(作者向倩儀系清華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博士研究生;楚亞杰系清華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在站博士后;金兼斌系清華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
【責(zé)任編輯:劉 俊】
*本文系國(guó)家社科基金項(xiàng)目“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中的輿情演變機(jī)制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11BXW01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