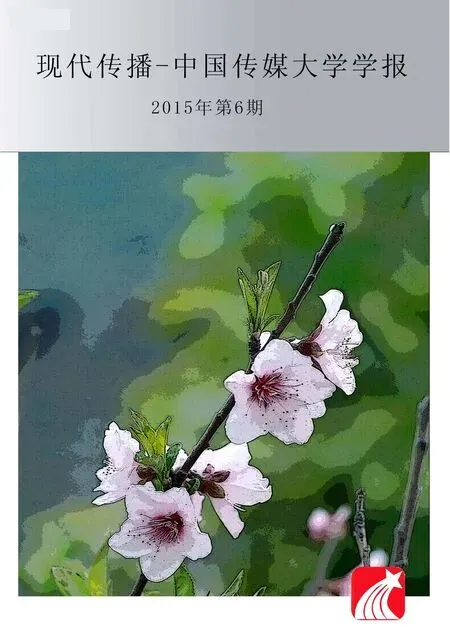社交媒體使用與身份認(rèn)同研究
——以“皮村”鄉(xiāng)城遷移者為例①
■ 王錫苓 李笑欣
社交媒體使用與身份認(rèn)同研究
——以“皮村”鄉(xiāng)城遷移者為例①
■ 王錫苓 李笑欣
隨著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日漸普及,鄉(xiāng)城遷移者也逐漸利用社交媒體構(gòu)建起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這些共同影響著農(nóng)民工的自主意識(shí)與身份認(rèn)同,嵌入其中的社會(huì)資本是這一過程中或隱性或顯性的重要因素,成為鄉(xiāng)城遷移者獲取生活、工作資源的途徑。本研究立足社會(huì)資本理論,剖析位于北京朝陽區(qū)金盞鄉(xiāng)——鄉(xiāng)城遷移者聚居地的皮村中鄉(xiāng)城遷移者社交媒體的建構(gòu)及其嵌入的社會(huì)資本和身份認(rèn)同的復(fù)雜關(guān)系。研究發(fā)現(xiàn),社交媒體的使用幫助鄉(xiāng)城遷移者構(gòu)建了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擴(kuò)大了社交圈子。然而由于中國(guó)戶籍制度的現(xiàn)實(shí)安排,社交媒體及其嵌入的社會(huì)資本未能帶來鄉(xiāng)城遷移者身份認(rèn)同的改變。身份認(rèn)同更有賴于法律地位的賦予而非心理的認(rèn)知。
鄉(xiāng)城遷移者;社交媒體;社會(huì)資本;身份認(rèn)同
盡管人類已步入信息時(shí)代,中國(guó)社會(huì)正發(fā)生著深刻的變革與發(fā)展,但中國(guó)地區(qū)間、城鄉(xiāng)間發(fā)展的不平衡,從農(nóng)村流入城市的鄉(xiāng)城遷移者的現(xiàn)實(shí),無刻不在提醒著步入現(xiàn)代化快車道的人們,不要忽視這一龐大人群。鄉(xiāng)城遷移者被稱為農(nóng)民工、打工者、外來務(wù)工人員等,他們進(jìn)入城市、滯留城市卻無權(quán)分享城市居民福利與城市發(fā)展建設(shè)的成果②。皮村就是這樣一個(gè)由外地鄉(xiāng)城遷移者在京城居住、生活的聚居地,也是我們實(shí)地調(diào)查的所在地。
由于制度安排、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差異及歷史遺留等因素,鄉(xiāng)城遷移者面臨著身份建構(gòu)的困境,同所在城市的其他民眾共同生活和工作卻不能分享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福利、社會(huì)保障待遇,職業(yè)與身份的分離錯(cuò)位是他們?nèi)谌胨畛鞘械淖畲笳系K。
一、本研究涉及的關(guān)鍵概念
1.社交媒體
指隨著Web2.0時(shí)代的到來而出現(xiàn)的用以分享交流意見、見解、經(jīng)驗(yàn)和觀點(diǎn)的工具平臺(tái)。主要包括網(wǎng)站、微博、微信、論壇、博客等。本文所涉及的社交媒體主要指以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為平臺(tái)的微博、微信、QQ等社交工具。
2.社會(huì)資本
社會(huì)資本的正式提出最早可追溯到海尼凡(L.J. Hanifan),之后社會(huì)學(xué)家科爾曼(J.Coleman)于1988年發(fā)表關(guān)于社會(huì)資本的文章后,這一概念開始受到關(guān)注。1993年普特南(R.Putnam)的著作“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出版后,吸引了眾多學(xué)科研究的目光。20世紀(jì)80年代,有關(guān)社會(huì)資本的研究首先在社會(huì)學(xué)領(lǐng)域興起,邊燕杰、張文宏等學(xué)者對(duì)此領(lǐng)域進(jìn)行了大量實(shí)證研究。隨著社交媒體技術(shù)的普及和應(yīng)用,傳播學(xué)領(lǐng)域的學(xué)者也開始關(guān)注這一主題。對(duì)于社會(huì)資本的概念,有個(gè)體層面和集體層面兩種取向,邊燕杰從個(gè)體層面定義了社會(huì)資本:(1)社會(huì)資本即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個(gè)人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越多,則個(gè)人的社會(huì)資本存量越大;(2)社會(huì)資本即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高密度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有助于約束個(gè)人遵從團(tuán)體規(guī)范,而低密度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則可以減少這種約束,為占據(jù)結(jié)構(gòu)洞位置的個(gè)人帶來信息和控制的優(yōu)勢(shì),有利于其在競(jìng)爭(zhēng)的環(huán)境中求生和先贏;(3)社會(huì)資本是一種網(wǎng)絡(luò)資源,是個(gè)人所建立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個(gè)人在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中的位置,最終表現(xiàn)為借此位置所能動(dòng)員和使用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中的嵌入性資源③。羅家德從集體層面角度研究社會(huì)資本,梳理了布迪厄、科爾曼等人的研究后,認(rèn)為社會(huì)資本包含三個(gè)方面:(1)社會(huì)資本首先是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中的“某些方面”,是有助于“特定行動(dòng)”的社會(huì)連帶;(2)它是被作為一種社會(huì)連帶或是連帶的結(jié)構(gòu)而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3)它產(chǎn)生了行動(dòng),而這些行動(dòng)可以帶來資源④。
本文研究對(duì)象為聚居在皮村的鄉(xiāng)城遷移者,筆者取用邊燕杰對(duì)社會(huì)資本的定義,測(cè)量鄉(xiāng)城遷移者:(1)個(gè)人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且這種關(guān)系主要源自社交媒體的交往而形成;(2)個(gè)人所構(gòu)建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及其嵌入其中的社會(huì)資本。
3.身份認(rèn)同
陳映芳從公民權(quán)/市民權(quán)、國(guó)民待遇/市民待遇等對(duì)概念出發(fā),對(duì)身份認(rèn)同與制度安排進(jìn)行了分析。陳映芳認(rèn)為,citizenship中包含了“權(quán)利”(right)和“身份認(rèn)同”(identity)兩個(gè)組成要素,其中權(quán)利是citizenship的地位(staus of citizenship),是citizenship的法律層面(legal dimension),而身份認(rèn)同是citizenship的感受(feeling of citizenship),是citizenship的心理層面(phychological dimension),是法律地位之外的另一種歸屬政治共同體的方式。以這樣的一種理論為基本范式,不難做出這樣的推論:一種與市民權(quán)相關(guān)的社會(huì)事實(shí)的成立和維持,一方面有賴于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也與相關(guān)群體的身份認(rèn)同有關(guān)⑤。在目前的制度安排尚無太多松動(dòng)(尤其是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戶籍改革)的現(xiàn)實(shí)下,考察鄉(xiāng)城遷移者自我歸屬共同體的心理感受,就成為本次研究所要討論的主要內(nèi)容。
二、研究假設(shè)
社會(huì)學(xué)研究顯示,身份認(rèn)同既包括制度安排所賦予個(gè)體在法律層面的權(quán)利,也包括個(gè)體感受的心理層面的歸屬感。在目前制度安排尚無法松動(dòng)的現(xiàn)實(shí)困境下,鄉(xiāng)城遷移者也會(huì)在其社會(huì)交往中,通過建立各種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逐漸適應(yīng)、融入所在城市的生活。而這種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的建立,既有助于他們對(duì)其共同體的歸屬認(rèn)同,也可能提供某種資源使鄉(xiāng)城遷移者向著城市居民的身份認(rèn)同逐漸靠近。社交媒體是他們建構(gòu)其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的主要途徑,同時(shí)也是嵌入在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中社會(huì)資本的來源所在。我們力圖通過鄉(xiāng)城遷移者所使用的社交媒體所構(gòu)建的網(wǎng)絡(luò),及其嵌入在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中的社會(huì)資本分析,探討其與身份認(rèn)同的關(guān)系。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shè):
假設(shè)1:社交媒體的使用差異影響鄉(xiāng)城遷移者所建構(gòu)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
假設(shè)2:鄉(xiāng)城遷移者所構(gòu)建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的不同致使其擁有不同的社會(huì)資本;
假設(shè)3: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及其所蘊(yùn)含的社會(huì)資本影響鄉(xiāng)城遷移者的身份認(rèn)同。
我們假設(shè)社交媒體的使用會(huì)增加鄉(xiāng)城遷移者提高其社會(huì)資本的機(jī)會(huì),社會(huì)資本的增加又會(huì)有利于對(duì)其鄉(xiāng)城遷移者身份的改變。
三、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分析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diào)查的方式,調(diào)查時(shí)間為2014年10月12日、19日,共發(fā)放問卷136份,回收有效問卷120份,有效回收率88.2%。
樣本性別比例為,男性61.4%,女性38.6%。年齡構(gòu)成多為21—40歲的中青年人。考慮到調(diào)查主題與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有關(guān),故此樣本的年齡分布能較好地代表鄉(xiāng)城遷移者中使用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的人群。盡管所調(diào)查樣本均為智能手機(jī)的使用者,但其受教育程度仍較低,以初中教育程度為眾數(shù)(71.2%),其次為高中文化程度(16.1%)。月收入3000—4000元的比例為25.2%,2000元以下為19.1%,月收入在2000—3000元的比例相對(duì)較低為17.4%,4000元以上的比例為38.3%。與北京整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相比,這一人群屬于低收入、低文化程度的人群。
1.社交媒體使用情況
調(diào)查樣本對(duì)社交媒體使用的基本情況如表1。

表1 社交工具使用頻率
由于被訪者對(duì)微博社交媒體的使用量較低,互動(dòng)并不頻繁,在此主要關(guān)注以QQ、微信為交往工具的社交媒體。在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分析中,用來分析隸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即2-模網(wǎng)的方法和工具應(yīng)用較為廣泛,居住皮村的鄉(xiāng)城遷移者所建構(gòu)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也可以看做是2-模問題,可以使用相關(guān)的方法來分析其結(jié)構(gòu)特征。我們可以從被訪者社交媒體使用所構(gòu)建的關(guān)系網(wǎng)中分析其具有的性質(zhì)。
(1)度數(shù)中心度(Degree)指隸屬關(guān)系網(wǎng)中一個(gè)點(diǎn)所隸屬的事件數(shù),一個(gè)事件的度數(shù)中心度是該事件所擁有的行動(dòng)者數(shù)⑥。聚居在皮村的鄉(xiāng)城遷移者所建構(gòu)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以“認(rèn)識(shí)皮村的人”和“皮村之外其他機(jī)會(huì)認(rèn)識(shí)的人”作為與其關(guān)聯(lián)的事件,分析結(jié)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 QQ好友社交關(guān)系2-模網(wǎng)中心性分析

表4 微信好友社交關(guān)系2-模網(wǎng)中心性分析
(2)接近中心度(Closeness)根據(jù)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分析的原理,隸屬網(wǎng)絡(luò)所有的點(diǎn)僅僅與事件有關(guān)聯(lián),從一點(diǎn)出發(fā)的途徑必然首先經(jīng)過該行動(dòng)者所隸屬的各個(gè)事件;同樣,由于事件僅僅與行動(dòng)者有關(guān)聯(lián),因此所有從事件發(fā)出的途徑也必然首先經(jīng)過該事件所包含的各個(gè)行動(dòng)者⑦。仍然以“認(rèn)識(shí)皮村的人”和“皮村之外其他機(jī)會(huì)認(rèn)識(shí)的人”作為關(guān)聯(lián)事件,對(duì)被訪者的接近中心度的分析見表3、表4.
(3)中間中心度(Betweenne)關(guān)注的是,只有當(dāng)一個(gè)事件的行動(dòng)者不屬于其他事件時(shí),該事件的中間中心度增加。在隸屬網(wǎng)絡(luò)中,由于每對(duì)行動(dòng)者之間的聯(lián)絡(luò)都要通過行動(dòng)者參與的各種事件來完成,因此,事件總是處于行動(dòng)者之間的捷徑上,與之類似,對(duì)各對(duì)事件之間的聯(lián)絡(luò)都要通過行動(dòng)者來完成,因此行動(dòng)者總是處于事件之間的捷徑上。以通過社交媒體“認(rèn)識(shí)皮村的人”和“皮村之外其他機(jī)會(huì)認(rèn)識(shí)的人”作為關(guān)聯(lián)事件,計(jì)算被訪者的中間中心度如表3、表4。
可以看出,度數(shù)中心度最高的群體是“同鄉(xiāng)朋友”和“家人親戚”,度數(shù)中心度最低的群體是“居住在皮村的人”和“皮村之外其他機(jī)會(huì)認(rèn)識(shí)的人”,同時(shí)度數(shù)中心度最高者,即“同鄉(xiāng)朋友”和“家人親戚”的接近中心度和中間中心度也最高,說明這兩個(gè)群體是農(nóng)民工QQ/微信好友社交網(wǎng)絡(luò)中的核心交往點(diǎn);同時(shí),度數(shù)中心度低的群體“居住在皮村的人”和“皮村之外其他機(jī)會(huì)認(rèn)識(shí)的人”相比,“皮村之外其他機(jī)會(huì)認(rèn)識(shí)的人”接近中心度和中間中心度最低,說明通過社交媒體所結(jié)識(shí)的皮村之外的人,在農(nóng)民工的QQ/微信好友社交網(wǎng)絡(luò)中未能占據(jù)中心位置。也即,皮村的鄉(xiāng)城遷移者在社交媒體上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以地緣和親緣為核心,盡管他們身處異鄉(xiāng)的北京皮村,同鄉(xiāng)/親戚朋友仍是其通過社交媒體互動(dòng)的核心圈子。
鑒于此,實(shí)證數(shù)據(jù)驗(yàn)證了假設(shè)1。
2.社會(huì)資本的測(cè)量
本文以社交媒體建構(gòu)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中的職業(yè)來檢視鄉(xiāng)城遷移者社會(huì)資本的異同。在職業(yè)聲望和職業(yè)權(quán)力中,有學(xué)者認(rèn)為職業(yè)權(quán)力所蘊(yùn)含的社會(huì)資本高于職業(yè)聲望⑧。但由于在本研究中,在鄉(xiāng)城遷移者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中,頗具職業(yè)權(quán)力的人離他們的現(xiàn)實(shí)生活較為隔離,因此,仍以職業(yè)聲望作為社會(huì)資本的衡量指標(biāo),分別對(duì)其社交媒體(QQ、微信)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的好友職業(yè)進(jìn)行比對(duì)。從圖1至圖4可以看出,無論QQ還是微信所建構(gòu)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在認(rèn)識(shí)皮村外的人所建構(gòu)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公務(wù)員、醫(yī)生、律師的節(jié)點(diǎn)面積大,聯(lián)系較為密集,他們所擁有的職業(yè)聲望可為與之密切聯(lián)系的鄉(xiāng)城遷移者帶來一定的社會(huì)資本。而不認(rèn)識(shí)皮村之外的人所建構(gòu)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技術(shù)人員、企業(yè)經(jīng)理、工程師是聯(lián)系較為密集的人。這一點(diǎn)可以從鄉(xiāng)城遷移者在建筑工地、工廠企業(yè)工作的現(xiàn)實(shí)中得到印證。
教師是以上兩類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中聯(lián)系都為密集的職業(yè),這一點(diǎn)可從我們的實(shí)地調(diào)查中得到印證:皮村工人活動(dòng)中心通過慈善機(jī)構(gòu)捐贈(zèng)、發(fā)行打工者原創(chuàng)唱片獲得的版稅籌建了皮村同心實(shí)驗(yàn)學(xué)校⑨,居住此地的鄉(xiāng)城遷移者的孩子大多就讀于該校,學(xué)校教師成為他們溝通孩子學(xué)習(xí)的重要對(duì)象。

圖1 “認(rèn)識(shí)皮村之外的人”被訪者的QQ好友職業(yè)類別

圖2 “不認(rèn)識(shí)皮村之外的人”被訪者的QQ好友職業(yè)類別

圖3 “認(rèn)識(shí)皮村之外的人”被訪者的微信好友職業(yè)類別

圖4 “不認(rèn)識(shí)皮村之外的人”被訪者的微信好友職業(yè)類別
為進(jìn)一步分析使用社交媒體的程度與其建構(gòu)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在此對(duì)社交媒體的使用程度進(jìn)行劃分,即“經(jīng)常互動(dòng)的好友數(shù)量大于10”為重度使用者,小于等于10,為輕度使用者。并對(duì)其與社交媒體(QQ、微信)所建構(gòu)的社會(huì)關(guān)系進(jìn)行獨(dú)立性分析,如表5所示。在社交媒體的重度使用者所建構(gòu)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嵌入其中的社會(huì)資本高于社交媒體的輕度使用者(卡方值為8.954,自由度df=2,顯著性水平為0.011,見表3—6)。
對(duì)微信的使用程度與其嵌入于社交媒體的社會(huì)資本進(jìn)行分析,得出同樣的結(jié)論。
鑒于此,實(shí)證數(shù)據(jù)驗(yàn)證了假設(shè)2。

表5 QQ使用程度與QQ好友范圍的交叉分析

表3—6 卡方檢驗(yàn)

表7 微信使用程度與微信好友范圍的交叉分析
3.社交媒體使用與身份認(rèn)同
對(duì)于身份認(rèn)同,在此次調(diào)查中涉及兩個(gè)問題,其一,調(diào)查被訪者更愿意或更習(xí)慣于他人對(duì)自己的稱謂。如陳映芳在一篇關(guān)于農(nóng)民工身份認(rèn)同與制度安排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概念使用的差異,部分地反映了研究者價(jià)值立場(chǎng)和問題意識(shí)的不同。即使我們是以客觀的實(shí)際情形為依據(jù)來定義研究對(duì)象,但研究者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身份、地位的應(yīng)然性的認(rèn)知,必然會(huì)影響到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社會(huì)屬性的界定和對(duì)他們的實(shí)際權(quán)利狀況的判斷,也會(huì)影響到視野的射程所及”⑩。因此本研究沿用陳映芳提出的對(duì)農(nóng)民工的新稱謂“鄉(xiāng)城遷移者”。其二,發(fā)展5級(jí)李克特量表,分析被訪者身份認(rèn)同的現(xiàn)實(shí)狀況。

表8 卡方檢驗(yàn)
對(duì)第1個(gè)問題的分析結(jié)果如表9,幾乎一半的被訪者選擇了“無所謂”的態(tài)度,打工者、外來務(wù)工人員更為其所認(rèn)可(兩者之和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對(duì)皮村文化活動(dòng)中心提倡的“新工人”(11)的選項(xiàng)的選擇不到十分之一。這種選擇說明被訪者對(duì)身份與職業(yè)分離的無奈,也表現(xiàn)出對(duì)新工人稱謂的信心不足。

表9 更愿意別人稱呼您
另外,為探明被訪者通過社交媒體所構(gòu)建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及嵌入其中的社會(huì)資本與其身份認(rèn)同的關(guān)系,以是否通過社交媒體結(jié)識(shí)皮村之外的人為劃分標(biāo)準(zhǔn),將被訪者的社交媒體好友范圍分為兩組,與被訪者所能接受的稱謂進(jìn)行卡方分析,結(jié)果顯示,卡方值為6.790,顯著性水平為0.341(見表10)。也即,在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涉及媒體的使用中,農(nóng)民工建構(gòu)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及其嵌入的社會(huì)資本與其身份認(rèn)同并沒有顯著關(guān)系。

表10 卡方檢驗(yàn)
為了進(jìn)一步驗(yàn)證以上結(jié)論,在此將對(duì)5級(jí)量表中涉及身份認(rèn)同的題目加總,將其與被訪者社交媒體好友范圍進(jìn)行方差分析。結(jié)果顯示,兩組被訪者在身份認(rèn)同程度均值不存在明顯差異,Sig.=0.355(見表12)。說明在社交媒體使用中,鄉(xiāng)城遷移者通過社交媒體建構(gòu)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及其嵌入的社會(huì)資本與其身份
認(rèn)同之間并沒有顯著差異。實(shí)證數(shù)據(jù)否認(rèn)了假設(shè)3。

表11 組統(tǒng)計(jì)量

表12 獨(dú)立樣本檢驗(yàn)
對(duì)這個(gè)結(jié)論,筆者在實(shí)地調(diào)查中進(jìn)行問卷調(diào)查時(shí),與被訪者的交談中可知,通過社交媒體構(gòu)建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的差異(這種差異反映為網(wǎng)頂?shù)母叩停┘捌淝度肫渲械纳鐣?huì)資本的多寡與其身份認(rèn)同并沒有很大聯(lián)系,多數(shù)被訪者表示自己就是打工者。社交媒體確實(shí)拓寬了其交往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假設(shè)1和假設(shè)2。但是由于中國(guó)當(dāng)下戶籍制度的安排,至少在近一個(gè)時(shí)期內(nèi)尚無松動(dòng)的跡象。筆者認(rèn)為這些資源只是對(duì)其改善生活或獲得工作信息渠道有所影響,但是對(duì)其身份認(rèn)同無法產(chǎn)生直接的明顯影響。身份認(rèn)同的改變更多依賴于戶籍制度的改革與安排。
四、結(jié)語
通過對(duì)皮村鄉(xiāng)城遷移者的實(shí)地問卷調(diào)查筆者得出以下結(jié)論:(1)隨著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發(fā)展,鄉(xiāng)城遷移者通過社交媒體構(gòu)建和擴(kuò)大了其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為其生活工作信息的獲取帶來一定的便利和益處;(2)社交媒體所構(gòu)建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及嵌入其中的社會(huì)資本擴(kuò)大或增加了鄉(xiāng)城遷移者的資源與人脈;(3)由于我國(guó)當(dāng)下戶籍制度的松動(dòng)尚待時(shí)日,身份認(rèn)同更多依賴法律上的認(rèn)可。
(本文系國(guó)家留基委2013年資助項(xiàng)目的研究成果。)
注釋:
① 三年前,筆者對(duì)皮村的自我“賦權(quán)”文化建設(shè)活動(dòng)進(jìn)行了調(diào)研。筆者認(rèn)為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為皮村的鄉(xiāng)城遷移者提供了建構(gòu)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資本的有效渠道,而對(duì)弱化鄉(xiāng)城遷移者的身份認(rèn)同有著某種影響。這就是本研究繼續(xù)選皮村作為觀察點(diǎn)的緣由。
② 對(duì)由農(nóng)村流入城市、滯留城市的人群,有不同的稱謂,農(nóng)民工是其中普遍采用的。但是由于本研究認(rèn)為,稱謂反映出主體對(duì)客體的身份的認(rèn)識(shí),映射了主體內(nèi)心的對(duì)客體認(rèn)識(shí)的取向。因此,在本文中采用學(xué)者陳映芳的方法,稱其為鄉(xiāng)城遷移者。
③ 張文宏:《中國(guó)的社會(huì)資本研究:概念、操作化測(cè)量和經(jīng)驗(yàn)研究》,《江蘇社會(huì)科學(xué)》,2007年第3期。
④ 羅家德:《社會(huì)網(wǎng)分析講義》,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頁。
⑤ 陳映芳:《農(nóng)民工:制度安排與身份認(rèn)同》,《社會(huì)學(xué)研究》,2005年第3期。
⑥⑦ 劉軍:《整體網(wǎng)分析講義——UCINET軟件實(shí)用指南》,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234頁。
⑧ 尉建文、趙延?xùn)|:《權(quán)力還是聲望?——社會(huì)資本測(cè)量的爭(zhēng)論與測(cè)量》,《社會(huì)學(xué)研究》,2011年第3期。
⑨(11) 王錫苓、汪舒、苑婧:《農(nóng)民工的自我賦權(quán)與影響:以北京朝陽區(qū)皮村為個(gè)案》,《現(xiàn)代傳播》,2011年第10期。
⑩ 陳映芳:《農(nóng)民工:制度安排與身份認(rèn)同》,《社會(huì)學(xué)研究》,2005年第3期。
(作者王錫苓系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新聞傳播學(xué)部新聞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李笑欣系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新聞傳播學(xué)部新聞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
【責(zé)任編輯:潘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