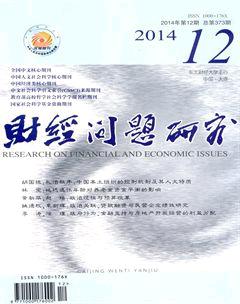地方政府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管理體制研究
丁兆君
摘要:與其他一般性公共服務(wù)相比,由于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建設(shè)更具有經(jīng)濟(jì)發(fā)展先導(dǎo)性以及對(duì)地方經(jīng)濟(jì)明顯的拉動(dòng)效應(yīng),地方政府在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入方面的資金規(guī)模與增長(zhǎng)速度要遠(yuǎn)遠(yuǎn)高于其對(duì)基礎(chǔ)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和社會(huì)保障等公共服務(wù)的投入。而單純依靠政府的“賣(mài)地”收入以及政府債務(wù)來(lái)維持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建設(shè)和運(yùn)營(yíng)是難以持續(xù)的,地方政府債務(wù)風(fēng)險(xiǎn)的凸顯已然證明了這一點(diǎn)。因此,本文在對(duì)部分地區(qū)的地方融資平臺(tái)調(diào)研基礎(chǔ)上,總結(jié)歸納了地方政府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中存在的問(wèn)題,并提出利用“市場(chǎng)化”理念建立“雙主體”的地方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供給體制的具體構(gòu)想。
關(guān)鍵詞:地方政府;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體制;“雙主體”
中圖分類(lèi)號(hào):F81045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1000176X(2014)12007905
一、研究背景
在多方面體制和機(jī)制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將轄區(qū)內(nèi)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建設(shè)作為其履行政府職能的重中之重,同時(shí)在理論上,地方性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供給的確是地方政府的職能范疇;這就要求地方政府有足夠的可支配收入作為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的資金來(lái)源,但事實(shí)上,由于現(xiàn)有財(cái)政體制框架內(nèi)地方政府“財(cái)力無(wú)法與事權(quán)相匹配”,地方政府對(duì)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投資資金只能依靠以“土地財(cái)政”為支撐的政府收入以及各種顯性或隱性的地方政府債務(wù)。各地土地出讓規(guī)模以及地方融資平臺(tái)債務(wù)數(shù)量一直保持猛增勢(shì)頭的現(xiàn)狀也證明了地方政府及其下屬機(jī)構(gòu)很容易通過(guò)土地抵押或者財(cái)政擔(dān)保的方式突破財(cái)政預(yù)算或法律約束實(shí)現(xiàn)對(duì)外舉債\[1\]。
盡管地方政府通過(guò)體制外舉債融資進(jìn)行地方性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項(xiàng)目建設(shè)具有一定的內(nèi)在必要性及合理性,但這種地方政府“自創(chuàng)”性的投融資體制缺乏制度監(jiān)管以及風(fēng)險(xiǎn)控制,已經(jīng)使得地方政府債務(wù)風(fēng)險(xiǎn)問(wèn)題凸顯;在未來(lái)宏觀經(jīng)濟(jì)增速趨緩、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進(jìn)一步升級(jí)調(diào)整的情況下,以“賣(mài)地”或地方債務(wù)急劇增長(zhǎng)的方式為擴(kuò)張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資籌資,將會(huì)導(dǎo)致難以控制的地方性財(cái)政風(fēng)險(xiǎn)。中央相關(guān)部門(mén)在此過(guò)程中,為防范地方政府的債務(wù)危機(jī),曾多次發(fā)文對(duì)地方政府的對(duì)外融資行為進(jìn)行“糾錯(cuò)”式的指導(dǎo)或限制。例如:2010年7月發(fā)改委規(guī)定,凡是以地方財(cái)政應(yīng)收賬款作擔(dān)保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tái)公司所申請(qǐng)債券將全部停批;2011年發(fā)改委發(fā)\[2881\]號(hào)文件,明確規(guī)定,城投公司的主營(yíng)收入70%需要來(lái)自自身,政府補(bǔ)貼只能占30%;國(guó)開(kāi)行也開(kāi)始大大縮減對(duì)地方政府融資平臺(tái)的放款規(guī)模,而在2009年之前,國(guó)開(kāi)行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tái)最為主要的資金提供者。中央相關(guān)部門(mén)對(duì)地方融資平臺(tái)融資渠道的“單方堵截”式的治理,只能是對(duì)地方債務(wù)增長(zhǎng)規(guī)模起到一時(shí)的控制,但無(wú)法從根本上解決地方政府“財(cái)力吃緊”、融資渠道單一與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資需求增長(zhǎng)之間的客觀矛盾。同時(shí),隨著我國(guó)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加快,以及城鎮(zhèn)化理念的提升,在農(nóng)村建立與城市基本水平一致的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和基本公共服務(wù)是實(shí)現(xiàn)城鄉(xiāng)統(tǒng)籌一體化的必然選擇;這就意味著未來(lái)發(fā)展中,地方政府將面臨更多的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提供問(wèn)題。
本文從梳理我國(guó)地方政府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體制演化進(jìn)程入手,通過(guò)對(duì)重慶“八大投”模式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分析,總結(jié)出目前我國(guó)地方政府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體制面臨的問(wèn)題;在借鑒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制度較為成熟國(guó)家的先進(jìn)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提出以“市場(chǎng)化”理念創(chuàng)新我國(guó)地方政府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體制的具體構(gòu)想。
二、“土地財(cái)政”到“土地金融”的地方政府投融資管理體制
在現(xiàn)有的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自創(chuàng)性”的用于城市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項(xiàng)目投資建設(shè)資金的投融資管理體制大致經(jīng)歷了一個(gè)從“土地財(cái)政”模式到“土地金融”模式的演進(jìn)過(guò)程。
1地方政府“土地財(cái)政”式的投融資管理體制
“土地財(cái)政”是地方政府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土地管理法》第二章第八條“城市市區(qū)的土地屬于國(guó)家所有”的規(guī)定,在“國(guó)家統(tǒng)一所有,政府分級(jí)代表”的國(guó)有資產(chǎn)管理體制下,憑借行政區(qū)劃內(nèi)城市土地的所有權(quán),按照國(guó)有土地有償使用原則,建立起的與土地相關(guān)的收益體系。“土地財(cái)政”是我國(guó)各級(jí)地方政府在城鎮(zhèn)化初期,獲取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資金的重要來(lái)源之一,2008年國(guó)家審計(jì)署對(duì)全國(guó)土地出讓金使用情況進(jìn)行了審計(jì),2004—2006年北京等11個(gè)城市共實(shí)現(xiàn)土地出讓凈收益2 61869億元。其中,用于城市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的支出約占土地出讓凈收益的80%[2]。為規(guī)范地方政府“儲(chǔ)地—賣(mài)地—建設(shè)”的這一行為,加強(qiáng)對(duì)數(shù)額龐大的土地出讓金的管理,2007年1月1日起,國(guó)家規(guī)定將土地出讓金、基礎(chǔ)設(shè)施配套費(fèi)納入地方基金預(yù)算管理,實(shí)行徹底的“收支兩條線”,結(jié)束了土地出讓金作為非稅收入游離于預(yù)算之外的歷史。
雖然“土地財(cái)政”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資金難問(wèn)題,從實(shí)踐來(lái)看,體制內(nèi)融資基本不能滿足地方基礎(chǔ)設(shè)施投資需要,更多的是發(fā)揮財(cái)政兜底作用。另外,國(guó)家對(duì)地方的“土地財(cái)政”加強(qiáng)了控制和規(guī)范,2006年出臺(tái)的《國(guó)有土地使用權(quán)出讓收支管理辦法》嚴(yán)格規(guī)定了土地出讓金的使用途徑,在提留規(guī)定比例的各項(xiàng)規(guī)費(fèi)(包括國(guó)有土地收益基金、農(nóng)業(yè)土地開(kāi)發(fā)資金和新增建設(shè)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fèi)),剔除征地拆遷補(bǔ)償?shù)瘸杀拘蚤_(kāi)支,以及按國(guó)家政策指定提取的保障房、教育和農(nóng)田水利建設(shè)資金后,作為地方政府機(jī)動(dòng)財(cái)力支持其他領(lǐng)域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的空間基本不存在\[3\]。
2地方政府“土地金融”式的投融資管理體制
我國(guó)地方政府在《預(yù)算法》約束下,不具備獨(dú)立的直接或間接對(duì)外融資權(quán)利。除了直接掛牌出讓土地,獲取新城改造、改擴(kuò)建基礎(chǔ)設(shè)施資金之外;各級(jí)地方政府紛紛成立了事業(yè)單位性質(zhì)或者是國(guó)有獨(dú)資公司性質(zhì)的“融資平臺(tái)”,在財(cái)政管理尚存漏洞的情況下,“自創(chuàng)性”地開(kāi)拓融資渠道。地方政府將其幾乎全部可以自主支配的“富裕”資金和資產(chǎn)都通過(guò)融資平臺(tái)注入到了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建設(shè)中,通過(guò)平臺(tái)進(jìn)行對(duì)外大規(guī)模融資,加快推進(jìn)各地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項(xiàng)目的建設(shè)。之后的城鎮(zhèn)化進(jìn)程更是助推了各級(jí)地方政府“賣(mài)土地”、“找貸款”、“上項(xiàng)目”等諸多投融資行為。尤其是2008年4萬(wàn)億投資的刺激政策出臺(tái)后,各家商業(yè)銀行超過(guò)國(guó)開(kāi)行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債權(quán)人,其放貸資金主要用于地方政府安排的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項(xiàng)目建設(shè)所需要的資本性支出。根據(jù)中國(guó)人民銀行《2009年四季度地方投融資平臺(tái)貸款情況專(zhuān)項(xiàng)調(diào)查》的結(jié)果顯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tái)項(xiàng)目貸款中約有2/3直接投向公共設(shè)施管理業(yè)、電力、燃?xì)饧八纳a(chǎn)和供應(yīng)業(yè)以及交通運(yùn)輸業(yè)等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管理項(xiàng)目。
圖1地方政府“土地金融”式的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體制資料來(lái)源:作者整理。
在“自創(chuàng)性”投融資體制中,融資平臺(tái)成為政府經(jīng)營(yíng)城市、開(kāi)拓融資渠道的媒介,市場(chǎng)理念、金融理念逐漸被注入到以政府為主導(dǎo)的投融資行為中;地方政府從單純的“儲(chǔ)地—賣(mài)地—建設(shè)”的“土地財(cái)政”模式升級(jí)到了“儲(chǔ)地—融資—建設(shè)”的“土地金融”模式,從簡(jiǎn)單的“賣(mài)地”到綜合的“用地”來(lái)獲取建設(shè)資金。但無(wú)論是“土地財(cái)政”模式還是“土地金融”模式,地方政府始終沒(méi)有擺脫“以土地?fù)Q資金”的籌資運(yùn)營(yíng)邏輯。
三、地方政府“土地金融”式的投融資管理體制面臨的問(wèn)題
1地方政府作為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唯一責(zé)任主體,負(fù)擔(dān)沉重且不可持續(xù)
盡管重慶“八大投”重慶“八大投”指2003年創(chuàng)建的,由重慶政府擁有、授權(quán)經(jīng)營(yíng)的重慶城投、高發(fā)、高投、地產(chǎn)、建投、開(kāi)投、水務(wù)控股和水投公司等融資平臺(tái)。作為為地方基礎(chǔ)設(shè)施進(jìn)行投融資活動(dòng)的地方融資平臺(tái),一直是國(guó)內(nèi)業(yè)界備受關(guān)注和爭(zhēng)議的一個(gè)范例。重慶模式運(yùn)作獲取的建設(shè)資金規(guī)模是顯而易見(jiàn)的,以2009年為例,為了應(yīng)對(duì)全球金融危機(jī)以及配套中央的4萬(wàn)億投資,由重慶市主導(dǎo)的道路、橋梁、旅游、水務(wù)、舊城改造等公共基礎(chǔ)建設(shè)項(xiàng)目的投資就超過(guò)了5 200億元。而僅在2011年,重慶就完成固定資產(chǎn)投資7 600億元,占當(dāng)年重慶經(jīng)濟(jì)生產(chǎn)總值比例高達(dá)76%。 數(shù)據(jù)來(lái)源:http://wwwchinatimescc/site1/hxsb/html/2012-04/02/content_6774htm 從資金的籌集力度以及投資規(guī)模來(lái)看,重慶模式是成功的,但在這些數(shù)字背后還存在著巨大的風(fēng)險(xiǎn)和亟待解決的問(wèn)題。
1模式部分滲透了市場(chǎng)化、金融化的運(yùn)作理念,以市場(chǎng)利益為指引,通過(guò)盤(pán)活國(guó)有土地等資源、利用金融手段進(jìn)行了大規(guī)模的投融資活動(dòng);但無(wú)論是之前的“土地財(cái)政”,還是現(xiàn)在的“土地金融”,地方政府始終是地方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提供的唯一責(zé)任者及風(fēng)險(xiǎn)主體。地方政府在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管理體制中,既是“裁判員”也是“運(yùn)動(dòng)員”,負(fù)責(zé)從項(xiàng)目立項(xiàng)、規(guī)劃設(shè)計(jì)、資金籌集、施工建設(shè),到運(yùn)營(yíng)管理、后期維護(hù)的整個(gè)過(guò)程。這種投融資管理體制,一方面加重了政府的財(cái)政資金以及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的成本和負(fù)擔(dān),例如:重慶財(cái)政局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1年重慶財(cái)政開(kāi)支高達(dá)3 961億元,其財(cái)政資金缺口超過(guò)1 000億; 數(shù)據(jù)來(lái)源:http://wwwchinatimescc/site1/hxsb/html/2012-04/02/content_6774htm,另一方面在某些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建設(shè)及運(yùn)營(yíng)上,由政府提供的效率要遠(yuǎn)遠(yuǎn)低于私人提供的效率。在較為成熟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條件下,部分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提供完全可以通過(guò)“公私合營(yíng)”的方式完成。因此,我國(guó)地方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提供的真正市場(chǎng)化,是投資主體、責(zé)任主體的市場(chǎng)化、多元化,繼而發(fā)展為投融資模式的市場(chǎng)化、手段的多元化;而不單純是政府“賣(mài)地掙錢(qián)搞建設(shè)”還是“用地借錢(qián)搞建設(shè)”的問(wèn)題。
2融資平臺(tái)以國(guó)有土地作為運(yùn)營(yíng)載體,運(yùn)營(yíng)連續(xù)性取決于地價(jià)
融資平臺(tái)以地方政府為背景,盡管相對(duì)于地方政府而言是獨(dú)立法人,但其由政府派生的屬性決定了融資平臺(tái)的規(guī)模、資產(chǎn)數(shù)量、融資能力都受當(dāng)?shù)卣芰Φ挠绊懸约靶姓袨榈南拗疲胤秸娜谫Y平臺(tái)運(yùn)營(yíng)現(xiàn)狀不容樂(lè)觀。
一是融資平臺(tái)的資產(chǎn)質(zhì)量不高,融資能力有限。注入融資平臺(tái)的資產(chǎn)來(lái)自于財(cái)政的撥付,除了國(guó)有土地外大部分為非經(jīng)營(yíng)性資產(chǎn)(市政路橋、隧道等),不能用于抵押、擔(dān)保等融資行為,限制了融資平臺(tái)的融資規(guī)模。二是缺乏穩(wěn)定的經(jīng)營(yíng)收入,盈利能力欠佳,可持續(xù)發(fā)展后勁不足。平臺(tái)公司基本上沒(méi)有經(jīng)營(yíng)性資產(chǎn)和經(jīng)營(yíng)收入,承建的項(xiàng)目主要以社會(huì)效益為主,項(xiàng)目本身沒(méi)有或有很少的投資回報(bào),貸款的還本付息主要是依靠出讓儲(chǔ)備土地的收入。三是償債機(jī)制不健全,公司缺乏償還貸款的能力。平臺(tái)公司項(xiàng)目貸款的還款來(lái)源主要是通過(guò)項(xiàng)目自身的收益和財(cái)政預(yù)算內(nèi)外統(tǒng)籌資金。雖然部分項(xiàng)目與財(cái)政部門(mén)簽訂了項(xiàng)目資產(chǎn)回購(gòu)協(xié)議,但這只是為了滿足前期的融資條件,在實(shí)際操作中因財(cái)力緊張等原因很難落實(shí)。
因此,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地方融資平臺(tái)的建立和運(yùn)營(yíng)主要還是在圍繞地方的土地資源做文章,地方政府是否能夠籌集到足夠的資金、是否能夠維持投融資的循環(huán),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的土地儲(chǔ)備量以及土地的增值額。例如:2011年前后,重慶市政府陸續(xù)向“八大投”注入了1萬(wàn)畝的土地儲(chǔ)備用于當(dāng)?shù)貛鬃缃髽虻慕ㄔO(shè),平臺(tái)公司先是利用土地從銀行獲得抵押貸款,大橋建成后,使用土地增值的收益對(duì)基建項(xiàng)目進(jìn)行回購(gòu),前提是周邊土地在這一過(guò)程中獲得了增值。整個(gè)項(xiàng)目的運(yùn)作風(fēng)險(xiǎn)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土地收益,而在國(guó)家政策調(diào)整以及市場(chǎng)波動(dòng)的影響下,土地收益的不確定性最終會(huì)影響到地方政府融資平臺(tái)資金運(yùn)營(yíng)鏈條的完整性和可持續(xù)性。
3地方政府雙重身份界定不清,缺乏制約無(wú)序擴(kuò)張
我國(guó)地方政府作為公共事務(wù)管理者和國(guó)有資產(chǎn)所有者的雙重身份體現(xiàn)在,一方面以公共預(yù)算資金投資建設(shè)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履行公共事務(wù)管理者的職能;另一方面以土地等國(guó)有資產(chǎn)注入到融資平臺(tái),經(jīng)過(guò)資本運(yùn)營(yíng)籌集資金注入到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中,從而履行國(guó)有資產(chǎn)所有者的職能。但在實(shí)踐中,一是對(duì)融資平臺(tái)的性質(zhì)界定不清,理論上,各地方政府成立的融資平臺(tái)應(yīng)屬于國(guó)有獨(dú)資企業(yè)的性質(zhì),實(shí)際上很多地方將融資平臺(tái)下設(shè)在財(cái)政部門(mén),將其定義為事業(yè)單位,各自的責(zé)、權(quán)、利劃分不清,且不統(tǒng)一。二是對(duì)政府和融資平臺(tái)的財(cái)務(wù)關(guān)系界定不清,地方融資平臺(tái)以政府為背景,可輕易獲得土地等國(guó)有資源的注資、可以政府財(cái)政應(yīng)收賬款作為擔(dān)保、與政府財(cái)政部門(mén)關(guān)系密切;盡管名義上是獨(dú)立法人,但投資風(fēng)險(xiǎn)約束機(jī)制和責(zé)任機(jī)制難以落實(shí),資金使用效率低下。三是融資平臺(tái)缺乏完整規(guī)范的預(yù)算管理制度,缺乏獨(dú)立第三方的審核、監(jiān)督和評(píng)價(jià)。地方政府大規(guī)模的土地出讓金在2007年才被納入政府性基金管理,但這一預(yù)算還沒(méi)進(jìn)入到同級(jí)人大的審批監(jiān)督階段,從理論上講,仍屬于“非法”的政府性收入。而且,目前較為規(guī)范的公共財(cái)政預(yù)算中部分資金進(jìn)入到融資平臺(tái)后,人大對(duì)這筆資金使用的監(jiān)督鏈條中斷,而通過(guò)融資平臺(tái)運(yùn)營(yíng)的全部資金都沒(méi)有納入到預(yù)算管理。因此,地方政府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的科學(xué)性、必要性無(wú)從考評(píng)。2010年開(kāi)始重慶計(jì)劃10年內(nèi)投入1 000億元用于建設(shè)4 000萬(wàn)平方米公租房;其中,政府投入占30%,剩下的70%都要依靠市場(chǎng)進(jìn)行融資,數(shù)據(jù)來(lái)源:http://wwwchinatimescc/site1/hxsb/html/2012-04/02/content_6774htm “地方性融資平臺(tái)蘊(yùn)含巨大風(fēng)險(xiǎn)。”銀監(jiān)會(huì)對(duì)此曾提出警告。
4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渠道單一,社會(huì)資源動(dòng)員力不足
地方政府仍然是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唯一責(zé)任主體就意味著在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投融資改革中并未進(jìn)行真正的市場(chǎng)化改革。從社會(huì)資金資源的角度來(lái)看,目前的投融資體制是資金通過(guò)銀行或投資機(jī)構(gòu)間接注入到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中,并沒(méi)有創(chuàng)造條件使社會(huì)閑置資金得到充分利用;從社會(huì)技術(shù)管理資源的角度來(lái)看,政府單方面的主體地位嚴(yán)重忽視了私人部門(mén)在某些公共基礎(chǔ)或公共事業(yè)領(lǐng)域的專(zhuān)業(yè)技術(shù)和管理方法。盡管在實(shí)踐中,部分地區(qū)已經(jīng)嘗試進(jìn)行BOT模式BOT模式的英文全稱(chēng)是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設(shè)—經(jīng)營(yíng)—轉(zhuǎn)讓模式。的探索,但所占地方政府整個(gè)投融資規(guī)模的比重過(guò)小,而且僅限于部分經(jīng)營(yíng)性基建項(xiàng)目的籌資。因此,我國(guó)現(xiàn)有的以地方政府為主體的“土地金融”式的投融資管理體制還未真正起到撬動(dòng)、引導(dǎo)并動(dòng)員社會(huì)資源的作用。
四、地方政府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融資管理體制的創(chuàng)新構(gòu)想
針對(duì)以上分析的四方面問(wèn)題,結(jié)合國(guó)外一些國(guó)家的先進(jìn)經(jīng)驗(yàn),筆者認(rèn)為,我國(guó)地方政府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理念是“市場(chǎng)化”、指導(dǎo)原則是“政府性主導(dǎo)、市場(chǎng)化運(yùn)營(yíng);整合國(guó)有資產(chǎn)、動(dòng)員社會(huì)資本”。改變政府的角色、轉(zhuǎn)變其職能;為社會(huì)資源的利用搭建科學(xué)合理的平臺(tái),實(shí)現(xiàn)地方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利益共享、風(fēng)險(xiǎn)共擔(dān)的“雙主體”機(jī)制(如圖1所示)。
圖1地方政府“土地金融”式的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體制資料來(lái)源:作者整理。
在“自創(chuàng)性”投融資體制中,融資平臺(tái)成為政府經(jīng)營(yíng)城市、開(kāi)拓融資渠道的媒介,市場(chǎng)理念、金融理念逐漸被注入到以政府為主導(dǎo)的投融資行為中;地方政府從單純的“儲(chǔ)地—賣(mài)地—建設(shè)”的“土地財(cái)政”模式升級(jí)到了“儲(chǔ)地—融資—建設(shè)”的“土地金融”模式,從簡(jiǎn)單的“賣(mài)地”到綜合的“用地”來(lái)獲取建設(shè)資金。但無(wú)論是“土地財(cái)政”模式還是“土地金融”模式,地方政府始終沒(méi)有擺脫“以土地?fù)Q資金”的籌資運(yùn)營(yíng)邏輯。
三、地方政府“土地金融”式的投融資管理體制面臨的問(wèn)題
1地方政府作為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唯一責(zé)任主體,負(fù)擔(dān)沉重且不可持續(xù)
盡管重慶“八大投”重慶“八大投”指2003年創(chuàng)建的,由重慶政府擁有、授權(quán)經(jīng)營(yíng)的重慶城投、高發(fā)、高投、地產(chǎn)、建投、開(kāi)投、水務(wù)控股和水投公司等融資平臺(tái)。作為為地方基礎(chǔ)設(shè)施進(jìn)行投融資活動(dòng)的地方融資平臺(tái),一直是國(guó)內(nèi)業(yè)界備受關(guān)注和爭(zhēng)議的一個(gè)范例。重慶模式運(yùn)作獲取的建設(shè)資金規(guī)模是顯而易見(jiàn)的,以2009年為例,為了應(yīng)對(duì)全球金融危機(jī)以及配套中央的4萬(wàn)億投資,由重慶市主導(dǎo)的道路、橋梁、旅游、水務(wù)、舊城改造等公共基礎(chǔ)建設(shè)項(xiàng)目的投資就超過(guò)了5 200億元。而僅在2011年,重慶就完成固定資產(chǎn)投資7 600億元,占當(dāng)年重慶經(jīng)濟(jì)生產(chǎn)總值比例高達(dá)76%。 數(shù)據(jù)來(lái)源:http://wwwchinatimescc/site1/hxsb/html/2012-04/02/content_6774htm 從資金的籌集力度以及投資規(guī)模來(lái)看,重慶模式是成功的,但在這些數(shù)字背后還存在著巨大的風(fēng)險(xiǎn)和亟待解決的問(wèn)題。
1模式部分滲透了市場(chǎng)化、金融化的運(yùn)作理念,以市場(chǎng)利益為指引,通過(guò)盤(pán)活國(guó)有土地等資源、利用金融手段進(jìn)行了大規(guī)模的投融資活動(dòng);但無(wú)論是之前的“土地財(cái)政”,還是現(xiàn)在的“土地金融”,地方政府始終是地方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提供的唯一責(zé)任者及風(fēng)險(xiǎn)主體。地方政府在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管理體制中,既是“裁判員”也是“運(yùn)動(dòng)員”,負(fù)責(zé)從項(xiàng)目立項(xiàng)、規(guī)劃設(shè)計(jì)、資金籌集、施工建設(shè),到運(yùn)營(yíng)管理、后期維護(hù)的整個(gè)過(guò)程。這種投融資管理體制,一方面加重了政府的財(cái)政資金以及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的成本和負(fù)擔(dān),例如:重慶財(cái)政局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1年重慶財(cái)政開(kāi)支高達(dá)3 961億元,其財(cái)政資金缺口超過(guò)1 000億; 數(shù)據(jù)來(lái)源:http://wwwchinatimescc/site1/hxsb/html/2012-04/02/content_6774htm,另一方面在某些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建設(shè)及運(yùn)營(yíng)上,由政府提供的效率要遠(yuǎn)遠(yuǎn)低于私人提供的效率。在較為成熟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條件下,部分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提供完全可以通過(guò)“公私合營(yíng)”的方式完成。因此,我國(guó)地方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提供的真正市場(chǎng)化,是投資主體、責(zé)任主體的市場(chǎng)化、多元化,繼而發(fā)展為投融資模式的市場(chǎng)化、手段的多元化;而不單純是政府“賣(mài)地掙錢(qián)搞建設(shè)”還是“用地借錢(qián)搞建設(shè)”的問(wèn)題。
2融資平臺(tái)以國(guó)有土地作為運(yùn)營(yíng)載體,運(yùn)營(yíng)連續(xù)性取決于地價(jià)
融資平臺(tái)以地方政府為背景,盡管相對(duì)于地方政府而言是獨(dú)立法人,但其由政府派生的屬性決定了融資平臺(tái)的規(guī)模、資產(chǎn)數(shù)量、融資能力都受當(dāng)?shù)卣芰Φ挠绊懸约靶姓袨榈南拗疲胤秸娜谫Y平臺(tái)運(yùn)營(yíng)現(xiàn)狀不容樂(lè)觀。
一是融資平臺(tái)的資產(chǎn)質(zhì)量不高,融資能力有限。注入融資平臺(tái)的資產(chǎn)來(lái)自于財(cái)政的撥付,除了國(guó)有土地外大部分為非經(jīng)營(yíng)性資產(chǎn)(市政路橋、隧道等),不能用于抵押、擔(dān)保等融資行為,限制了融資平臺(tái)的融資規(guī)模。二是缺乏穩(wěn)定的經(jīng)營(yíng)收入,盈利能力欠佳,可持續(xù)發(fā)展后勁不足。平臺(tái)公司基本上沒(méi)有經(jīng)營(yíng)性資產(chǎn)和經(jīng)營(yíng)收入,承建的項(xiàng)目主要以社會(huì)效益為主,項(xiàng)目本身沒(méi)有或有很少的投資回報(bào),貸款的還本付息主要是依靠出讓儲(chǔ)備土地的收入。三是償債機(jī)制不健全,公司缺乏償還貸款的能力。平臺(tái)公司項(xiàng)目貸款的還款來(lái)源主要是通過(guò)項(xiàng)目自身的收益和財(cái)政預(yù)算內(nèi)外統(tǒng)籌資金。雖然部分項(xiàng)目與財(cái)政部門(mén)簽訂了項(xiàng)目資產(chǎn)回購(gòu)協(xié)議,但這只是為了滿足前期的融資條件,在實(shí)際操作中因財(cái)力緊張等原因很難落實(shí)。
因此,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地方融資平臺(tái)的建立和運(yùn)營(yíng)主要還是在圍繞地方的土地資源做文章,地方政府是否能夠籌集到足夠的資金、是否能夠維持投融資的循環(huán),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的土地儲(chǔ)備量以及土地的增值額。例如:2011年前后,重慶市政府陸續(xù)向“八大投”注入了1萬(wàn)畝的土地儲(chǔ)備用于當(dāng)?shù)貛鬃缃髽虻慕ㄔO(shè),平臺(tái)公司先是利用土地從銀行獲得抵押貸款,大橋建成后,使用土地增值的收益對(duì)基建項(xiàng)目進(jìn)行回購(gòu),前提是周邊土地在這一過(guò)程中獲得了增值。整個(gè)項(xiàng)目的運(yùn)作風(fēng)險(xiǎn)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土地收益,而在國(guó)家政策調(diào)整以及市場(chǎng)波動(dòng)的影響下,土地收益的不確定性最終會(huì)影響到地方政府融資平臺(tái)資金運(yùn)營(yíng)鏈條的完整性和可持續(xù)性。
3地方政府雙重身份界定不清,缺乏制約無(wú)序擴(kuò)張
我國(guó)地方政府作為公共事務(wù)管理者和國(guó)有資產(chǎn)所有者的雙重身份體現(xiàn)在,一方面以公共預(yù)算資金投資建設(shè)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履行公共事務(wù)管理者的職能;另一方面以土地等國(guó)有資產(chǎn)注入到融資平臺(tái),經(jīng)過(guò)資本運(yùn)營(yíng)籌集資金注入到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中,從而履行國(guó)有資產(chǎn)所有者的職能。但在實(shí)踐中,一是對(duì)融資平臺(tái)的性質(zhì)界定不清,理論上,各地方政府成立的融資平臺(tái)應(yīng)屬于國(guó)有獨(dú)資企業(yè)的性質(zhì),實(shí)際上很多地方將融資平臺(tái)下設(shè)在財(cái)政部門(mén),將其定義為事業(yè)單位,各自的責(zé)、權(quán)、利劃分不清,且不統(tǒng)一。二是對(duì)政府和融資平臺(tái)的財(cái)務(wù)關(guān)系界定不清,地方融資平臺(tái)以政府為背景,可輕易獲得土地等國(guó)有資源的注資、可以政府財(cái)政應(yīng)收賬款作為擔(dān)保、與政府財(cái)政部門(mén)關(guān)系密切;盡管名義上是獨(dú)立法人,但投資風(fēng)險(xiǎn)約束機(jī)制和責(zé)任機(jī)制難以落實(shí),資金使用效率低下。三是融資平臺(tái)缺乏完整規(guī)范的預(yù)算管理制度,缺乏獨(dú)立第三方的審核、監(jiān)督和評(píng)價(jià)。地方政府大規(guī)模的土地出讓金在2007年才被納入政府性基金管理,但這一預(yù)算還沒(méi)進(jìn)入到同級(jí)人大的審批監(jiān)督階段,從理論上講,仍屬于“非法”的政府性收入。而且,目前較為規(guī)范的公共財(cái)政預(yù)算中部分資金進(jìn)入到融資平臺(tái)后,人大對(duì)這筆資金使用的監(jiān)督鏈條中斷,而通過(guò)融資平臺(tái)運(yùn)營(yíng)的全部資金都沒(méi)有納入到預(yù)算管理。因此,地方政府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的科學(xué)性、必要性無(wú)從考評(píng)。2010年開(kāi)始重慶計(jì)劃10年內(nèi)投入1 000億元用于建設(shè)4 000萬(wàn)平方米公租房;其中,政府投入占30%,剩下的70%都要依靠市場(chǎng)進(jìn)行融資,數(shù)據(jù)來(lái)源:http://wwwchinatimescc/site1/hxsb/html/2012-04/02/content_6774htm “地方性融資平臺(tái)蘊(yùn)含巨大風(fēng)險(xiǎn)。”銀監(jiān)會(huì)對(duì)此曾提出警告。
4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渠道單一,社會(huì)資源動(dòng)員力不足
地方政府仍然是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唯一責(zé)任主體就意味著在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投融資改革中并未進(jìn)行真正的市場(chǎng)化改革。從社會(huì)資金資源的角度來(lái)看,目前的投融資體制是資金通過(guò)銀行或投資機(jī)構(gòu)間接注入到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中,并沒(méi)有創(chuàng)造條件使社會(huì)閑置資金得到充分利用;從社會(huì)技術(shù)管理資源的角度來(lái)看,政府單方面的主體地位嚴(yán)重忽視了私人部門(mén)在某些公共基礎(chǔ)或公共事業(yè)領(lǐng)域的專(zhuān)業(yè)技術(shù)和管理方法。盡管在實(shí)踐中,部分地區(qū)已經(jīng)嘗試進(jìn)行BOT模式BOT模式的英文全稱(chēng)是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設(shè)—經(jīng)營(yíng)—轉(zhuǎn)讓模式。的探索,但所占地方政府整個(gè)投融資規(guī)模的比重過(guò)小,而且僅限于部分經(jīng)營(yíng)性基建項(xiàng)目的籌資。因此,我國(guó)現(xiàn)有的以地方政府為主體的“土地金融”式的投融資管理體制還未真正起到撬動(dòng)、引導(dǎo)并動(dòng)員社會(huì)資源的作用。
四、地方政府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融資管理體制的創(chuàng)新構(gòu)想
針對(duì)以上分析的四方面問(wèn)題,結(jié)合國(guó)外一些國(guó)家的先進(jìn)經(jīng)驗(yàn),筆者認(rèn)為,我國(guó)地方政府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理念是“市場(chǎng)化”、指導(dǎo)原則是“政府性主導(dǎo)、市場(chǎng)化運(yùn)營(yíng);整合國(guó)有資產(chǎn)、動(dòng)員社會(huì)資本”。改變政府的角色、轉(zhuǎn)變其職能;為社會(huì)資源的利用搭建科學(xué)合理的平臺(tái),實(shí)現(xiàn)地方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利益共享、風(fēng)險(xiǎn)共擔(dān)的“雙主體”機(jī)制(如圖1所示)。
圖1地方政府“土地金融”式的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體制資料來(lái)源:作者整理。
在“自創(chuàng)性”投融資體制中,融資平臺(tái)成為政府經(jīng)營(yíng)城市、開(kāi)拓融資渠道的媒介,市場(chǎng)理念、金融理念逐漸被注入到以政府為主導(dǎo)的投融資行為中;地方政府從單純的“儲(chǔ)地—賣(mài)地—建設(shè)”的“土地財(cái)政”模式升級(jí)到了“儲(chǔ)地—融資—建設(shè)”的“土地金融”模式,從簡(jiǎn)單的“賣(mài)地”到綜合的“用地”來(lái)獲取建設(shè)資金。但無(wú)論是“土地財(cái)政”模式還是“土地金融”模式,地方政府始終沒(méi)有擺脫“以土地?fù)Q資金”的籌資運(yùn)營(yíng)邏輯。
三、地方政府“土地金融”式的投融資管理體制面臨的問(wèn)題
1地方政府作為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唯一責(zé)任主體,負(fù)擔(dān)沉重且不可持續(xù)
盡管重慶“八大投”重慶“八大投”指2003年創(chuàng)建的,由重慶政府擁有、授權(quán)經(jīng)營(yíng)的重慶城投、高發(fā)、高投、地產(chǎn)、建投、開(kāi)投、水務(wù)控股和水投公司等融資平臺(tái)。作為為地方基礎(chǔ)設(shè)施進(jìn)行投融資活動(dòng)的地方融資平臺(tái),一直是國(guó)內(nèi)業(yè)界備受關(guān)注和爭(zhēng)議的一個(gè)范例。重慶模式運(yùn)作獲取的建設(shè)資金規(guī)模是顯而易見(jiàn)的,以2009年為例,為了應(yīng)對(duì)全球金融危機(jī)以及配套中央的4萬(wàn)億投資,由重慶市主導(dǎo)的道路、橋梁、旅游、水務(wù)、舊城改造等公共基礎(chǔ)建設(shè)項(xiàng)目的投資就超過(guò)了5 200億元。而僅在2011年,重慶就完成固定資產(chǎn)投資7 600億元,占當(dāng)年重慶經(jīng)濟(jì)生產(chǎn)總值比例高達(dá)76%。 數(shù)據(jù)來(lái)源:http://wwwchinatimescc/site1/hxsb/html/2012-04/02/content_6774htm 從資金的籌集力度以及投資規(guī)模來(lái)看,重慶模式是成功的,但在這些數(shù)字背后還存在著巨大的風(fēng)險(xiǎn)和亟待解決的問(wèn)題。
1模式部分滲透了市場(chǎng)化、金融化的運(yùn)作理念,以市場(chǎng)利益為指引,通過(guò)盤(pán)活國(guó)有土地等資源、利用金融手段進(jìn)行了大規(guī)模的投融資活動(dòng);但無(wú)論是之前的“土地財(cái)政”,還是現(xiàn)在的“土地金融”,地方政府始終是地方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提供的唯一責(zé)任者及風(fēng)險(xiǎn)主體。地方政府在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管理體制中,既是“裁判員”也是“運(yùn)動(dòng)員”,負(fù)責(zé)從項(xiàng)目立項(xiàng)、規(guī)劃設(shè)計(jì)、資金籌集、施工建設(shè),到運(yùn)營(yíng)管理、后期維護(hù)的整個(gè)過(guò)程。這種投融資管理體制,一方面加重了政府的財(cái)政資金以及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的成本和負(fù)擔(dān),例如:重慶財(cái)政局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1年重慶財(cái)政開(kāi)支高達(dá)3 961億元,其財(cái)政資金缺口超過(guò)1 000億; 數(shù)據(jù)來(lái)源:http://wwwchinatimescc/site1/hxsb/html/2012-04/02/content_6774htm,另一方面在某些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建設(shè)及運(yùn)營(yíng)上,由政府提供的效率要遠(yuǎn)遠(yuǎn)低于私人提供的效率。在較為成熟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條件下,部分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提供完全可以通過(guò)“公私合營(yíng)”的方式完成。因此,我國(guó)地方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提供的真正市場(chǎng)化,是投資主體、責(zé)任主體的市場(chǎng)化、多元化,繼而發(fā)展為投融資模式的市場(chǎng)化、手段的多元化;而不單純是政府“賣(mài)地掙錢(qián)搞建設(shè)”還是“用地借錢(qián)搞建設(shè)”的問(wèn)題。
2融資平臺(tái)以國(guó)有土地作為運(yùn)營(yíng)載體,運(yùn)營(yíng)連續(xù)性取決于地價(jià)
融資平臺(tái)以地方政府為背景,盡管相對(duì)于地方政府而言是獨(dú)立法人,但其由政府派生的屬性決定了融資平臺(tái)的規(guī)模、資產(chǎn)數(shù)量、融資能力都受當(dāng)?shù)卣芰Φ挠绊懸约靶姓袨榈南拗疲胤秸娜谫Y平臺(tái)運(yùn)營(yíng)現(xiàn)狀不容樂(lè)觀。
一是融資平臺(tái)的資產(chǎn)質(zhì)量不高,融資能力有限。注入融資平臺(tái)的資產(chǎn)來(lái)自于財(cái)政的撥付,除了國(guó)有土地外大部分為非經(jīng)營(yíng)性資產(chǎn)(市政路橋、隧道等),不能用于抵押、擔(dān)保等融資行為,限制了融資平臺(tái)的融資規(guī)模。二是缺乏穩(wěn)定的經(jīng)營(yíng)收入,盈利能力欠佳,可持續(xù)發(fā)展后勁不足。平臺(tái)公司基本上沒(méi)有經(jīng)營(yíng)性資產(chǎn)和經(jīng)營(yíng)收入,承建的項(xiàng)目主要以社會(huì)效益為主,項(xiàng)目本身沒(méi)有或有很少的投資回報(bào),貸款的還本付息主要是依靠出讓儲(chǔ)備土地的收入。三是償債機(jī)制不健全,公司缺乏償還貸款的能力。平臺(tái)公司項(xiàng)目貸款的還款來(lái)源主要是通過(guò)項(xiàng)目自身的收益和財(cái)政預(yù)算內(nèi)外統(tǒng)籌資金。雖然部分項(xiàng)目與財(cái)政部門(mén)簽訂了項(xiàng)目資產(chǎn)回購(gòu)協(xié)議,但這只是為了滿足前期的融資條件,在實(shí)際操作中因財(cái)力緊張等原因很難落實(shí)。
因此,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地方融資平臺(tái)的建立和運(yùn)營(yíng)主要還是在圍繞地方的土地資源做文章,地方政府是否能夠籌集到足夠的資金、是否能夠維持投融資的循環(huán),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的土地儲(chǔ)備量以及土地的增值額。例如:2011年前后,重慶市政府陸續(xù)向“八大投”注入了1萬(wàn)畝的土地儲(chǔ)備用于當(dāng)?shù)貛鬃缃髽虻慕ㄔO(shè),平臺(tái)公司先是利用土地從銀行獲得抵押貸款,大橋建成后,使用土地增值的收益對(duì)基建項(xiàng)目進(jìn)行回購(gòu),前提是周邊土地在這一過(guò)程中獲得了增值。整個(gè)項(xiàng)目的運(yùn)作風(fēng)險(xiǎn)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土地收益,而在國(guó)家政策調(diào)整以及市場(chǎng)波動(dòng)的影響下,土地收益的不確定性最終會(huì)影響到地方政府融資平臺(tái)資金運(yùn)營(yíng)鏈條的完整性和可持續(xù)性。
3地方政府雙重身份界定不清,缺乏制約無(wú)序擴(kuò)張
我國(guó)地方政府作為公共事務(wù)管理者和國(guó)有資產(chǎn)所有者的雙重身份體現(xiàn)在,一方面以公共預(yù)算資金投資建設(shè)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履行公共事務(wù)管理者的職能;另一方面以土地等國(guó)有資產(chǎn)注入到融資平臺(tái),經(jīng)過(guò)資本運(yùn)營(yíng)籌集資金注入到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中,從而履行國(guó)有資產(chǎn)所有者的職能。但在實(shí)踐中,一是對(duì)融資平臺(tái)的性質(zhì)界定不清,理論上,各地方政府成立的融資平臺(tái)應(yīng)屬于國(guó)有獨(dú)資企業(yè)的性質(zhì),實(shí)際上很多地方將融資平臺(tái)下設(shè)在財(cái)政部門(mén),將其定義為事業(yè)單位,各自的責(zé)、權(quán)、利劃分不清,且不統(tǒng)一。二是對(duì)政府和融資平臺(tái)的財(cái)務(wù)關(guān)系界定不清,地方融資平臺(tái)以政府為背景,可輕易獲得土地等國(guó)有資源的注資、可以政府財(cái)政應(yīng)收賬款作為擔(dān)保、與政府財(cái)政部門(mén)關(guān)系密切;盡管名義上是獨(dú)立法人,但投資風(fēng)險(xiǎn)約束機(jī)制和責(zé)任機(jī)制難以落實(shí),資金使用效率低下。三是融資平臺(tái)缺乏完整規(guī)范的預(yù)算管理制度,缺乏獨(dú)立第三方的審核、監(jiān)督和評(píng)價(jià)。地方政府大規(guī)模的土地出讓金在2007年才被納入政府性基金管理,但這一預(yù)算還沒(méi)進(jìn)入到同級(jí)人大的審批監(jiān)督階段,從理論上講,仍屬于“非法”的政府性收入。而且,目前較為規(guī)范的公共財(cái)政預(yù)算中部分資金進(jìn)入到融資平臺(tái)后,人大對(duì)這筆資金使用的監(jiān)督鏈條中斷,而通過(guò)融資平臺(tái)運(yùn)營(yíng)的全部資金都沒(méi)有納入到預(yù)算管理。因此,地方政府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的科學(xué)性、必要性無(wú)從考評(píng)。2010年開(kāi)始重慶計(jì)劃10年內(nèi)投入1 000億元用于建設(shè)4 000萬(wàn)平方米公租房;其中,政府投入占30%,剩下的70%都要依靠市場(chǎng)進(jìn)行融資,數(shù)據(jù)來(lái)源:http://wwwchinatimescc/site1/hxsb/html/2012-04/02/content_6774htm “地方性融資平臺(tái)蘊(yùn)含巨大風(fēng)險(xiǎn)。”銀監(jiān)會(huì)對(duì)此曾提出警告。
4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渠道單一,社會(huì)資源動(dòng)員力不足
地方政府仍然是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唯一責(zé)任主體就意味著在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投融資改革中并未進(jìn)行真正的市場(chǎng)化改革。從社會(huì)資金資源的角度來(lái)看,目前的投融資體制是資金通過(guò)銀行或投資機(jī)構(gòu)間接注入到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中,并沒(méi)有創(chuàng)造條件使社會(huì)閑置資金得到充分利用;從社會(huì)技術(shù)管理資源的角度來(lái)看,政府單方面的主體地位嚴(yán)重忽視了私人部門(mén)在某些公共基礎(chǔ)或公共事業(yè)領(lǐng)域的專(zhuān)業(yè)技術(shù)和管理方法。盡管在實(shí)踐中,部分地區(qū)已經(jīng)嘗試進(jìn)行BOT模式BOT模式的英文全稱(chēng)是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設(shè)—經(jīng)營(yíng)—轉(zhuǎn)讓模式。的探索,但所占地方政府整個(gè)投融資規(guī)模的比重過(guò)小,而且僅限于部分經(jīng)營(yíng)性基建項(xiàng)目的籌資。因此,我國(guó)現(xiàn)有的以地方政府為主體的“土地金融”式的投融資管理體制還未真正起到撬動(dòng)、引導(dǎo)并動(dòng)員社會(huì)資源的作用。
四、地方政府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融資管理體制的創(chuàng)新構(gòu)想
針對(duì)以上分析的四方面問(wèn)題,結(jié)合國(guó)外一些國(guó)家的先進(jìn)經(jīng)驗(yàn),筆者認(rèn)為,我國(guó)地方政府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投融資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理念是“市場(chǎng)化”、指導(dǎo)原則是“政府性主導(dǎo)、市場(chǎng)化運(yùn)營(yíng);整合國(guó)有資產(chǎn)、動(dòng)員社會(huì)資本”。改變政府的角色、轉(zhuǎn)變其職能;為社會(huì)資源的利用搭建科學(xué)合理的平臺(tái),實(shí)現(xiàn)地方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利益共享、風(fēng)險(xiǎn)共擔(dān)的“雙主體”機(jī)制(如圖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