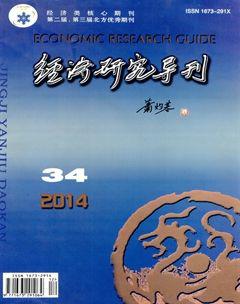中國行政問責客體范圍探析
婁成彬
摘 要:行政問責客體是行政問責制要素之一,即向“誰”問責。只有厘清行政問責的指向對象,在實際操作中才能充分發揮行政問責的功能,踐行行政問責的意義。行政問責制是對行政權力的監督與制約的制度。以行政權力為主線進行解析,界定行政問責客體范圍,確定行政問責客體構成要件,以此來分析中國行政問責客體屬性及簡要的分類。通過對行政問責客體范圍的分析、界定與分類,對行政問責理論構建與實踐運行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行政權力;行政問責制;行政問責客體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34-0257-02
行政問責客體作為行政問責制組成要素之一,是行政問責制的組成要件與指向對象,是“責任”的承擔主體。對行政問責客體進行深入研究有助于豐富和完善行政問責制的理論體系,也有利于加強行政問責實踐的指導意義和可操作性。當前,中國學者對行政問責客體范圍的界定仍有分歧,有以下兩種觀點:一是認為任何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都應當成為行政問責的指向對象,包括國家的立法機關、國家行政機關、國家司法機關的公職人員。二是認為行政問責的客體應該是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務人員。學者們依據自身研究的方法與角度的不同,對行政問責客體范圍的界定迥異。此類分歧的產生,歸根結底是學者們在定義行政問責制概念及內涵之初就已出現分歧,從而行政問責客體概念及內涵隨之嬗變,進而導致行政問責客體范圍產生差異。因此,筆者試圖從授權及權力運行角度出發來作為解析行政問責客體相關概念的切入點。
一、行政問責客體辨析之源——行政問責制
現代的行政問責理論源自西方,較早對行政問責概念進行規范界定的見于美國《公共行政實用辭典》,書中將行政問責界定為“由法律或組織授權的高官,必須對其組織職位范圍內的行為或其社會范圍內的行為接受質問、承擔責任。”[1]中國學者鄒健在《問責制概念及特征的探討》中對問責制的定義“所謂問責制,就是關于特定組織或個人通過一定的程序追究沒有履行好分內之事的公共權力使用者,使其承擔政治責任、道德責任或法律責任、接受譴責、處罰等消極后果的所有辦法、條例等制度的總稱。”[2] 王宏偉在《中國行政問責制的完善》中概括問責制含義為“指對政府及其官員的一切行為和后果都必須而且能夠追究責任的制度,其實質是通過各種形式的責任約束、限制、規范政府權力和官員行為,最終達到權為民所用的目的。”[3]周亞越在《行政問責制研究》中提出“行政問責制是問責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是指特定的問責主體針對各級政府及其公務員承擔的職責和義務的履行情況而實施的,并要求其承擔否定性結果的一種制度規范。”[4] 周仲秋在《論行政問責制》中指出“行政問責制是政府實現其行政責任的一種自律或自我控制。所謂行政自律機制,是政府憑借自身的行政權力所建立的一種內部控制機制。”[5]
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學者們對行政問責制的表述不盡相同。國內學者相關研究多以政府為研究對象提出“政府問責制”,政府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政府指包括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在內的國家機關,狹義的政府僅指國家行政機關。對于政府兩種涵義的不同界定,行政問責的概念與內涵就會發生變化,從而出現不同的問責對象。問責制與行政問責制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問責客體與行政問責客體也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問責作為一種遍及社會的關系形式存在于許多社會環境和社會關系之中,而行政問責常常與公共行政聯系在一起被視為一種行政結構和治理方式。
二、行政問責客體解析之鑰——行政權力
無論是“政府問責制”還是“行政問責制”,學界普遍認同問責制的核心是對國家權力的監督與制約,以達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目的。那么,權力可以作為打開“未知之門”的鑰匙。問責源自授權。人民將權力授予國家,國家作為公共權力的掌權者,對人民負責,國家機關在行使公共權力的同時,受人民的監督與制約,并接受人民的問責。人民視為問責主體,國家機關視為問責客體。可以說人民對國家機關的問責是一種廣義的問責,是人民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而行政問責無法等同于廣義的國家問責,行政活動通過行政權力運行來實現,所以行政問責的范圍相對較小,是一種狹義的問責。無論是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還是古德諾的政治與行政二分法,都是將行政機關的行政權力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來看,所以行政問責應是行政問責主體對行政權力主體的監督與制約。由此,我們可以推導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行政問責客體應該是行政權力的擁有者和實施者即行政權力主體。行政權力主體在其行使行政權力時,產生不當或違法行為等否定性后果,就要接受問責。
行政權力是政治權力的一種,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理解的行政權力普遍地存在于各種公共組織中。政府、非政府組織、政黨、各社會團體都可以成為行政權力的主體。但是,除專司行政管理職能的國家機關中的行政機關外。其他機構所擁有的行政權力類似于管理權力。這些機構行使的權力并不具備行政權力的全部功能及特征,所以只能稱其為“行政性權力”,“行政性權力”的主體也只稱之為“準行政權力主體”。狹義上理解的行政權力就是指專司行政管理職能的國家機關中的行政機關。廣義的問責制,問責客體范圍較廣,行政權力主體及準行政權力主體都包含其中。而狹義的問責制即行政問責制,其問責客體則屬于行政權力主體,那么行政問責客體則包含于行政權力主體之中。
三、中國行政問責客體分類之逕——行政主體
在中國,行政主體享有國家行政權力,是從事行政管理活動并獨立承擔由此產生的法律責任的組織。中國行政主體主要指國家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需要說明的是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所行使的多是管理權力,可以作為問責客體,甚至是與行政問責客體并列,雖然現代治理理論從管理的公共性特征角度把此類組織看作是行政主體,但并不具備行政權力的所有功能和特征,依據行政權力的特征和功能等特性應將這些組織排除在行政問責客體范圍之外。那么,在中國可以作為行政問責客體的行政主體的主要有:endprint
(一)中央人民政府
中國憲法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國務院由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組成。并實行總理負責制。各部、各委員會實行部長、主任負責制。國務院作為中國最高行政機關,依據憲法和法律的相關規定,享有管理全國的行政事務的職權,可以制定行政法規,規定行政措施,發布決定和命令。因此,國務院是行政主體,相應的可以作為行政問責的客體。國務院各部、委和行、署、廳作為國務院的工作部門或職能機關,依法對于某一方面的行政事務行使全國范圍內的管理權限。它們要接受國務院的領導和監督,執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又可以在法定的職權范圍內,以自己的名義實施活動,并承擔相應的責任。所以,國務院的組成部門也可以看做行政主體,相應地也作為行政問責客體。與此類似,國務院的直屬機構、各部、委管理的國家局等機構根據其各自特點。都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依法行使專門事務的行政職權。因此,它們也具有行政主體資格,相應地作為行政問責客體。
(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
中國憲法明確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是地方國家行政機關,作為本級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管理地方各級所轄范圍內的行政事務。與國務院一致,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同樣實行首長負責制。中國地方國家行政機關分為省(自治區、直轄市)、市(自治州、直轄市的區)、縣、鄉四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省長、自治區主席、市長、州長、縣長、區長、鄉長、鎮長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并報告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既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也是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在其管轄的地域范圍內,依照憲法和有關法律所規定的權限,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各項行政事務,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作為行政主體也是行政問責的客體。同樣地,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職能部門、派出機關能以自己的名義作出行政行為并對行政后果承擔法律責任,實際上履行了—級人民政府的職能。所以都具有行政主體資格,也就相應地作為行政問責客體。
四、結語
行政權力是行政問責客體范圍界定的中軸線,追根溯源借以限定行政問責范圍,由上而下厘清行政問責客體范圍。經過授權的行政權力擁有者包含行政問責客體,行政主體擁有行政權力,那么行政問責客體屬于行政主體。在中國的問責實踐中,行政主體之中的國家行政機關視為行政問責客體,即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行政問責客體的限定并不是削減了行政問責的意義和功能,對于行政問責制以外的部分可以借用涵蓋意義更廣泛的問責制等相關制度來補充,如黨內問責制、司法問責制、人大機關問責制等。行政問責客體范圍的明確有助于行政問責功能的體現,更有助于行政問責機制的有效實施。行政問責客體范圍的界定是規范行政權力的運行與監督,也是構建責任政府和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參考文獻:
[1] Jay M.Shafritz.The facts on file dictiona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M].New York: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1985.
[2] 鄒建.問責制概念及特征的探討[J].中共南寧市委黨校學報,2006,(3):47-49.
[3] 王宏偉.中國行政問責制的完善[J].經濟師,2006,(3):22-23.
[4] 周亞越.行政問責制研究[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36.
[5] 周仲秋.論行政問責制[J].社會科學,2004,(3):128.
[責任編輯 王曉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