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北京起航
蒲曉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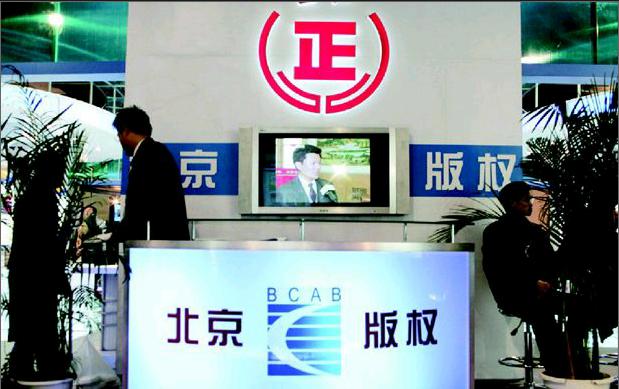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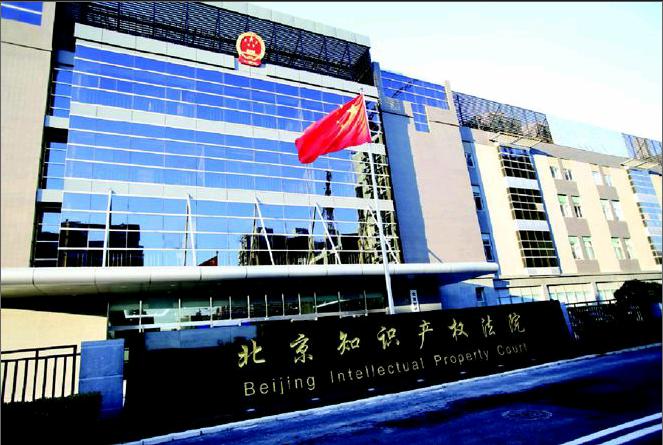
北京試水起航
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從提出到設(shè)立,一直在穩(wěn)步推進(jìn)。
在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ì)作出了“加強(qiáng)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運(yùn)用和保護(hù),健全技術(shù)創(chuàng)新激勵(lì)機(jī)制,探索建立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的重大部署。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huì)第十次會(huì)議通過《關(guān)于在北京、上海、廣州設(shè)立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的決定》(以下簡(jiǎn)稱《決定》),以立法形式宣布在北京、上海、廣州設(shè)立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并對(du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的機(jī)構(gòu)設(shè)置、案件管轄、法官任命等作了規(guī)定。
11月3日,最高法發(f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北京、上海、廣州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案件管轄的規(guī)定》(以下簡(jiǎn)稱《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案件管轄規(guī)定》),該規(guī)定共8條內(nèi)容,主要涉及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的案件管轄及審級(jí)關(guān)系,包括一審管轄、跨區(qū)域管轄、專屬管轄、二審管轄、上訴管轄及未結(jié)案件處理等。
“雖然《決定》對(du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的管轄案件類型、與上下級(jí)法院的關(guān)系等作了規(guī)定,但是相關(guān)規(guī)定仍需要進(jìn)一步明確,不少問題仍亟待解決。”最高人民法院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審判庭副庭長王闖在發(fā)布會(huì)上表示。
也就在最高法召開發(fā)布會(huì)的前一天,11月2日閉幕的北京市第十四屆人大常委會(huì)第十四次會(huì)議通過表決,任命宿遲為首任北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院長,陳錦川、宋魚水為副院長。會(huì)議還表決任命了北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的首批25名法官。
11月6日,穩(wěn)步推進(jìn)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在北京試水起航。西南政法大學(xué)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研究中心副主任鄧宏光表示,“成立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是司法體制改革頂層設(shè)計(jì)中的重要部分。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就像是一張白紙,可以用更科學(xué)的方法來勾畫新的發(fā)展藍(lán)圖。從這個(gè)角度來看,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的設(shè)立可以說是開創(chuàng)性的改革。”
實(shí)行員額制,設(shè)立技術(shù)調(diào)查室
成立當(dāng)日,北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就已開始受理案件。
關(guān)于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管轄的第一審案件的范圍,《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案件管轄規(guī)定》列出了三類案件:一是專利、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shè)計(jì)、技術(shù)秘密、計(jì)算機(jī)軟件等技術(shù)類民事和行政案件;二是對(duì)國務(wù)院部門或者縣級(jí)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涉及著作權(quán)、商標(biāo)、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等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行政案件;三是涉及馳名商標(biāo)認(rèn)定的民事案件。
“北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成立后,我們預(yù)計(jì)將面臨非常繁重的審判任務(wù)。”宿遲說,“光是涉及到國家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局和國家工商總局商標(biāo)局的專利行政案件和商標(biāo)行政案件每年就在1萬件以上,將占到我們審判任務(wù)的80%以上。面對(duì)這個(gè)挑戰(zhàn),我們只有深入研究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案件規(guī)律,不斷提高審判效率。”
據(jù)了解,北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內(nèi)設(shè)4個(gè)審判庭,技術(shù)調(diào)查室和法警隊(duì)兩個(gè)司法輔助機(jī)構(gòu)以及一個(gè)綜合行政機(jī)構(gòu)。其中,北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司法輔助人員中專門設(shè)置了法官助理和技術(shù)調(diào)查官,分別負(fù)責(zé)協(xié)助法官進(jìn)行法律研究、起草法律文書和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專業(yè)技術(shù)意見。
“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將借鑒日本、韓國、中國臺(tái)灣地區(qū)在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專設(shè)技術(shù)調(diào)查官的成熟經(jīng)驗(yàn),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技術(shù)調(diào)查官制度。”最高人民法院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庭庭長宋曉明表示,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制定相關(guān)司法解釋和工作規(guī)范,明確技術(shù)調(diào)查官的職能定位、配置數(shù)量、選任條件、管理模式、職權(quán)行使等問題。
技術(shù)調(diào)查官作為法官的技術(shù)助手,協(xié)助法官理解和查明案件的專業(yè)技術(shù)問題。這將進(jìn)一步提高技術(shù)事實(shí)查明的科學(xué)性、專業(yè)性和中立性,保證技術(shù)類案件審理的公正與高效。有關(guān)專家建議,在具體制度設(shè)計(jì)的時(shí)候,也要注意規(guī)范技術(shù)調(diào)查官參與案件調(diào)查的方式、權(quán)限、監(jiān)督機(jī)制等,避免法官對(duì)技術(shù)調(diào)查官意見過度依賴。
除了設(shè)立技術(shù)調(diào)查官制度,法院主審法官將實(shí)行員額制。據(jù)悉,北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法官員額30名,首批選任法官22名,4人被任命為庭長。
“目前來看,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法官員額是非常少的,和其他法院比少,因?yàn)閺?qiáng)調(diào)的是主審法官,要突出法官的核心地位,所以搞分類管理,法官助理、其他行政人員和法官是分類的,這樣在一個(gè)法院編制固定的情況下,法官的數(shù)量肯定相對(duì)比較少,這樣才突出法官的主體作用。”王闖介紹說。
“在國外,很多判決的草稿都是由助手來寫,法官主要是在關(guān)鍵問題上把關(guān)。在德國聯(lián)邦法院,每年都會(huì)有很多從州里中級(jí)法院和高級(jí)法院過來交流的法官,負(fù)責(zé)幫助法官分析案情、撰寫判決草稿等工作。這樣的交流,還有利于在法官系統(tǒng)中形成審判思路上的統(tǒng)一。”同濟(jì)大學(xué)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學(xué)院教授劉曉海今年7月曾去德國專利法院訪問。
“法官在法治建設(shè)中的作用至關(guān)重要,司法的精英化應(yīng)當(dāng)是將來的發(fā)展方向。員額制是必然的發(fā)展方向,只有這樣才能遴選出精英,讓精英化的法官得到尊重和認(rèn)同。”鄧宏光說。
鄧宏光同時(shí)認(rèn)為,在過渡期間實(shí)行員額制可能會(huì)有陣痛,“畢竟所有的改革會(huì)觸痛相關(guān)方面的利益,進(jìn)入的標(biāo)準(zhǔn)是什么、有沒有退出機(jī)制等問題都需要考慮”。
劉曉海建議提高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法官的報(bào)酬和待遇。“當(dāng)然,同時(shí)也要加大他們的責(zé)任,這種責(zé)任與收入對(duì)等的機(jī)制,在司法體制改革中對(duì)于審理其他案件的法官也有示范作用。”
“二合一”成最大亮點(diǎn)
“《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案件管轄規(guī)定》的最大亮點(diǎn)是,根據(jù)全國人大常委會(huì)《決定》的精神,徹底實(shí)現(xiàn)了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及其所在地高級(jí)人民法院民事和行政審判‘二合一,即由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及其所在地高級(jí)人民法院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審判庭統(tǒng)一管轄和審理涉及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全部民事和行政案件。”王闖在發(fā)布會(huì)上表示。
王闖介紹,這一亮點(diǎn)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
第一,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管轄的第一審案件,不僅包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授權(quán)確權(quán)類行政案件,還包括涉及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行政處罰、行政強(qiáng)制措施等引發(fā)的普通行政案件。
第二,在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轄區(qū)內(nèi),對(duì)基層人民法院第一審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民事和行政判決、裁定提起的上訴案件,均由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管轄,無論該第一審案件由基層法院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審判庭審理還是由行政審判庭審理。
第三,對(du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作出的第一審民事和行政判決、裁定提起的上訴案件,均由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所在地的高級(jí)人民法院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審判庭審理,不再分由該高級(jí)人民法院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審判庭和行政審判庭各自審理。
“這是我國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案件審判體制的重大革新,對(duì)于統(tǒng)一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案件裁判標(biāo)準(zhǔn)、提升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司法保護(hù)品質(zhì)具有重要意義。”王闖在發(fā)布會(huì)上對(duì)媒體表示。
將法律規(guī)定轉(zhuǎn)化為具體的司法判決,無疑是一個(gè)既具有高度技術(shù)性又具有實(shí)踐智慧性的過程。記者了解到,目前,我國對(duì)專利侵權(quán)具有管轄權(quán)的法院有100多家,不同的法院在知識(shí)背景、審理經(jīng)驗(yàn)方面,往往有著巨大的差別,以上述的等同原則適用為例,100多家法院對(duì)同一種技術(shù)改進(jìn)是否侵權(quán)可能有不同的意見,而不一致的判決結(jié)果只能給創(chuàng)新活動(dòng)帶來障礙。
“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的建立,就是為解決這種法律適用過程中的不一致性,從而對(duì)于后來的改進(jìn)技術(shù)相對(duì)于前人的專利權(quán)是否構(gòu)成侵權(quán)給出一個(gè)確定的答案,這種確定的答案所帶來的法律統(tǒng)一性給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帶來了確定性,而這種確定性又給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的法律風(fēng)險(xiǎn)帶來了可預(yù)測(cè)性,通過這種可預(yù)測(cè)性又為企業(yè)的長期經(jīng)濟(jì)規(guī)劃提供了有力的保證,我們理解這就是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對(duì)創(chuàng)新型社會(huì)作出的重要貢獻(xiàn)之一,也就是建立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對(duì)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積極意義。”國家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局發(fā)明審查部、高級(jí)審查員何春暉撰文表示。
實(shí)踐中,北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并未實(shí)行三合一的審判模式,但王闖認(rèn)為,在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設(shè)立之后,其他的法院已經(jīng)搞了三合一的,仍然要進(jìn)行三合一。據(jù)悉,2014年6月召開的全國法院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審判工作會(huì)議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陶凱元在講話里專門提出,“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的運(yùn)行和其他法院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審判三合一是并行不悖的。”
對(duì)于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在審判模式上的探索,鄧宏光對(duì)“三合一”模式表達(dá)了自己的疑問。“刑事涉及到一個(gè)國家的刑事司法統(tǒng)一,包括一些標(biāo)準(zhǔn),刑事與民事合一后,會(huì)不會(huì)出現(xiàn)以刑事相要挾影響民事的效果?如果仍然按照以前先刑事后民事的做法,很可能會(huì)讓現(xiàn)有的成果倒退。”
助推司法體制改革
2014年6月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lǐng)導(dǎo)小組第三次會(huì)議上,審議《關(guān)于設(shè)立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的方案》。習(xí)近平強(qiáng)調(diào),設(shè)立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也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基礎(chǔ)性、制度性措施的一個(gè)重要方面。
“從戰(zhàn)略發(fā)展的角度看,司法體制改革應(yīng)該從最容易的地方突破。相對(duì)于其他案件,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案件牽涉的利益面更小,也更容易改革,即使是在一定程度上失敗了也是可以承受。”鄧宏光分析道。
“所以,設(shè)立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不僅僅是中國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司法保護(hù)的重要制度,也是中國司法體制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中央關(guān)于司法改革,要在6個(gè)省市試驗(yàn),而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卻一步到位了。中央司改的很多司法改革措施都要在這里面實(shí)行的,主審法官員額制、辦案責(zé)任制,包括人員的分管理,法官的制度保障,還有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都要在這里進(jìn)行的。所以,它運(yùn)轉(zhuǎn)如何,對(duì)整個(gè)中國司法體制未來的走向可以說是有重大影響的。”王闖在新聞發(fā)布會(huì)上說。
對(duì)于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的設(shè)立,鄧宏光認(rèn)為,有必要在高院層級(jí)設(shè)立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如果能在北京設(shè)立高院層級(jí)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更能夠表明政府對(duì)于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的重視。此外,還可以對(duì)可能對(duì)于社會(huì)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案件進(jìn)行宏觀把握,還能在國際貿(mào)易中最大限度地保護(hù)國家利益。”鄧宏光說。
劉曉海則認(rèn)為,作為司法體制改革中的突破口,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當(dāng)前還面臨“循環(huán)訴訟”這一難題。
劉曉海向記者介紹,所謂循環(huán)訴訟是指,如果專利訴訟委員會(huì)對(duì)專利作出有效或者無效的意見,當(dāng)事人不服到中級(jí)法院提起訴訟,不服判決后再上訴到高院,高院如果和專利訴訟委員會(huì)意見不一致,會(huì)發(fā)回重審。如果發(fā)回重審后,專利訴訟委員會(huì)仍然保持原有意見,這樣的訴訟就還要再走一圈。
“循環(huán)訴訟使審判效率低下,審判周期過長,民事權(quán)利歸屬委決不下。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對(du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提出了考驗(yàn)。”劉曉海說。
客觀上說,與其他案件相比,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案件在審理程序、證據(jù)規(guī)則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專門化的程序和審理規(guī)則。例如,在司法實(shí)踐中存在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民事、行政訴訟程序交叉問題。在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民事侵權(quán)案件審理過程中,當(dāng)事人經(jīng)常對(duì)特定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有效性提出質(zhì)疑,并啟動(dòng)行政無效程序請(qǐng)求宣告該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無效,從而形成民事侵權(quán)程序與行政無效程序的交叉。
宋曉明表示,中國現(xiàn)行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實(shí)行民事侵權(quán)和行政無效二元分立體制,審理民事案件的法院通常不能直接審查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效力。為保證民事侵權(quán)案件審理結(jié)果的公正性,審理民事侵權(quán)案件的法院經(jīng)常不得不中止審理,等待行政無效程序的結(jié)果,因而影響了民事侵權(quán)案件的審理效率。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建立后,在這方面是否可以先行探索,為未來的制度設(shè)計(jì)提供經(jīng)驗(yàn)支撐。
盡管有了統(tǒng)一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但不同地區(qū)法院其審判的一致性問題,依然令人擔(dān)憂。目前,不服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第一審專利等技術(shù)類案件判決和裁定而提起的上訴案件,分別由北京、上海、廣東高級(jí)人民法院審理。在這一體制下,三地高院的技術(shù)類案件的裁判標(biāo)準(zhǔn)可能存在不一致性。未來如何防止出現(xiàn)裁判標(biāo)準(zhǔn)不一致的問題,是否需要設(shè)置相當(dāng)于高級(jí)人民法院層級(jí)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統(tǒng)一受理技術(shù)類上訴案件,仍值得進(jìn)一步觀察和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