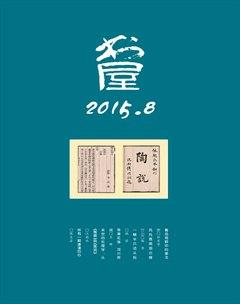懷有一顆謙謹(jǐn)?shù)男?/h1>
2015-01-17 02:15:47陳文芬
書屋 2015年8期 關(guān)鍵詞:研究
陳文芬
2012年10月,瑞典學(xué)院宣布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
我問悅?cè)唬骸澳缘锚勀愀吲d嗎?”
悅?cè)徽f:“高興。”
我又問:“為什么高興?”
悅?cè)幌騺碇环g他自己欣賞的作家,如李銳、曹乃謙、高行健、北島、楊牧等。悅?cè)徊皇悄缘淖g者,他只是接受瑞典學(xué)院諾獎提名小組委員會的委托翻譯莫言的作品。悅?cè)豢疾炝烁鞣N語言的莫言譯本,發(fā)現(xiàn)其中很少有短篇作品。他明確指出,莫言的作品短篇勝過長篇,《小說九段》中的風(fēng)景描寫有著沈從文一般簡潔風(fēng)景畫的力道,作者描述的外在環(huán)境與內(nèi)心樸質(zhì)性情的互相交映,尤其使人感動。“他是雙腳站在土地上的農(nóng)民的孩子。”他回答記者的話第二天刊載于《瑞典日報》頭條。
回答“為什么高興莫言得獎”,悅?cè)徽f:“我高興一個鄉(xiāng)巴佬得獎,尤其是一個中國的鄉(xiāng)巴佬得獎,沈從文、曹乃謙、莫言都是鄉(xiāng)巴佬作家。我終于等到了這一天。”
1948年,馬悅?cè)坏街袊{(diào)查方言,在四川生活了兩年,結(jié)識了許多文人學(xué)者并成為一生的好友。初到中國時他給自己取了中文名字“馬可漢”,那個“漢”字有追隨老師高本漢的意思,日后他說到這個名字笑著搖頭:“這名字簡直不行!”當(dāng)時四川華西大學(xué)中文系主任、一位優(yōu)雅的學(xué)者聞宥教授為他取名“馬悅?cè)弧保娜鸬湔Z名字就是“悅?cè)弧保℅?觟ran),相當(dāng)于英語的“喬治”,這美麗的中文名字伴隨了他的一生。
馬悅?cè)?946年開始追隨瑞典漢學(xué)家高本漢學(xué)習(xí)漢語,一生致力于漢語的研究與翻譯,而他的中文寫作卻推遲得很晚,這是所有漢學(xué)家的處境。2000年,以中文寫作的法國籍作家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之后,臺灣報刊邀請馬悅?cè)蛔珜懮⑽膶谝荒辏蠹Y(jié)成書即《另一種鄉(xiāng)愁》,我當(dāng)時負(fù)責(zé)編輯聯(lián)合文學(xué)出版的繁體字版,李銳將書稿交給北京三聯(lián)書店出版簡體字版,還作了序。
我的朋友、研究中國左翼文學(xué)作品的臺灣學(xué)者施淑女贊嘆馬悅?cè)灰怀鍪謱懮⑽模蛯懗隽松鲜兰o(jì)三十年代的民國優(yōu)雅白話文體。過了十幾年再讀《另一種鄉(xiāng)愁》,我更加喜愛。這本書尤為珍貴的意義是悅?cè)辉趯懽鬟^程中沉浸于對寧祖的畢生愛戀與懷念之中。2005年,悅?cè)粠е隙鍫枴合笨张c孫兒女一大家人回到成都祭拜寧祖的父母。兒媳與孫兒們都是老外,卻如中國人一般磕頭跪拜;一家人又陪悅?cè)恢氐嵌朊忌剑哌M(jìn)報國寺。2007年秋天,四川畫家老友吳一峰百年冥誕畫展,我隨悅?cè)换爻啥迹踩グ菰L報國寺,寺廟大致維持了當(dāng)年居住的模樣。峨眉山風(fēng)景如畫,游人如織,鄉(xiāng)愁就像還愿一樣還完了。
馬悅?cè)坏闹形膶懽鱽淼秒m遲,他的創(chuàng)作力量卻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全方位地爆發(fā)出來,明亮而有節(jié)奏。首先寫作散文集《另一種鄉(xiāng)愁》,接著創(chuàng)作俳句集《俳句一百首》,后又寫了微型小說集《我的金魚會唱莫扎特》,一部接著一部,最后還翻譯了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的《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詩作與散文的中文譯本)。瑞典學(xué)院前任常務(wù)秘書霍爾斯·恩達(dá)爾是個優(yōu)秀的散文作家,他也發(fā)現(xiàn)馬悅?cè)挥兄\用漢語創(chuàng)作各種文類作品的才華。我認(rèn)為,馬悅?cè)挥巫哂诟鞣N文類寫作都有著閃閃生輝的魅力,他是他自己的吹笛人,能召喚出往昔無限美好的記憶,傳達(dá)出他的語言學(xué)涵養(yǎng)與經(jīng)年累月研究漢語文學(xué)的哲思。
《另一種鄉(xiāng)愁》呈現(xiàn)了一位漢學(xué)家研究中國音韻學(xué)、古文與現(xiàn)代中文作品的許多心得,馬悅?cè)挥煤啒愕奈淖置枋鰧W(xué)術(shù)上深刻的道理,就像一幅一幅地拓印漢代畫像磚,當(dāng)讀者看過之后,連綴起來,就能了解當(dāng)時的文化生活,也理解了為什么漢學(xué)家需要研究中國音韻學(xué)。在《關(guān)于勞動號子的節(jié)奏》一文中,馬悅?cè)挥迷娙瞬苄林墓P名“杭約赫”三個字來記錄他在四川聽到的拉板車的人哼唱勞動號子的節(jié)奏。幾年之后,他發(fā)現(xiàn)兩千多年前荀子《成相篇》的節(jié)奏跟勞動號子的節(jié)奏完全相同。又過了一些年,他發(fā)現(xiàn)一個不識字但很有天賦的陜西詩人王老九吟唱的敘事長詩也有相同的節(jié)奏,甚至一些彈詞與“數(shù)來寶”也用這個節(jié)奏。馬悅?cè)粚懙溃骸笆澜缟辖^沒有一種語言的生命力能夠跟漢語相比。”
本書的一些文章將來會成為研究中國文學(xué)史未完的線索。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有著不同的方法,最常見的是以一個學(xué)者的力量寫一本當(dāng)代中國文學(xué)史,這個方法比較容易,因為一個學(xué)者只有一個觀點。1980—1982年、1986—1988年馬悅?cè)粌啥犬?dāng)選歐洲漢學(xué)協(xié)會主席。一次在德國召開的漢學(xué)會議,大家認(rèn)為1949年以前的中國處于動蕩不安的時代,西方的漢學(xué)家有責(zé)任記錄二十世紀(jì)上半葉的中國文學(xué)史,這個文學(xué)史最大的意義是使許多被歷史遺忘的中國作家通過這部文學(xué)史的出版而“復(fù)活”。
通過漢學(xué)家們的投票,由馬悅?cè)粨?dān)任總編輯的《中國文學(xué)指南1900~1949》(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分為短篇小說、長篇小說、詩歌、戲劇四卷,邀集一百名漢學(xué)家撰寫導(dǎo)讀書評,為作者立傳,闡述作品精華。在這個過程中,總編輯必須跟撰寫書評及擔(dān)任各卷主編的漢學(xué)家們不斷通信、討論、辯論甚至爭執(zhí)才能得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文學(xué)史觀點。真不容易!
1958年到1979年,馬悅?cè)粵]有機(jī)會拜訪中國。1979年4月,中國發(fā)給悅?cè)弧幾嫒刖匙C,往后兩三年悅?cè)换乇本┞?lián)系了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的朋友,找到了他需要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所寫著作的第一版,記得曾在七月的大熱天揮汗如雨,在瑞典大使館一頁一頁影印了所有的小說詩集讀本。后來,這批影印本送進(jìn)了瑞典遠(yuǎn)東圖書館,作為他自己研究,以后也成為編選文學(xué)指南的參考依據(jù)。
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初悅?cè)槐樵L中國的學(xué)者作家,搜集研究文學(xué)史料的意見。悅?cè)坏暮糜疡T至先生提到了一位被遺忘的詩人韋叢蕪所寫的長詩《君山》,共一百四十頁的《君山》可能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里最長的情詩。韋叢蕪生于1905年,寫作《君山》時才十九歲,一生只出版了兩本詩集。悅?cè)粴J佩馮至先生的文學(xué)觀點與研究態(tài)度,他不以功成名就的著名學(xué)者的姿態(tài)對被遺忘的詩人施以偏見,能夠秉持謙謹(jǐn)?shù)墓目创煌髡叩淖髌贰?980年,馬悅?cè)煌扑]馮至先生選進(jìn)瑞典皇家人文歷史考古學(xué)院成為外國院士,而收入了《君山》一詩的《中國文學(xué)指南1900~1949》至今仍擺放在瑞典學(xué)院諾貝爾文學(xué)圖書館閱覽室的書架上。
馬悅?cè)粠状翁岬健氨贿z忘的詩人”是研究文學(xué)史的非常嚴(yán)肅的命題。讀者也許奇怪為什么他常能發(fā)掘別人所不知道的詩人如楊吉甫、王老九,以及小說家如曹乃謙。悅?cè)徽f:“那是我偶然發(fā)現(xiàn)的。”能使偶然變成必然,需要勤奮閱讀,需要手到腳到地做足功課,更需要一顆像馮至那樣的謙謹(jǐn)之心。
近年來學(xué)界興起一股風(fēng)潮,引用薩依德的“東方主義”來作為否定漢學(xué)家研究的一種依據(jù)。我認(rèn)為“東方主義”是好的學(xué)說,但利用此說法來否定漢學(xué)家的觀點,對真正優(yōu)秀的漢學(xué)家不會有什么影響;反過來說,要是因此加深了對漢學(xué)研究的誤解,造成損失,那是西方文明走下坡路的一種象征。書中有一篇《巨人都到哪里去了》,悅?cè)话l(fā)現(xiàn)在高本漢的時代,無論西方還是中國到處都有學(xué)術(shù)巨人,現(xiàn)在卻沒有了。我們可以想想這是為什么。
《另一種鄉(xiāng)愁》增訂版添加了馬悅?cè)坏娜伦鳌读种锌盏氐氖^》、《想念林語堂先生》、《真理是美麗的》,附錄三篇訪問文章為編輯所選。
([瑞典]馬悅?cè)唬骸读硪环N鄉(xiāng)愁》(增訂版),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猜你喜歡
FMS與YBT相關(guān)性的實證研究體育科技文獻(xiàn)通報(2022年3期)2022-05-23 13:46:54 2020年國內(nèi)翻譯研究述評天津外國語大學(xué)學(xué)報(2021年3期)2021-08-13 08:32:18 遼代千人邑研究述論遼金歷史與考古(2021年0期)2021-07-29 01:06:54 視錯覺在平面設(shè)計中的應(yīng)用與研究科技傳播(2019年22期)2020-01-14 03:06:54 關(guān)于遼朝“一國兩制”研究的回顧與思考遼金歷史與考古(2019年0期)2020-01-06 07:45:20 EMA伺服控制系統(tǒng)研究民用飛機(jī)設(shè)計與研究(2019年4期)2019-05-21 07:21:24 基于聲、光、磁、觸摸多功能控制的研究電子制作(2018年11期)2018-08-04 03:26:04 新版C-NCAP側(cè)面碰撞假人損傷研究汽車工程學(xué)報(2017年2期)2017-07-05 08:13:02 關(guān)于反傾銷會計研究的思考國際商務(wù)財會(2017年8期)2017-06-21 06:14:14 焊接膜層脫落的攻關(guān)研究電子制作(2017年23期)2017-02-02 07:17:19
陳文芬
2012年10月,瑞典學(xué)院宣布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
我問悅?cè)唬骸澳缘锚勀愀吲d嗎?”
悅?cè)徽f:“高興。”
我又問:“為什么高興?”
悅?cè)幌騺碇环g他自己欣賞的作家,如李銳、曹乃謙、高行健、北島、楊牧等。悅?cè)徊皇悄缘淖g者,他只是接受瑞典學(xué)院諾獎提名小組委員會的委托翻譯莫言的作品。悅?cè)豢疾炝烁鞣N語言的莫言譯本,發(fā)現(xiàn)其中很少有短篇作品。他明確指出,莫言的作品短篇勝過長篇,《小說九段》中的風(fēng)景描寫有著沈從文一般簡潔風(fēng)景畫的力道,作者描述的外在環(huán)境與內(nèi)心樸質(zhì)性情的互相交映,尤其使人感動。“他是雙腳站在土地上的農(nóng)民的孩子。”他回答記者的話第二天刊載于《瑞典日報》頭條。
回答“為什么高興莫言得獎”,悅?cè)徽f:“我高興一個鄉(xiāng)巴佬得獎,尤其是一個中國的鄉(xiāng)巴佬得獎,沈從文、曹乃謙、莫言都是鄉(xiāng)巴佬作家。我終于等到了這一天。”
1948年,馬悅?cè)坏街袊{(diào)查方言,在四川生活了兩年,結(jié)識了許多文人學(xué)者并成為一生的好友。初到中國時他給自己取了中文名字“馬可漢”,那個“漢”字有追隨老師高本漢的意思,日后他說到這個名字笑著搖頭:“這名字簡直不行!”當(dāng)時四川華西大學(xué)中文系主任、一位優(yōu)雅的學(xué)者聞宥教授為他取名“馬悅?cè)弧保娜鸬湔Z名字就是“悅?cè)弧保℅?觟ran),相當(dāng)于英語的“喬治”,這美麗的中文名字伴隨了他的一生。
馬悅?cè)?946年開始追隨瑞典漢學(xué)家高本漢學(xué)習(xí)漢語,一生致力于漢語的研究與翻譯,而他的中文寫作卻推遲得很晚,這是所有漢學(xué)家的處境。2000年,以中文寫作的法國籍作家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之后,臺灣報刊邀請馬悅?cè)蛔珜懮⑽膶谝荒辏蠹Y(jié)成書即《另一種鄉(xiāng)愁》,我當(dāng)時負(fù)責(zé)編輯聯(lián)合文學(xué)出版的繁體字版,李銳將書稿交給北京三聯(lián)書店出版簡體字版,還作了序。
我的朋友、研究中國左翼文學(xué)作品的臺灣學(xué)者施淑女贊嘆馬悅?cè)灰怀鍪謱懮⑽模蛯懗隽松鲜兰o(jì)三十年代的民國優(yōu)雅白話文體。過了十幾年再讀《另一種鄉(xiāng)愁》,我更加喜愛。這本書尤為珍貴的意義是悅?cè)辉趯懽鬟^程中沉浸于對寧祖的畢生愛戀與懷念之中。2005年,悅?cè)粠е隙鍫枴合笨张c孫兒女一大家人回到成都祭拜寧祖的父母。兒媳與孫兒們都是老外,卻如中國人一般磕頭跪拜;一家人又陪悅?cè)恢氐嵌朊忌剑哌M(jìn)報國寺。2007年秋天,四川畫家老友吳一峰百年冥誕畫展,我隨悅?cè)换爻啥迹踩グ菰L報國寺,寺廟大致維持了當(dāng)年居住的模樣。峨眉山風(fēng)景如畫,游人如織,鄉(xiāng)愁就像還愿一樣還完了。
馬悅?cè)坏闹形膶懽鱽淼秒m遲,他的創(chuàng)作力量卻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全方位地爆發(fā)出來,明亮而有節(jié)奏。首先寫作散文集《另一種鄉(xiāng)愁》,接著創(chuàng)作俳句集《俳句一百首》,后又寫了微型小說集《我的金魚會唱莫扎特》,一部接著一部,最后還翻譯了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的《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詩作與散文的中文譯本)。瑞典學(xué)院前任常務(wù)秘書霍爾斯·恩達(dá)爾是個優(yōu)秀的散文作家,他也發(fā)現(xiàn)馬悅?cè)挥兄\用漢語創(chuàng)作各種文類作品的才華。我認(rèn)為,馬悅?cè)挥巫哂诟鞣N文類寫作都有著閃閃生輝的魅力,他是他自己的吹笛人,能召喚出往昔無限美好的記憶,傳達(dá)出他的語言學(xué)涵養(yǎng)與經(jīng)年累月研究漢語文學(xué)的哲思。
《另一種鄉(xiāng)愁》呈現(xiàn)了一位漢學(xué)家研究中國音韻學(xué)、古文與現(xiàn)代中文作品的許多心得,馬悅?cè)挥煤啒愕奈淖置枋鰧W(xué)術(shù)上深刻的道理,就像一幅一幅地拓印漢代畫像磚,當(dāng)讀者看過之后,連綴起來,就能了解當(dāng)時的文化生活,也理解了為什么漢學(xué)家需要研究中國音韻學(xué)。在《關(guān)于勞動號子的節(jié)奏》一文中,馬悅?cè)挥迷娙瞬苄林墓P名“杭約赫”三個字來記錄他在四川聽到的拉板車的人哼唱勞動號子的節(jié)奏。幾年之后,他發(fā)現(xiàn)兩千多年前荀子《成相篇》的節(jié)奏跟勞動號子的節(jié)奏完全相同。又過了一些年,他發(fā)現(xiàn)一個不識字但很有天賦的陜西詩人王老九吟唱的敘事長詩也有相同的節(jié)奏,甚至一些彈詞與“數(shù)來寶”也用這個節(jié)奏。馬悅?cè)粚懙溃骸笆澜缟辖^沒有一種語言的生命力能夠跟漢語相比。”
本書的一些文章將來會成為研究中國文學(xué)史未完的線索。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有著不同的方法,最常見的是以一個學(xué)者的力量寫一本當(dāng)代中國文學(xué)史,這個方法比較容易,因為一個學(xué)者只有一個觀點。1980—1982年、1986—1988年馬悅?cè)粌啥犬?dāng)選歐洲漢學(xué)協(xié)會主席。一次在德國召開的漢學(xué)會議,大家認(rèn)為1949年以前的中國處于動蕩不安的時代,西方的漢學(xué)家有責(zé)任記錄二十世紀(jì)上半葉的中國文學(xué)史,這個文學(xué)史最大的意義是使許多被歷史遺忘的中國作家通過這部文學(xué)史的出版而“復(fù)活”。
通過漢學(xué)家們的投票,由馬悅?cè)粨?dān)任總編輯的《中國文學(xué)指南1900~1949》(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分為短篇小說、長篇小說、詩歌、戲劇四卷,邀集一百名漢學(xué)家撰寫導(dǎo)讀書評,為作者立傳,闡述作品精華。在這個過程中,總編輯必須跟撰寫書評及擔(dān)任各卷主編的漢學(xué)家們不斷通信、討論、辯論甚至爭執(zhí)才能得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文學(xué)史觀點。真不容易!
1958年到1979年,馬悅?cè)粵]有機(jī)會拜訪中國。1979年4月,中國發(fā)給悅?cè)弧幾嫒刖匙C,往后兩三年悅?cè)换乇本┞?lián)系了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的朋友,找到了他需要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所寫著作的第一版,記得曾在七月的大熱天揮汗如雨,在瑞典大使館一頁一頁影印了所有的小說詩集讀本。后來,這批影印本送進(jìn)了瑞典遠(yuǎn)東圖書館,作為他自己研究,以后也成為編選文學(xué)指南的參考依據(jù)。
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初悅?cè)槐樵L中國的學(xué)者作家,搜集研究文學(xué)史料的意見。悅?cè)坏暮糜疡T至先生提到了一位被遺忘的詩人韋叢蕪所寫的長詩《君山》,共一百四十頁的《君山》可能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里最長的情詩。韋叢蕪生于1905年,寫作《君山》時才十九歲,一生只出版了兩本詩集。悅?cè)粴J佩馮至先生的文學(xué)觀點與研究態(tài)度,他不以功成名就的著名學(xué)者的姿態(tài)對被遺忘的詩人施以偏見,能夠秉持謙謹(jǐn)?shù)墓目创煌髡叩淖髌贰?980年,馬悅?cè)煌扑]馮至先生選進(jìn)瑞典皇家人文歷史考古學(xué)院成為外國院士,而收入了《君山》一詩的《中國文學(xué)指南1900~1949》至今仍擺放在瑞典學(xué)院諾貝爾文學(xué)圖書館閱覽室的書架上。
馬悅?cè)粠状翁岬健氨贿z忘的詩人”是研究文學(xué)史的非常嚴(yán)肅的命題。讀者也許奇怪為什么他常能發(fā)掘別人所不知道的詩人如楊吉甫、王老九,以及小說家如曹乃謙。悅?cè)徽f:“那是我偶然發(fā)現(xiàn)的。”能使偶然變成必然,需要勤奮閱讀,需要手到腳到地做足功課,更需要一顆像馮至那樣的謙謹(jǐn)之心。
近年來學(xué)界興起一股風(fēng)潮,引用薩依德的“東方主義”來作為否定漢學(xué)家研究的一種依據(jù)。我認(rèn)為“東方主義”是好的學(xué)說,但利用此說法來否定漢學(xué)家的觀點,對真正優(yōu)秀的漢學(xué)家不會有什么影響;反過來說,要是因此加深了對漢學(xué)研究的誤解,造成損失,那是西方文明走下坡路的一種象征。書中有一篇《巨人都到哪里去了》,悅?cè)话l(fā)現(xiàn)在高本漢的時代,無論西方還是中國到處都有學(xué)術(shù)巨人,現(xiàn)在卻沒有了。我們可以想想這是為什么。
《另一種鄉(xiāng)愁》增訂版添加了馬悅?cè)坏娜伦鳌读种锌盏氐氖^》、《想念林語堂先生》、《真理是美麗的》,附錄三篇訪問文章為編輯所選。
([瑞典]馬悅?cè)唬骸读硪环N鄉(xiāng)愁》(增訂版),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