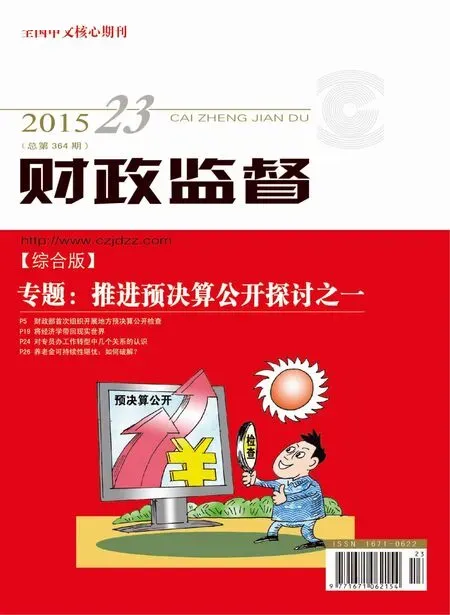將經濟學帶回現實世界
———記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
●本刊編輯部
將經濟學帶回現實世界
———記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
●本刊編輯部


每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都引人注目,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人們希望從諾獎得主的研究與觀點中找到自身發展的“良方”。今年諾獎得主也不例外,作為諾獎頒獎季的壓軸獎,獨享此殊榮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與國際事務教授安格斯·迪頓依舊全球矚目。自1969年以來,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47次,76人次獲獎,其中僅24次頒給一人,在全球經濟學理論與實踐都有較大發展的今天,單獨斬獲諾獎殊為不易。正如迪頓本人在接到自己得獎信息的電話中所說:“如果你到了我這個年紀,且已經工作很長時間,你知道這是一個可能性,但是有那么多人值得獲獎,自己中獎在我看來概率很低。”這位70歲的經濟學家因“對消費、貧窮和福祉的分析”而獨摘桂冠,可見其學術貢獻之分量。
安格斯·迪頓,微觀經濟學家,計量經濟學領域才華突出,與2011年諾獎得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并稱 “普林斯頓計量雙塔”,既是研究消費問題的大家,也以研究貧困和不平等問題著名。早年就職于英國劍橋大學、布里斯托大學,后于1983年來到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至今。輾轉于英美經濟學重鎮,迪頓是理論界堪稱“教科書級”的國際知名經濟學家,歷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世界銀行研究審核委員會主席、哈佛大學經濟系顧問團主席、美國經濟學會主席等,是1978年首屆經濟計量學會“弗里希獎”得主,也曾因在消費和儲蓄理論以及經濟福利度量等方面的貢獻,獲得了2011年BBVA基金會的“經濟、金融和管理知識先鋒”獎。著作等身,獲獎無數,然其“高大上”的榮譽皆來自于“接地氣”的研究,瑞典皇家科學院成員馬茨·佩爾森表示“迪頓在發展經濟學上的研究‘十分實用’”、《經濟學人》雜志評價迪頓所做的工作“重新將經濟學帶回現實世界”、更多的共識認為迪頓的研究與觀點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諾貝爾經濟學獎評獎委員會在聲明中如是寫道:“他的研究事關人類福祉的巨大重要性,尤其是在那些貧窮國家。迪頓的研究對實踐決策和科學界都有巨大影響。”本期大家走近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一窺其接地氣的經濟學研究。


英美教育的受益者
1945年出生于英國愛丁堡的迪頓,成長于二戰后的和平發展年代,盡管出身于并不富裕的工人家庭,但比起其父輩,則接受了系統良好的教育。迪頓的父親生于英國南約克郡一個以挖煤為業的小村子里,早年長期在礦井里從事最底層的工作,對他來講,當時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夠爬到地面上工作;他因二戰的打響而參軍遠征又因自己患肺結核而退役返鄉。此后,迪頓的父親賣力干活,抓住機會學習,終于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一名排水工程師,從經濟上讓全家脫離貧困,為子孫開啟了未來。迪頓的父親極為重視教育,曾為了讓迪頓能夠通過愛丁堡一所有名的私立學校的獎學金考試而說服老師為其“開小灶”,不負所望的迪頓最終拿到獎學金成為僅有的兩個可以免費入學的學生之一。此后迪頓又發憤考入劍橋大學數學專業,逐漸轉向經濟學,在劍橋攻讀下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終成為一名經濟學教授。

父輩的努力和良好的家庭教育為迪頓成為一代經濟大師奠定了初步基礎,而完善的教育體系和健康的學術氛圍則開啟了迪頓的學術生命。
數學專業出身的迪頓,對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課程有著天生的愛好,一路求學任教于英美經濟學重鎮讓其打下堅實的數理基礎。上世紀六十年代,劍橋經濟學系有瓊·羅賓遜、尼古拉斯·卡爾多、詹姆斯·米德等大家坐鎮,他們對世界面臨的貧困與發展問題的研究興趣感染著就讀于此的迪頓,加之劍橋重視分配問題的經濟學研究傳統,都潛移默化地讓迪頓在經濟學領域逐步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他曾深情談及對自己意義重大的師者: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這一生欠了不少‘學術債’,很多師長使我受益匪淺。其中,理查德·斯通對我的影響恐怕是最為深刻的。我從他那里學到了‘衡量標準’的重要——沒有衡量標準,我們就無法得出任何結論,而正確地建立衡量標準,亦是無比重要的事項。阿瑪蒂亞·森則教會我思考什么讓生命更有價值,以及應以整體的視角去思考人類的幸福,而不是僅僅考察其中的某些方面。”
理查德·斯通是國民經濟統計之父、劍橋期間迪頓的導師,阿瑪蒂亞·森也曾在劍橋待了一些年后至美國,他們的治學研究影響著迪頓的學術思想。現今擁有英美雙重國籍的迪頓,在英式教育環境中成長,又在美國教研體系中發展,深受兩國教育塑造。英式教育中對學生多方面涉獵的要求培養了迪頓廣闊的視野和豐富的知識結構,對文學歷史的看重、于廣泛議題中尋找終身興趣都讓迪頓獲益匪淺。從英國轉戰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這一經濟學重鎮、全球發展經濟學研究主要基地之一,也讓迪頓的研究推向縱深、逐漸扎根于美國的學術土壤。“在普林斯頓的經濟學圈內,沒有人比他更受尊敬”,密歇根大學教授沃爾夫斯如是評價。


接地氣的經濟學家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名單一經公布,就有網友調侃稱迪頓因研究“買買買”而獲獎。雖為戲言,但細窺評委會給出的三方面獲獎理由,其中前兩方面都是關于消費問題研究,第三方面關于發展經濟學,可見其對消費問題研究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所謂 “買買買”,無非是個人的消費選擇。諾獎聲明中指出“為了設計能夠增進福利、減少貧困的政策,我們必須首先理解個人的消費選擇。迪頓的研究強化了這一認識,他對此所做的改進無人能及。”早期迪頓即主要關注消費者行為,分析家庭和個人的需求、消費及儲蓄等,他的博士論文即題為《消費者需求模型及其在英國的應用》。1980年,迪頓與約翰·米爾鮑爾合著的《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出版,該書對消費者行為研究范式和相關理論結果進行了全面總結,闡明了消費者理論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該書一經出版即成經典,至今重印20多次,是經濟學系研究生做消費理論研究的必備讀物。此后,他與米爾鮑爾構建了一個“幾近理想狀態的需求分析系統”,成為微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工具,它不僅克服了傳統需求分析系統的局限性,模型本身的靈活性和可擴展性對消費行為研究提供了推動力,至今仍被廣泛應用、“持續作為經濟政策效果評估、價格指數建構和跨國、跨期生活水平比較時的圭臬”。
“今年的諾獎是關于消費——無論是宏觀層面還是個體層面的。”評委會這樣概括迪頓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看似日常的消費問題得到這一評價,并不失其分量。實際上,估計人們對商品的需求模式和需求曲線是經濟學的中心議題,只有了解人們對不同產品的需求、對人們的消費行為有所判斷,才能進行政策評價;反之,政策評價也要經得起微觀經濟實證層面的檢驗。

1990年前后,迪頓獨立完成了對消費和收入之間聯系的研究,與前一項成果是微觀經濟學里的重要工具不同,這一成就直指宏觀經濟學領域的重要問題。此間的迪頓發表多篇論文指出當時以宏觀收入和宏觀消費為起點的主流消費理論無法解釋收入與消費的實際關系、存在“迪頓悖論”,應該注意到微觀收入與宏觀收入變化的不同,并從個體收入和消費的研究著手來研究宏觀的消費行為。這一研究改變了自凱恩斯以來基于總量數據的宏觀經濟學研究,加總個體行為獲得整個經濟體的數據已經成為當代宏觀經濟學慣用方法,這其中迪頓的研究功不可沒。
隨著對消費問題的深入研究,迪頓的視野更加深邃廣闊,他開始轉向發展經濟學,開啟了對貧困、發展、福祉和不平等的研究,并將計量經濟研究模式應用其中,開創了發展經濟學領域的實證研究。在迪頓看來,經濟發展背后的規律應重視從個體家庭消費水平的可靠統計中得來,研究聚焦于家庭調查,推動了發展經濟學這一基于整體數據建構的理論領域向基于個體數據研究的實用領域轉變。而今的發展經濟學實證研究早已告別基于國民賬戶總量數據的分析,其基礎是描述每一個國家內數以千計單個家庭的詳細數據。毫無疑問,迪頓是這一偉大轉型的主要推動者之一。

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孫立堅認為,迪頓清楚地了解現在的問題和現實的密切結合,擺脫了整個美國學術界就經濟發展研究越來越數學化的方向。他的研究讓人們再次看到了經濟學是對現實有幫助的。他關注消費、測度貧困,據悉,印度政府已透過迪頓的研究改變對貧困的衡量方法,影響了政府的減貧政策。他還研究不平等、幸福感等問題,用經濟學實證證明了賺大錢真的未必讓人比較快樂;2013年出版的暢銷書 《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及不平等的起源》更是體現了他從多維度刻畫人們福祉的主張。他始終強調家庭調查是研究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的關鍵數據源,其著作《家庭調查分析:發展政策的微觀計量方法》更是高校經濟系學生人手一本的典范之作。
不難看出,從研究領域到治學方法,這位獲得無數“高大上”榮譽的經濟學家終生致力解決的皆為“接地氣”的現實社會問題,被同仁視作年輕經濟學家的完美榜樣。
用數據連接理論和現實
與一般微觀經濟學家不同,迪頓更愿意將自己稱為應用經濟學家,將一生奉獻給理解與改善處于貧窮中人們的命運是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孜孜不倦在做的事情;而為達成這一志向與愿望的根源則來自于自身對現實的關心、個體的重視以及對數據的認知與熱愛。不論是從幾十年前就開始參與始于上世紀70年代的國際比較項目(ICP)到與世界銀行保持長達數十年的合作,還是近年來出任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的高級科學家,迪頓一以貫之,通過合適的統計方法連接微觀和宏觀數據,打通理論與現實。他的實證結論和在經濟發展、不平等、貧困等問題上的政策主張,全都是建立在對扎實的微觀數據的計量分析基礎之上。

迪頓獲獎后,媒體曾轉載過他在自傳中講過的這樣一段經歷:
“在布里斯托,我被告知應該去找一個研究助理,這聽起來很合理,但是我從來沒有真正搞明白如何使用一位研究助理。對我來說,收集數據、編程、計算,每個步驟都是整個創意過程的有機組成部分。缺其一,我腦子里就不太可能冒出火花,告訴我哪里不對。”
在迪頓眼中,來源于家庭調查的微觀數據以及這些數據的有機組合是學術靈感的源頭。他熱愛數據,能夠嫻熟地運用數據,以精確之至的標準要求其他學者,是一名微觀數據的“挖掘者”,但他并不被數據機械地束縛,堅定地反對單純運用“隨機對照試驗”等計量手段、不顧理論基礎與現實情況的研究方法和政策抉擇,他以自己的研究證明“智慧地運用調查數據才能夠幫助我們解決攸關人類福祉的重大問題”。

1980年代中期,世界銀行開啟了一項大規模家庭調查項目,其關鍵在于數據的可得性。迪頓在此期間提出用多期跨部門數據來構建了“擬面板數據”,并證明其結果的準確性且收集成本更低,被世行等機構和研究者廣泛采用。

幾十年來,迪頓對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尤其對印度上世紀90年代的貧困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著力于貧困度量的問題。在其擔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后也曾多次呼吁應更多借助百姓自報的福祉數據來測度貧困。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一直預測迪頓能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因為其對迪頓的工作熟悉而欽佩——“他對貧苦測量有非常重要的貢獻,他的研究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家庭微觀數據采集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動作用。”孫立堅教授更是明確指出,迪頓將難以挖掘出的數據通過他的方法找到精準信息,捕捉到問題本質,得到諾獎評委會對其方法論的高度評價,“他的獲獎不僅因為他關注的問題最棘手,其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最前沿。”
新著《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及不平等的起源》跨越250年的經濟史研究,被“福布斯”評為年度最佳書籍之一、入選當年英國《金融時報》年度商業圖書榜單。其中文版譯者崔傳剛談及迪頓著作的啟發時說道:“除財富不平等外,也需要看到整體福利不平等可能導致的問題。在未來,中國也好,世界也好,解決不平等的問題不單單是財富問題,甚至不是財富問題,而是綜合的福利。”當迪頓主張從健康、自由、幸福感等多維度來刻畫人類的福祉、生命的價值問題時,探討不平等也就要關注這些指標、數據所傳遞的信息;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則為該領域的持續研究提供著更便利可靠的條件。

這位“接地氣”的經濟學家,游走于理論與現實之間,憑借的是對數據的熟稔、熱愛和智慧運用。“世界是充滿迷霧的,有時候要搞清楚一些事很困難”,迪頓在獲獎后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最好的瞬間在于,你借助數據點亮了之前一片黑暗之下的東西。”借由數據,迪頓撥開迷霧、照亮黑暗,將經濟學帶回現實世界。■
(本欄目責任編輯:阮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