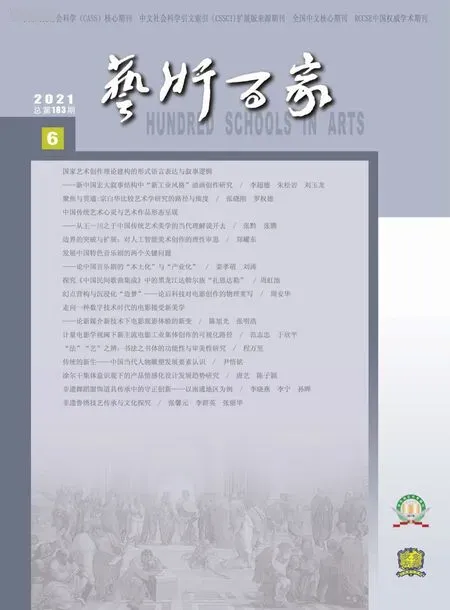習行踐履,格物致知
陳娟娟
中圖分類號:J80 文獻標識碼:A
王國維在《戲曲考原》中說:“戲曲者,謂以歌舞演故事也。”說到底,戲曲是一種舞臺表演藝術,只要表演存在,戲曲就不會滅亡,表演既是戲曲存活的生命體征又是其充滿活力之所在。昆劇作為“百戲之祖”,歷經六百多年的興衰浮沉,依靠上一代演員向下一代演員口傳心授的習藝方式,使傳統表演藝術的基本格局能夠流傳至今,并存活在舞臺上,成為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20世紀以來,隨著西方戲劇觀念的傳入和傳統戲劇學科的初步建立,關于昆劇表劇藝術的研究也開始受到重視,這一時期有關昆曲表演藝術研究的論著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昆劇老藝術家們演出的經驗總結,即以談藝錄的形式呈現;二是在戲曲這個大范疇里探尋各劇種表演藝術的共性規律;三是夾雜在昆劇史論劇說中的關于昆劇表演藝術的論述。但是,真正以昆劇表演藝術為獨立研究對象的著述基本沒有,更不要說上升到像斯氏、布氏那樣的表演藝術理論體系。直到顧篤璜先生的《昆劇表演藝術論》一書,用“非經院式”式的文字闡釋傳統昆劇表演藝術厚重的歷史積淀,既從實際出發,又力求引入理論思考,才可以算是真正意義上的關于昆劇表演藝術的系統性、科學性、邏輯性的理論總結與體系建構嘗試。縱觀此書,其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對昆劇表演藝術的本質特征及其表現手法的辯證性認知顧篤璜先生將中國戲曲的表演原則歸納為:一、集“唱、念、做、打”于一身的大一統、大綜合原則;二、非幻覺主義的、與觀眾直接交流互動的原則。正是這兩大藝術原則,奠定了我國戲曲特有的“寫意”的藝術特征。這并非昆劇所創始,卻因昆劇而得到了穩定鞏固與深化。昆劇靠什么來寫意?靠程式。程式貫穿昆劇表演的全過程,并體現在表演的一切環節中;不僅包括表演主體演員,也包括“非演員”子系統。顧先生在對昆劇表演藝術的本質特征及由其所決定的表現手法進行闡釋梳理時,辯證性的思維貫穿始終。首先從表演的主體演員來看,昆劇表演藝術的程式化使得腳色分類、演員分行,各行當家門有其特有的程式化的身段表現方式。身段藝術作為一種獨立的符號系統,即源自生活,又獨立于生活原形之上。生活中的動作經過提煉加工,舞式化的藝術夸張,形成演員與觀眾共同的約定俗成,并且達到系列化的高度,便成為了程式身段。每一個身段的含義是確定的,但同樣的身段程式,在不同人物內心狀態的推動下,經過微調或略有變異,其表達出來的含義,以及塑造出來的人物形象便有很大的不同。身段程式作為一種符號,其組合是千變萬化的,它要求大家共同遵守,卻又允許甚至提倡合規律的變化創造。阿甲說:“戲曲程式是創造戲曲形象表現力很強的一種特殊形式。它管束表演的隨意性并放縱它有規律的自由。”[1]各行當家門特有的程式化的身段為演員扮演劇中人物提供了一個基調,但又并不妨礙演員在此基調上更深化人物性格的藝術創造。“梅蘭芳先生從藝術程式中獲得了動作自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其次從“非演員”的表演子系統來看,昆劇雖然成熟于我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物質相對豐富、技術相對進步的歷史時期,但他仍堅守程式化的藝術自覺和美學追求不動搖。“承認舞臺布置的使用功能而免除其再現和描繪功能。排斥設置實景,以中性道具象征性的示意故事發生的地點和環境”[2](p.32),著力發展寫意虛擬的表演手法。所以,也可以說,昆劇舞臺的“布景在演員身上”。虛化了布景,中性化與簡化了道具之后,舞臺美術自然就集中在人物造型藝術,主要是化妝與服飾兩個方面。“它追求的同樣是與生活現實原狀拉開距離,不求寫實地‘再現生活,而走寫意的‘描繪之路。從而又發展出利用舞弄服飾穿戴的技藝,用以渲染人物思想感情的許多手法來。”[2](p.45)化妝、服裝穿戴的程式化定型化使舞弄化妝、服飾等各種穿戴物的技藝以加強表演的手法得以形成。反過來,利用穿戴物以加強表演的成功創造,又使穿戴物通用的原則得以進一步鞏固而不變。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昆劇是一種即貧困又不貧困的表演藝術。從表面上看,舞臺上除了演員的程式化表演幾乎沒有其他“附加物”,但所有的“非演員”子系統,包括文學、舞臺美術、音樂等,都完全圍繞、附麗于演員的表演而呈現在舞臺上,各種輔助手段盡量壓縮(極小化),才能使演員的藝術功能充分發揮(極大化),從而達到最佳的藝術效果,給觀眾綜合、統一的審美感受。
二、對昆劇表演主體養成的實踐性思考顧篤璜先生自幼浸潤于昆劇文化的氛圍之中,十分熟知昆劇;又攻讀過戲劇專業,接受過系統的中西方戲劇教育,具有深厚的理論基礎。他自1953年開始創辦劇團,并附設學館,著手培養昆劇人才,曾先后聘請過五位“傳”字輩藝人授戲,并從旁觀摩全過程。1982年倡議重建昆劇傳習所并主持其事,參與培養了“繼”、“承”、“弘”三輩昆劇演員,前后長達三十多年時間。顧先生經常親自指導演員排練,為演員講授表演藝術理論,幫助他們理解、消化、掌握昆劇的體驗藝術,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本書就是根據顧先生幾十年來的筆記和授課講義舊稿整理、擴充而成,既有一定的理論高度,又有實際的指導意義。從演員的選材到培養,顧先生總結了許多優良傳統與寶貴經驗,他強調學戲從臨摹入手,劇目注重師承。古人對表演藝術精益求精的反復加工,使每一個折子戲或劇中人的表演藝術均有比較獨立的審美價值。“我們今天所說的表演藝術遺產,便集中在這些優秀的折子戲,更是骨子戲之中。”[2](p.100)對于這份遺產繼承和改革的問題,顧先生主張:昆劇表演藝術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傳承是活態的、流變的,又應該是繼承的恒定性與創造的變異性辯證結合。也就是梅蘭芳先生所說的“移步而不換形”。顧先生敏銳地看出并十分鄭重地強調:昆劇表演藝術具有重“體驗”的優良傳統。演員學戲先從外部動作(身段)的臨摹入手,進而尋找內心依據,漸漸達到“心到”的境界,這樣表演才傳神,才有感人的力量。但又指出昆劇授戲的傳統方法尚有欠缺之處,在處理內心體驗時對激活演員相應的記憶表象這一點往往強調不夠。提出“演員如何才能從模仿外部動作——身段入手的學藝方法中,進入內心體驗”這一造就昆劇演員的重要命題。對此顧先生給出的答案是是:采用“拿來主義”,學西方。“西方的表演藝術理論包括其訓練方法是建立在生理學、心理學乃至解剖學、物理學的基礎上的。特別是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對推動表演藝術理論研究所起的作用尤為關鍵。”[2](p.86)他自覺而謹慎地將斯氏體系相關理論引人昆劇表演人才的培養中,并指出“我們借鑒斯氏體系主要在于演員進入體驗的方法,而不在其追求的幻覺主義目標。”[2](p.86)endprint
三、對昆劇表演藝術獨特風格的原真性審視
昆劇表演藝術以人為載體,離不開社會、文化環境,所以,它的原真性又隨著人的存歿和環境的變化而發生變遷。這種變遷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災難性的。以京劇為例,“京劇有百分之六十來自昆劇”(歐陽予倩)。但是,京劇經過發展所確立的自己的藝術樣態反過來又對昆劇起了“反哺”作用,這種“反哺既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作用”,昆劇的京劇化不可避免地使昆劇藝術風格減弱甚至趨向消失。所以,顧篤璜先生提出:現在學界面臨的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就是對于昆劇表演藝術究竟是怎樣的,或究竟應該是怎樣的,在觀念上很是模糊。很多人“沒有真正確立昆劇觀,有的卻是京劇觀。”[2](p.114)而要想對昆劇表演藝術遺產真正地進行保護,首先必須清楚地樹立起原真態的昆劇觀。顧先生是昆劇“保守派領軍人物”,自1951年起從事昆劇的遺產搶救保護工作,至今任然活躍在搶救保護的第一線。他始終堅守的原則是:“傳統、傳統、再傳統”。甬昆、永嘉昆、吳江昆曲傀儡、蘇州老“堂名”等遺產,都因他的努力而部分地得到保護和存錄。這些“邊緣”藝術由于處于“邊緣地位”,所以較少受到其他劇種的侵蝕和干擾,較多地留存著傳統昆劇藝術的本真形態,顧篤璜先生將自己在這方面的工作體會上升為理論思辨,闡發自己的“昆劇觀”。顧先生指出昆劇是由文人參與并主導推動而發展起來的戲曲形式,因此,和之前的戲曲形態相比,必然有所轉型與提升:從民間的戲曲轉型提升為文士的戲曲;從通俗型戲曲轉型提升為高雅型戲曲;從粗放型戲曲轉型提升為精致型戲曲;從野外型戲曲轉型提升為室內型戲曲。這在昆劇表演藝術中便集中體現為輕、精、細、慢的藝術特色。為了讓讀者能更直觀、形象的認識原真態昆劇表演藝術的風格特征,并針對學界長期以來京昆不分的問題,本書專列一個小節對昆劇、京劇表演藝術從總體基調、唱腔、身段、做工、樂器、鑼鼓經等方面進行了分析比較,非常精彩。顧篤璜先生形象的比喻昆劇像太極,京劇像少林拳。《昆劇表演藝術論》一書,是顧篤璜先生六十多年來在昆劇遺產搶救保護第一線工作的實踐經驗的總結,也是他理論聯系實際,對原真態的昆劇表演藝術進行研究的理論成果的集中呈現,全書充溢辯證性的理性反思,在研究方法上兼具系統性、科學性和邏輯性,對于昆劇表演藝術理論體系的建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但本書作為“昆曲學”子課題的研究成果,受限于課題的分工,主要是關于“做”、“打”部分的研究探討,未能實現對表演藝術四功的全面覆蓋,未免令人稍感遺憾。(責任編輯:帥慧芳)
參考文獻:
[1]阿甲.談談京戲藝術的基本特點及其相互關系——為了研究現代京戲的改革[J].文藝研究,1981,(06):23.
[2]顧篤璜.昆劇表演藝術論[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