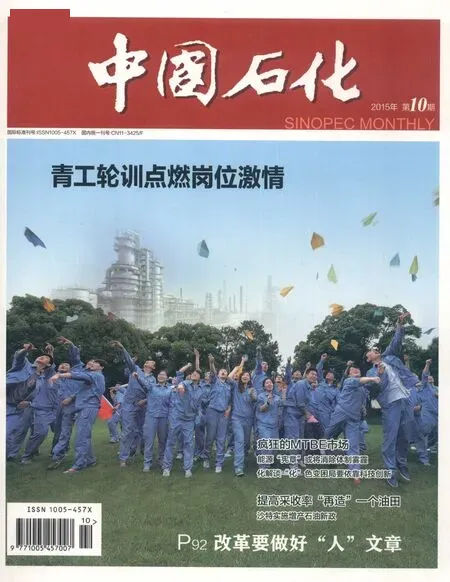破冰的期待
□ 李 珍
破冰的期待
□ 李 珍
《能源法》已經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機不可失、失難再得的時候。
媒體一條消息引人注目:國家發改委網站8月5日發布的信息顯示,起草多年的《能源法》已形成送審稿上報國務院,正在配合國務院法制辦做好立法審查工作。
醞釀已久的《能源法》,終于有了破冰跡象,這不能不引起全社會尤其是能源行業的關注與期待。
出臺是現實的需要
在人類歷史上,依法規范能源的系統認識始于近代。但能源立法在世界范圍進程的加快,卻是受“石油危機”的激發。
上世紀70年代爆發的“石油危機”,讓世界能源安全問題凸顯。發達國家為保障能源安全,加快了能源立法的進程。法國于1974年制定《省能法》,英國于1976年頒布《能源法》,美國于1978年頒布《國家能源政策法》,日本于1979年頒布《能源使用合理化法律》,德國也于1998年修訂《能源經濟法》。可以說,這個時期是世界能源法加快出臺的時期。這標志著用法律手段規范能源開發與利用活動,調整和解決能源問題,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與普遍做法。
中國的能源立法相對落后。這一方面是中國過去長期經濟落后,能源安全問題不太突出,能源立法所倚重的國家能源戰略與政策的研究也處于較低層次;另一方面是依法治國的思想觀念普遍淡薄,對制定能源法借以規范能源經濟關系的意義缺少認識。雖然,國家先后出臺并施行了《電力法》(1995年)、《煤炭法》(1996年)、《節約能源法》(1997年)、《可再生能源法》(2005年)等能源單行法律,構成了我國能源法律體系框架的雛形,但能源領域一直缺少一部綜合性、基礎性的法律。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世界格局的復雜多變,能源問題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生產國、第二大能源消費國,現有的政策和法律在應對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長和國內外能源形勢變化等方面已經顯得力所不及。
中國,急需出臺一部全面體現能源戰略和政策導向、總體調整能源關系和活動的能源基本法,同時不斷健全以《能源法》為核心的能源法律體系建設。《能源法》的立法,不僅是能源法律體系中基本法的制定,也是為修改和制定其他能源專門法和配套法規提供法律依據和價值取向,更有助于解決能源專門法與其他法律、能源專門法之間的銜接。能源法的制定由此提上日程。
可以說,《能源法》是國家有關能源領域的一部綜合性、基礎性法律,其調整對象應涉及中國能源各個領域普遍存在的共性問題、基本問題、重大問題、綜合性問題,這是任何一部能源領域的單行法都無法解決的。
有專家表示,世界各國能源立法的經驗與實踐表明,制定能源法有助于解決如下重大問題:一是明確國家能源發展的總體戰略,確立能源開發利用的戰略思想、方針、目標和措施。二是確立能源行業各單行法律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協調各單行能源立法。三是確立能源中長期規劃的法律地位,為實現能源發展目標提供法律保障。
也有專家認為,能源領域需要一部“小憲法”,從根本上說,是由我們國家能源領域的“三大需求”所決定的。
一是我國能源戰略安全的需要。目前,我國能源對外依存度日益提高,石油對外依存度57%,天然氣對外依存度31.6%,煤炭對外依存度10%,因而有必要用基本法律去處理能源安全與可持續性問題。
二是法律體系需要一個統領能源法律部門的基本法。在實踐中,由于缺少這樣一部統領性的基本法,以致現有的單行法律法規彼此間存在沖突與矛盾,有些制定于上世紀后期,也已不能滿足所在行業的需要。這就使得制定一部基本法,發揮統領作用,把涉及整個法律部門的基本原則、制度和內在邏輯關聯確立下來,成為當務之急。
三是能源對內與對外的合作需要基本法來規范。隨著能源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我國日益重視發揮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對保障能源供應的作用。然而,現行的對外能源合作立法制定較早,已經不適應實踐的需要,例如對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投資行為進行審查等問題就需要補充。開拓國際市場,如何爭取法律保障,也需要有上位法為依據。
可以說,是現實呼喚中國能源領域的基本大法盡早出臺。
出臺的契機來臨
早在2005年10月,媒體就披露,國務院時任總理溫家寶親自批示起草《能源法》,隨后,國家能源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成立,開始啟動能源法的起草工作。
2006年1月,《能源法》起草組成立。國家能源辦、國家發改委等15家單位為起草組成員單位,參與起草工作。
經近兩年努力,《能源法》多個討論稿形成,幾經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見稿。2006年12月,《能源法》修訂完畢,發往各相關單位征求意見,并向社會全文公布征求意見。
那時,全國上下都以為,“征求意見稿”匯總各方面的意見后,報國務院法制辦,交由全國人大環資委或財經委審定,再報全國人大法工委通過,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等程序,最早2007年底或2008年就可以正式出臺。
卻不料,這一等,就是8年。這一等8年,或許印證了一個至理:立法不是一件隨心所欲的事情。在某些情況下,等待是無奈的,卻也是不得已之下的次優選擇。
問題是,現在《能源法》何以又要加快出臺?
有專家分析認為,是經濟新常態倒逼轉型,形成《能源法》出臺的新契機。其一,近年我國能源工業快速發展,能源需求旺盛,供應能力明顯提高,產業體系進一步完善,為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能源生產大國和第二能源消費大國。近十年來,清潔能源發電裝機大幅增加,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跨越,2014年,非化石能源裝機約占總裝機的32.65%。
其二,“新常態”悄然成為宏觀經濟的新背景。對能源行業而言,需求增長將明顯放緩,生態環境約束將進一步增強,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持續推進將會是我國能源發展的“新常態”。適應“新常態”的發展要求,能源行業必須進行深層次結構調整,實現能源工業從體量的飛速發展到質量的有效提升,完成量變到質變的華麗轉身。《能源法》必須進行解答。
其三,《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對于能源行業來說,這意味著能源將回歸其商品屬性,由資源的稀缺性和供求關系來決定價格。對于政府部門來說,這意味著要重新審視自身的職能定位,減少對能源領域的干預,進一步簡政放權,大幅度減少能源審批事項,從過去的以批代管,向事中、事后監管轉變。這就要求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確,在能源市場化上給出答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對能源立法工作無疑也是一大利好。
也正是因為契機來臨,習近平在2014年6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研究中國能源安全戰略時,明確要求加強能源法律法規的“立改廢”工作和能源法治體系建設;11月國務院發布《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也提出要健全能源法律法規。《能源法》已經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機不可失,失難再得”的時候了。
非萬能但引人期待
“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能源法》的出臺是解決能源領域問題的必要,依法治國的必然。通過《能源法》的制定與實施,構建能源安全立法保障制度,有助于明確國家能源發展的總體戰略,有助于確立能源產業發展的方針、目標和措施,有助于明確能源市場的準入、價格、儲備、投資等基本行為規范,構筑穩定、經濟、清潔、安全的能源供給體系,以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支持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已得到全社會的認同。這是《能源法》出臺并得到實施的有利條件。
然而,誠如有能源專家指出的那樣,中國是能源生產大國,也是能源消費大國,能源領域的問題極為復雜,其中體制問題尤其是中國能源不安全的一大隱患,光靠一個《能源法》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
而且,中國能源立法雖已初具規模,卻并不完善,比如石油、天然氣、原子能領域至今沒有單項立法。這決定了我們國家的《能源法》不能采取美國的“法典化立法”模式。但日本式的“政策性立法”模式,因缺乏操作性,難以解決實際問題,也不宜采用。剩下的 “通則式立法”模式,即韓國《能源基本法》、蒙古《能源法》、德國《能源產業法案》等能源立法所采用的模式,即在法案中規定,在能源事項上具有管轄權的各國家機關的權限、能源活動許可證、能源費率與價格、能源監管機構對能源部門的安全和技術監管、爭議的解決和處罰等一套基本規則,也未必適用于中國。
我們國家的特殊國情決定了能源立法只能采取綜合立法模式,即主要對涉及能源安全、能源效率、能源管理、能源環境保護等全局性問題加以規范,同時對能源其他各單行法加以補充,所發揮的作用是宏觀管理和對單行立法加以協調和拾遺補缺。這要求實現從政策性立法向應用性立法、從“軟性”倡導向“軟硬”結合、從現實應對向科學前瞻、從政府唱“獨角戲”向多主體合作、從分割立法向協調立法轉變。但這個轉變的難度很大。比如,要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就要在立法中明確規定一些量化指標,但量化指標放在法律中雖然具有約束作用,但如果這些指標不能按期完成,也會有損法律的權威性。
然而,凡事不是非得等到什么條件都成熟了才來行動,也不可能求畢其功于一役。我們對《能源法》破冰的期待,只能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堅持能源安全原則、能源可持續利用原則、節能與能源效率原則、能源與環保協調原則,承載經濟增長、社會公正與環境保護三種法律價值,通過其制定與實施,為修改和制定其他能源專門法和配套法規提供法律依據和價值取向,不斷完善能源法規體系,達到保障能源供給、促進能源開發、優化能源結構、維護能源安全、規范能源清潔利用、加強能源合作的目的,在我們國家建立起一個健康有序發展的行業生態。
第一,期望這部法律能夠立足于市場經濟進行制度設計與安排,正確反映權力和利益訴求,進行有效的制度設計,既起到統領作用,不代替各能源單行法,又解決好能源法律與能源政策的協調配合,促成一個主管、協管、監管加行業協會自律和社會公眾參與的綜合能源管理體制。
第二,期望這部法律能夠從國情與世界能源的現實出發,既鼓勵促進可再生能源形成新的可替代能源,同時也堅持把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清潔、高效和綜合利用放在突出的位置,構筑穩定、經濟、清潔、安全的能源供給體系,支持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期望這部法律能夠以能源效率為出發點,以能源安全與能源效率為目標值,用產權效率與政府公平來推動能源產業的集約發展和清潔發展,促進建立統一、有序、和諧的國內外能源市場,避免私采濫挖造成的開采失控、效率低下、能源浪費,推動全社會能源節約。
(作者單位:重慶能源集團物資公司)
鏈接
《能源法》 立法進程
2005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副總理曾培炎批示,啟動《能源法》立法。
2006年初,《能源法》起草工作啟動。
2007年,舉辦中國能源法國際研討會,形成《能源法》(送審稿)。
2008年12月,《能源法》(送審稿)上報國務院。
2009年,成立《能源法》審查修改工作小組,形成《能源法》(修改稿)。
2010年,召開多次專題論證會、修改工作會,參加中美能源立法透明度對話。
2013年,《能源法》被列入國務院立法計劃。
2014年6月,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研究中國能源安全戰略時,明確要求加強能源法律法規的“立改廢”工作和能源法治體系建設;11月國務院發布《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指出,要健全能源法律法規。
2015年8月,《能源法》形成送審稿上報國務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