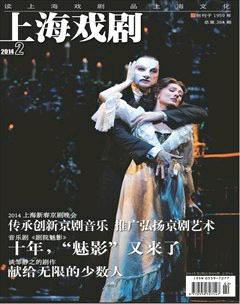淺談音樂劇《劇院魅影》的改編
老飛

《劇院魅影》改編自20世紀初,由法國報人兼作家卡斯頓·勒胡發表的同名小說。但有一點也是肯定的:舞臺上的故事,和書本里差異較大。
音樂劇版的主要人物基本上是沿用了原著的安排,沒有很大改動,除了兩個角色:書中本來沒有的男高音皮昂吉,以及在書中本來是個性格古怪且惹人嫌的領位員的吉瑞夫人——在音樂劇版里則是高貴嚴厲的芭蕾教練。吉瑞夫人熟知主人公魅影的秘密,這點保持不變。故事主線也依然是拉烏爾子爵、克麗絲汀和魅影三人之間的感情沖突。
小說原著是按照偵探小說的格局,即“事件一線索一疑團一解密一揭曉”的順序來來布置的。卡斯頓本人就是一個偵探小說家,據說在法國偵探小說界的地位與英國的柯南道爾齊名。書中諸多細節描寫細致入微,比如卡洛塔的行蹤、克麗絲汀和拉烏爾兩人的童年邂逅和情愫漸生、巴黎警方對歌劇院連續發生惡性案件的調查、拉烏爾的伯爵兄長、魅影的身世以及那個神秘的波斯人等。而回過頭來看音樂劇的故事,似乎顯得“粗線條”了不少:雖然故事主線依然是三個主角之間的感情沖突,但是許多細枝末節都被砍掉或者改掉了。
例如原著中很重要的神秘波斯人,在音樂劇中被刪除了。因此本來通過他的角度敘述的發生在地下迷宮里的魅影、克麗絲汀和拉烏爾三人之間的最后對峙情節,舞臺上也變成直接呈現;而由他引出的魅影離奇曲折的身世,在舞臺上,就變成由已經“轉型”為芭蕾舞教練的吉瑞夫人,向拉烏爾子爵在盛大的舞會后的短短幾句交談帶出而己,并沒有多費筆墨,甚至都沒有說清楚具體的內容。同樣消失的主要人物還有拉烏爾的伯爵兄長。
音樂劇中的《小小洛蒂》(LittleLotte)這首歌,是舞臺上拉烏爾子爵認出克麗絲汀后,趕到化妝間里,喚起克麗絲汀對童年往事回憶的所演唱的。可如果沒有讀過原著,對歌詞中提到的“紅絲巾”(redscarf)、“北方的黑暗傳說”(darkstories of the north)等內容就會一臉茫然。實際上原著花了相當大的篇幅來介紹拉烏爾子爵少年時和克麗絲汀的偶遇相識,并曾為她跳入波濤洶涌的大海,撈回被海風吹走的紅絲巾的經歷。這些都是兩人日后重逢會很快陷入愛河的鋪墊。
那么是不是可以說這樣的戲是有缺陷的呢?當然不。這是由小說和戲劇的不同特性引起的。戲劇的長度和表現方式決定了它在改編這類長篇小說時必須要抓大放小,突出矛盾。在有限的時間里,把故事主線說清楚講透徹,把主要的戲劇沖突矛盾詳細地展示給觀眾,讓觀眾深刻感受。其他的細節,則要么通過敘事過程做個簡單的介紹回顧,要么干脆就舍棄,讓有興趣的觀眾自己從現有情節里去推導出來。
比如說同為經典音樂劇的《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雨果的原著中開篇就花了整整一卷四萬多字的篇幅,講了卞福汝主教(MgrBienvenu)的故事。而盡管這個角色對主人公冉阿讓(Jean valjean)的心靈救贖是如此重要,在音樂劇里,則是以兩首歌總共不及8分鐘的時間,簡單勾勒一下就結束了,可也已經足夠讓觀眾了解到這個角色的特性以及其對劇情發展的影響了。所以《劇院魅影》的做法也是遵循了這個規律對原有情節人物進行取舍。
那取舍的標準是怎么定的呢?這里就要講到韋伯創作該劇的初衷了。原著雖然當年在法國銷量不佳,但是因為其詭異的人物和場景設定,常被后人拿來改編,尤其是電影,拍攝了不下四五部,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1925年朗·夏尼(LonChaney)主演的同名默片;中國觀眾熟悉的《夜半歌聲》,也是受這部電影的啟發而創作拍攝的。
在舞臺領域,英國劇作家肯·希爾(Ken Hill)在1976年即根據這本小說,改編創作過一部同樣名為《劇院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的音樂劇,大獲好評。1984年,韋伯在觀看了希爾的這部作品后,受到啟發,也開始創作他自己的版本,不過和希爾的版本不同在于:希爾的作品依然保持了原著的驚悚風格,著重描述魅影的神秘殘忍。韋伯則打算另辟蹊徑。
韋伯與曾和他一起制作《貓》(Cats)的制作人卡梅隆·麥金托什(Cameron Mackintosh)討論后決定,新的作品應該是以講述浪漫愛情為主的故事,驚悚懸念起到點綴作用即可。于是,故事主線就此集中在了魅影、克麗絲汀和拉烏爾這個“情感三人組”身上,而和“三人組”故事無關痛癢的人物劇情,就可以被“省略”或者“改造”了。這就是為什么拉烏爾的伯爵哥哥和波斯人都不見了,而吉瑞夫人“升職”的原因。
可是名字既然叫做《劇院魅影》,而且主角還是一個戴著面具在歌劇院里制造神秘事件的“怪人”,如果徹底改成浪漫歡樂的風格必然不妥。那怎么在舞臺上平衡呢?韋伯的團隊很巧妙地利用了以下幾個手法:
創作團隊采用了倒敘手法,在全劇的開頭加上一場光線幽暗的拍賣會作為序幕。通過一件件拍賣品的展示,配以神秘幽深的背景音樂,稍稍營造了些驚悚懸疑氛圍;然后又通過暮年子爵的演唱和拍賣師的念白,讓觀眾了解到克麗絲汀和歌劇院發生過的“神秘事件”,揭示了之后會出現的愛情線索;然后緊接著,通過大吊燈在耀眼光芒中神奇地從臺上升起,巧妙地將觀眾從幽暗神秘的氣氛中,帶回到了歌劇院當年輝煌明亮,光鮮奪目的舞臺上。
在三位主角的出場次序上,也有安排:最先出現的,是年輕麗質的克麗絲汀,然后是英俊瀟灑的拉烏爾子爵,最后才是神秘恐怖的魅影(之前只是別的角色提到一下)。這么做也是為了將全劇的基調牢牢固定在“浪漫愛情為主,驚悚神秘為輔的”的坐標上。
與此同時,為了進一步減弱驚悚效應,創作團隊還將劇中角色胡瑟夫·布凱(Joseph Buquet)的“死期”給推遲了。原著中,布凱一開篇就被魅影吊死在了劇院地下室里:而音樂劇中,布凱則是到第一幕快結束時,才被魅影吊死在了舞臺上。這么做是很符合戲劇特性的:與影視一樣,戲劇的“開頭五分鐘”也是很重要的,往往是確定整部戲的風格情感走向的關鍵。如果剛開場就來一個血腥的兇殺場面,大部分觀眾都會覺得這是一部驚悚懸疑劇,這顯然不是韋伯團隊當年的打算。
音樂劇的特色是有大量的音樂元素,如演唱、舞蹈和背景伴奏。該劇在音樂創作和安排上也是遵循了這個取舍標準。當時正值韋伯的創作黃金期,他發揮了自己的作曲天賦,在大量使用或者借用古典風格音樂的同時,創作了許多優美的流行風格的旋律,并使之成為劇中各個主要的音樂動機:克麗絲汀個人的音樂動機是《想著我》(Think of Me),而拉烏爾與她之間的愛情動機則是《都是我所盼》(AftI Ask of You),等到她和魅影之間的交流則是《音樂天使》(Angel ofMusic),魅影個人的動機,就是主題歌《劇院魅影》(ThePhantom ofthe Opera),他表露內心情感時的動機是《夜之樂章》(Music of theNight),而克麗絲汀與魅影之間的矛盾的動機則是《覆水難收》(Pointof No Return)。仔細觀察,實際上這些更容易讓觀眾接受并記住的旋律,都是發生在劇情故事或者角色情緒發生劇烈轉折的時刻點上,而正是這些點,描繪出了整部作品的情感變化路線。同時也避免了古典風格音樂和芭蕾舞的出現,以及劇中歌劇院的環境地點等這類容易導致加重觀眾欣賞壓力的情況,豐富了觀眾的感受,改善了觀劇體驗。
最后要提的就是大吊燈的設計安排。該劇的賣點之一,就是從空中飛速墜下的大吊燈。前面提到過開場時,大吊燈在主題曲中光芒四射地升起,是為了將觀眾從序幕的幽暗環境中“解放”出來。那么第一幕結束時的大吊燈墜落,也不是隨意的安排。前面提到過布凱是在第一幕快結束時被魅影吊死在舞臺上的,對于一部意圖強調浪漫風格的劇目來說,雖然謀殺這種極端事件可以帶來一個高潮,可要就此結束第一幕,不少觀眾肯定是會帶著陰暗的心態繼續看第二幕的,那就違背了創作意圖。于是,在布凱被殺的震撼場景之后,緊接著的是克麗絲汀和拉烏爾的愛的主題《都是我所盼》,以這一段舒緩歡快的場景,讓觀眾漸漸淡忘剛才的陰暗事件,接著再安排大吊燈從前排觀眾頭頂急墜,然后跌入舞臺的特技結束了第一幕,以一次相對輕松的強刺激,徹底取代了之前的謀殺帶給觀眾的心內心陰影。
音樂劇的創作和制作,本身就是十分精密嚴謹的過程,目的就是為了讓觀眾能深入到劇情之中,沉浸于舞臺效果。事實也證明,這些細致入微的劇情調整和設計,使得本身已擁有富有魔力的優美旋律,浪漫主義為主的舞臺風格的《劇院魅影》,能跨越近三十年時光,依然被全世界各地的“愛音客”們奉為永恒的經典,長演不衰。當然也有說法說,韋伯當時正與他的女神——莎拉·布萊曼(Sarah Brightman)的感情如火如荼,所以劇中女主角有大量的唱段就是為她量身定做的。這也說明,正是因為創作者注入劇中的愛,讓這部作品擁有了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