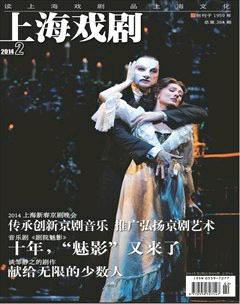尋找全球化語境下“跨文化戲曲”的實踐之路
張婷婷

自西洋戲劇被介紹引進入中國,中國的戲曲該如何改革,讓古老的藝術煥發出時代的生機,成為一個世紀以來戲劇家思考的重要命題。以中國傳統戲曲形式演繹西方戲劇劇目,用戲曲特有的表演符號體系傳播西方的戲劇文化,使外國名著“戲曲化”進行跨文化戲劇實踐,便是中國戲劇家尋找中國戲曲出路的一種有益嘗試。浙江京劇團與上海戲劇學院聯合創作的小劇場實驗京劇《王者·俄狄》,為近年來跨文化戲曲創作的典型代表,該劇將根植于不同文化語境中的東西方戲劇搬到同一舞臺猛烈碰撞與融合,兼采中西表演藝術的意象元素,以戲曲特有的符號體系表現異域文化的現象,值得我們關注與研究。
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洛斯的《俄狄浦斯王》曾被亞里士多德評價為“十全十美的悲劇”,該劇以洗練的倒敘式“回溯”方式,講述了俄狄浦斯“殺父娶母”的必然性命運,環環相扣地解開罪惡發生的過程,展現了人的自由意志在不可抗拒命運籠罩下的掙扎,最終,人歸于毀滅的過程。人的存在是有限的,當人試圖打破自身的有限性挑戰命運,毀滅注定會站在終點冷漠地凝視著人無能為力地一步一步邁向它,這就是古希臘命運悲劇的表達。但是,古希臘悲劇與中國戲曲各自植根于自己的生活語境中,雖然相似之處不少,但本質上仍分屬于不同的兩類藝術門類,不僅外在的表現形式具有較大差異,而且在內在的精神內核、文化理念均存在本質的不同。因此,古希臘的原著的中國化改編中,兩種文化因子的頑強體現與碰撞可謂處處可見。這種碰撞首先出現在“悲劇”與“悲感”的處理上。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定義,“悲劇是對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經過‘裝飾的語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別被用于劇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動,而不是敘述,通過引發憐憫和恐懼使這些情感得到疏泄。”悲劇要引發“恐懼”,必須避免悲喜混雜現象,為保持悲劇的莊嚴和嚴肅風格,基本上不允許在悲劇中滲入喜劇因素,“拋棄了簡略的情節和滑稽的詞句,經過很久才獲得莊嚴的風格”,悲劇不允許夾雜著喜劇的元素,否則就是向觀眾低俗趣味的妥協,必然遭到批評,例如莎士比亞的《麥克白》就是這類的例子:“拿滑稽跟悲劇的崇高的恐怖混在一起的,也只有《麥克白》中那場著名的戲。……這場戲是莎士比亞面對著那群特殊觀眾的一種讓步,這些觀眾今天是達官貴人,明天是喜歡窮開玩笑和暢懷大笑的粗野的水手。”與此相較,中國戲曲始終是伴隨著日常“娛樂”而存在的,“娛人”是戲曲肩負的最高使命,“不插科,不打問(諢),不為之傳奇”,“中間惟有笑偏饒。教看眾樂醄醄”,插科打諢,嬉笑打鬧,或宣泄放縱,輕浮粗俗,諸如此類的感性抒發形式,無不具有“娛樂化”的特點,因此中國戲曲很少有類似于西方嚴肅悲劇,它的“悲”是一種“悲苦”的情調,往往以“悲喜相錯”的情節布局展現悲喜交集和苦樂柑錯,以達到“忻喜之馀忽生悲痛,乃見真情”的效果。作為制造幽默效果的丑角,在戲曲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往往在情節過于沉重時,便會出來插科打諢。調節氣氛,照戲曲腳色行當設置丑角,必然破壞嚴格意義的“悲劇”,若按照西方“悲劇”的定義,則須犧牲戲曲的生動與活潑拋棄丑角。
嚴肅的悲劇與“悲苦”的戲劇在跨文化的戲曲中如何調和?《王者·俄狄》沿著“去神話化”的路徑進行了嘗試,讓敘事高度“中國化”。“謎一樣的遙遠國度梯國”的安排,模糊了東西方的地域差異,“謎一樣的傳奇國君俄狄”的設置,淡化了人物的國別,將古希臘原著中至高無上的神隱去,安排三位自稱瘋子的丑角——神算子、神珠子、神靈子,作為算命神,他們身穿八卦衣,手執拂塵,巫師般神秘地跳著、唱著,戲謔著,并通過隱喻性的臺詞,反復強調“懲罰一人,需解開先前的血疑”的隱射,不斷暗示俄狄王“黃沙蓋臉,死無全尸”的命運,正如編劇孫惠柱所言:“我是從中國文化中取材,把神示改為算命,把克瑞翁這個‘國舅塑造成像曹操那樣,企圖挾天子以令天下,而俄狄則成了一位充滿理想主義、為救國民不惜‘大義滅己的少年天子。”隱喻性氛圍的烘托貫穿全劇始終,丑角雖然以戲謔式的方式表演,但卻極具感染力地告訴觀眾,客觀世界中命運的必然與剝開這種必然的潛在性。俄狄王面臨艱難的選擇,這種選擇是非此即彼的,不可調和的,拯救遭受瘟疫的國家,則須揭開自己的命運,揭開自己的命運必然遭到徹底的毀滅,拯救蒼生的信念支持著俄狄王層層撕開不可逆轉命運的真相,同時也剝繭抽絲般地抽搐著觀眾的心。俄狄王以自我毀滅的方式擔當起拯救民族苦難的選擇,具有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普世性精神,這種戲劇藝術力量的傳達,即便是當下社會也具極大的感染力:如此徹底的社會災難,如此壓榨靈魂到極限的命運魔咒,如此掙扎撕裂的內心,如此不可調和與對抗的沖突,以一種極端的力量展現人性與命運博弈的張力,無不殘酷地敲擊著觀眾。普世性的精神力量,使戲劇藝術立刻“鮮活”起來,丑角諧謔的隱喻,非但沒有削弱悲劇氛圍的營造,反而調動起觀眾的精神和情緒,使得人在劇場中超越了文化的差異,關注到人性本質力量,從而在精神層面上引起最奧秘的質變。借用勃來特列的表述:“僅僅是不幸不能引起我們悲劇性的憐憫和畏懼,悲劇性的憐憫和畏懼是在沖突的目睹中和隨之而來的痛苦中獲得的,它們不僅訴之于我們的感覺和自衛的本能,并且深深感動我們的心靈和精神。真正悲劇性的沖突訴之于我們的精神,因為這是精神的沖突,有權力控制人們精神的力量和人們之間的沖突。這些力量就是人類的本質,尤其是人的倫理天性。家庭與國家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兄弟與姐妹之間,丈夫與妻子之間,公民與統治者之間,公民與公民之間的責任與感情的沖突,還有,在戀愛與榮譽,偉大目的、遠大理想如宗教、科學、或公眾福利等等之間的沖突——這些力量才在悲劇性的情節(動作)里表現出來。并且,這些力量是有權力要人類俯首帖耳的,這樣的沖突在悲劇里表現出來,才是深刻的,帶有普遍性的。”人的最本質的精神表達,超越了東西方文化的界限,打碎了藝術形式隔離,戲曲的表達只是一種形式,人性精神的超越性本質,才是人類戲劇共同探索的。
西方戲劇情節整一的規范與中國戲曲抒情化的表現,同樣是改編者需要調和的元素。古希臘悲劇的展開,按照“形式邏輯”的路徑,注重情節的發生、發展、結局的“完整”與“一致”,“戲劇不像史詩那樣描述整個世界的情況”,而“只突出它的基本內容所產生的單純沖突”,故事的敘述按照戲劇沖突的邏輯關系環環相生,處處相扣。中國的戲曲美學價值,更多地在于“以歌舞演故事”的抒情表達,“唱、念、做、打”除了推動故事的敘事之外,更能將隱性的內心感受顯性地傳遞給觀眾,同時還帶有一份形式上的觀賞愉悅與審美趣味,因此戲曲擅長于抒情化的演繹。《王者·俄狄》糅合兩種戲劇形式時,盡量簡化故事的曲折呈現,精簡人物關系,剔除多余的情節,所有的事件集中于俄狄王對真相的追問上,聚焦在一步步發現命運的情節推進的過程中,細膩刻畫了人物內心變化,以戲曲擅長的唱念做打,強化心靈起伏轉折的掙扎與撕裂,“就故事情節而言,《王者·俄狄》的改編與原著并無多大出入,說的都是一個理想化的英雄毀滅的歷程。但是,巧妙地運作時空流程,細膩地呈現主要人物的思想情感,夸張地營造氣勢和氣氛,彰顯出東西方戲劇在戲劇美學風格上的差異和不同。這是《王者·俄狄》在此次國際戲劇節中深深吸引國外觀眾的亮點。”舞臺背景雖然打破了一桌二椅的形式,但仍以“空”的傳統寫意化方式設置,在“空的空間”里,無論“神巫舞”烘托的神秘氛圍,“奔馬舞”傳遞的急切心情,“刺目舞”營造的凄美悲情,高難度的甩發、急速的蹉步、跪步、顛步、超長的水袖耍舞、快捷迅猛的開打騰翻、載歌載舞的詠嘆唱念,無不將戲曲“以歌舞演故事”的形式,運用得淋漓盡致。尤其在最后一幕,命運的真相被揭開,俄狄王面臨著“黃沙蓋臉,死無全尸”結局,他以刺瞎雙目茍且活著的方式進行自我懲罰與流放,此時,語言的表達已經無力了,舞臺上俄狄王猛然從銀白的龍袍寬袖中甩出3米長幅的水袖,以寫意化的方式傳遞刺目震撼而悲壯的場景,血紅的水袖極具象征意味,如同兩道穿心刺目的刀劍,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方式,將內在性的情感與超越性哲理憑借身段的舞動詮釋出來,古希臘悲劇的生命力透過傳統京劇的形式,竟然鳳凰涅槃般地重新綻放。人類的語言是有限的,而意義是無限的,用有限的語言表達無限的意義,是一種悖論,某種程度上,思想一旦變成文字,便失去了與聲音、與對話語境的活生生的聯系,正如黑格爾體系認為的那樣:“內在的思想被外化為語言時必然會異化:思想外化為語言,作為一種‘外在的表達,所遮蔽的東西如所開敞的東西一樣多,而且永遠不可能把內在的思想表達得恰到好處。”身段動作的詮釋,豐滿了語言表達的干枯,延展了語言之外的意義,表達了“不可言說的言說”,戲曲以特有的藝術形式打破了語言的局限,將古希臘悲劇潛藏的精神與價值表現出來,延展了藝術表達的疆界,創造了一種新的藝術形式,“打碎語言以接觸生活,這便是創造或再創造戲劇”。從國際戲劇協會塞浦路斯中心主席克里斯塔斯基·喬治烏觀感中,我們可以窺見跨文化實驗戲劇的震撼:“我們常常在一些古希臘戲劇表演中只看到技巧,看不到激情,或者只看到激情,而看不到精彩的技巧。在你們這些中國藝術家身上,我卻看到了精致的京劇表演和充滿激情的古希臘悲劇人物的心靈激蕩共存一體,太震撼了。”盡管俄狄成為“中國人”,按照傳統戲曲寫意化的方式進行表達,但舞臺上種種富有意味的文化碰撞與交融轉換,卻將古希臘悲劇蘊含的本屬于西方古人的命運、哲思、倫理、情感演繹出來,而西方古人的命運、哲思、倫理、情感又通過京劇的藝術形式與當代中國人的心靈體驗發生共振,顯示出強大的震撼力與生命力,藝術和審美的普遍價值是超越時間與空間的。
自西方戲劇被介紹引進入中國。為中國戲劇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營養,但兩種不同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也貫穿了整個中國當代戲劇發展進程。對于西方戲劇,應深入其文化的精神,對其文體形式、語言介質、藝術思維、審美趣味、美學原則、本體內涵等深入理解,才能真正從藝術內在的本體出發,將中西戲劇的文化精髓會通融合,從而促進本土戲劇的健康發展,建立既適應時代潮流又符合中國傳統審美習慣的民族戲劇。否則,就會破壞東西方戲劇的符號系統,造出“似驢非驢,似馬非馬”的戲劇,這樣失敗的跨文化戲劇實踐的例子也大量存在,例如法國戲劇家謝克納導演的京劇《奧瑞斯提亞》就是這樣的典型例子:“這部劇作帶有‘環境戲劇的鮮明特征——讓現場的觀眾參與演出,臺灣搞怪的電視文化和夸張的選舉文化、閩南方言、日語、英語、京腔韻白應有盡有,劇中人的裝扮有的像歐洲人,有的像日本人,有的像中國臺灣當代電視節目主持人,有的則像怪物。這部劇作確實有‘跨文化的鮮明特色,但它‘跨過了‘界——既不顧改編對象古希臘悲劇名著《奧瑞斯提亞》三部曲內容和審美特征的規定性,也不顧京劇劇種的基本規范,結果是:它既不像古希臘悲劇,更不像京劇,它只不過是謝克納‘環境戲劇的一次游戲式的實踐,是對京劇和古希臘悲劇輕率而不負責任的戲弄,因此,它遭到抵制與抗議是理所當然的。”@跨文化戲曲的實驗,并不是簡單地將兩者異質文化進行拼湊,必須深入中國固有文化和傳統藝術的客觀實際,伴隨著文化碰撞與交融的痛苦與掙扎,但無論過程有多么痛苦,其結果卻是富有積極意義的,同樣,京劇《王者·俄狄》的改編的成功也伴隨著文化的吸引與抗拒,融合與搏斗,值得我們認真地分析與總結,也為戲曲在當下的發展,開辟了一條富有生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