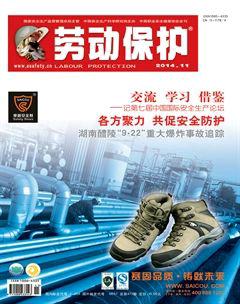工傷保險行政糾紛典型案例解讀(下)
黃樂平+徐建軍
判例三:何培祥訴江蘇省新沂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認定行政案
基本案情
原告何培祥系江蘇省新沂市原北溝鎮石澗小學教師,2006年12月22日上午,原告被石澗小學安排到新沂城西小學聽課,中午在新沂市區就餐。因石澗小學及原告居住地到城西小學無直達公交車,原告采取騎摩托車、坐公交車、步行相結合方式往返。當日15時40分左右,石澗小學職工邢漢民、何繼強、周恩宇等開車經過石澗村大陳莊水泥路時,發現何培祥騎摩托車摔倒在距離石澗小學約二三百米的水泥路旁,隨即將其送往醫院搶救治療。12月27日,原告所在單位就何培祥的此次傷害事故向被告江蘇省新沂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后因故撤回。2007年6月,原告就此次事故傷害直接向被告提出工傷認定申請。經歷了二次工傷認定、二次復議、二次訴訟后,被告于2009年12月26日作出《職工工傷認定》,認定:何培祥所受機動車事故傷害雖發生在上下班的合理路線上,但不是在上下班的合理時間內,不屬于上下班途中,不認定為工傷。原告不服,向新沂市人民政府申請復議,復議機關作出復議決定,維持了被告作出的工傷認定決定。之后,原告訴至法院,請求撤銷被告作出的工傷認定決定。
裁判結果
經江蘇省新沂市人民法院一審,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上下班途中的“合理時間”與“合理路線”,是兩種相互聯系的認定,屬于上下班途中受機動車事故傷害情形的必不可少的時空概念,不應割裂開來。結合本案,何培祥在上午聽課及中午就餐結束后返校的途中騎摩托車摔傷,其返校上班目的明確,應認定為合理時間。故判決撤銷被告新沂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作出的《職工工傷認定》;責令被告在判決生效之日起60日內就何培祥的工傷認定申請重新作出決定。
專家解讀
關于上下班途中發生通勤事故受傷認定為工傷的規定,我國的工傷保險立法也經歷了多次的變動,核心在于如何理解“上下班途中”。
1996年實施的《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以下簡稱《試行辦法》)第八條第(九)項規定,“在上下班的規定時間和必經路線上,發生無本人責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責任的道路交通機動車事故的”屬于工傷。該規定將“上下班途中”限定為“規定時間”和“必經路線”,且限于機動車事故。從法規的規定來看,采取的是較為嚴格、保守的立法思路。這一規定導致在實務當中如何認定是否屬于“必經路線”,以及起點至終點如何起算為“必經路線”產生了諸多的困難。
由于《試行辦法》的規定在實務操作中引起諸多爭議,2004年實施的《工傷保險條例》在《試行辦法》的基礎上,對于通勤事故導致的工傷在立法上作出了較大的調整,《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規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大大拓寬了工傷認定的范圍,體現在兩個方面的重大變化,一是刪除了“上下班的規定時間和必經路線”,對“上下班途中”不再作時間與路線的限制;二是對機動車事故傷害不再限于“無本人責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責任”,只要發生機動車事故傷害即使本人承擔主要責任或者全部責任也可以認定為工傷。從這一規定來看,《工傷保險條例》大大放寬了對于“上下班途中”的理解,加大了保護勞動者工傷權益的力度。
2010年修訂的《工傷保險條例》沿襲了原版的立法思路,沒有對“上下班途中”作范圍限定,但對于通勤事故的類型作出了限制,即非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城市軌道交通、客運輪渡、火車事故。
從立法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工傷保險立法理念的變化,進一步確立了保護勞動者權益、兼顧公平的核心原則。本案的處理,體現了司法對于立法原則的準確把握,符合法律規定的立法原意。本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對于“上下班途中”作出的規定,總結了司法實踐中常見的爭議性問題,對法規理解的誤區進行明確,有利于統一司法裁判尺度、促進保護工傷職工的合法權益。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本案雖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判例,在裁判理由方面也并非無懈可擊。何培祥在上午聽課及中午就餐結束后返校的途中騎摩托車摔傷,固然可以認定為返校上班,是基于上班途中的合理時間內發生的工傷。對何培祥上午外出聽課及返校上班的事實認定,如果認定為“因工外出”似乎更為恰當,倘能如此,那么判決認定為工傷的理由就要簡單得多。
判例四:鄒政賢訴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認定行政案
基本案情
宏達豪紡織公司系經依法核準登記設立的企業法人,其住所位于被告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轄區內。鄧尚艷與宏達豪紡織公司存在事實勞動關系。2006年4月24日,鄧尚艷在宏達豪紡織公司擅自增設的經營場所內,操作機器時左手中指被機器壓傷,經醫院診斷為“左中指中節閉合性骨折、軟組織挫傷、仲腱斷裂”。2006年7月28日,鄧尚艷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向被告申請工傷認定時,列“宏達豪紡織廠”(而不是“宏達豪紡織公司”)為用人單位。被告以“宏達豪紡織廠”不具有用工主體資格、不能與勞動者形成勞動關系為由不予受理其工傷認定申請。鄧尚艷后來通過民事訴訟途徑,最終確認與其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的用人單位是“宏達豪紡織公司”。2008年1月16日,鄧尚艷以宏達豪紡織公司為用人單位向被告申請工傷認定,被告于1月28日作出《工傷認定決定書》,認定鄧尚艷于2006年4月24日所受到的傷害為工傷。2008年3月24日,宏達豪紡織公司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準注銷。鄒政賢作為原宏達豪紡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09年3月10日收到該《工傷認定決定書》后不服,向佛山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申請行政復議,復議機關維持該工傷認定決定。鄒政賢仍不服,向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法院判決維持被告作出的《工傷認定決定書》。宣判后,鄒政賢不服,向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裁判結果
法院經審理認為,因宏達豪紡織公司未經依法登記即擅自增設營業點從事經營活動,故2006年7月28日鄧尚艷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向禪城區勞動局申請工傷認定時,錯列“宏達豪紡織廠”為用人單位并不存在主觀過錯。另外,鄧尚艷在禪城區勞動局以“宏達豪紡織廠”不具有用工主體資格、不能與勞動者形成勞動關系為由,不予受理其工傷認定申請并建議鄧尚艷通過民事訴訟途徑解決后,才由生效民事判決最終確認與其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的用人單位是宏達豪紡織公司。故禪城區勞動局2008年1月16日收到鄧尚艷以宏達豪紡織公司為用人單位的工傷認定申請后,從《工傷保險條例》切實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立法目的考量,認定鄧尚艷已在1年的法定申請時效內提出過工傷認定申請,是因存在不能歸責于其本人的原因而導致其維護合法權益的時間被拖長,受理其申請并作出是工傷的認定決定,程序并無不當。被告根據其認定的事實,適用法規正確。依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判決維持被告作出的《工傷認定決定書》。
專家解讀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工傷認定申請時效問題。關于工傷認定申請時效的規定,工傷保險立法也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申請主體的變化,二是申請時效的變化。1996年的《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只規定了用人單位申請工傷認定的時效,即企業應當自工傷事故發生之日或者職業病確診之日起,十五日內向當地勞動行政部門提出工傷報告。而2004年施行的《工傷保險條例》及之后修訂的條例規定,工傷認定的申請主體為用人單位或工傷職工一方,前者的申請時效為事故傷害發生之日或者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之日起30日內,工傷職工一方申請工傷認定的時效為事故傷害發生之日或者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之日起一年之內。
從表面上看,立法對于工傷認定申請主體及申請時效的放寬有利于保護工傷職工,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用人單位卻往往借助時效的規定逃避責任,比如采取欺詐手段騙取職工申請工傷認定的必備材料,導致工傷職工無法自行申請認定,或者利用職工對法律的無知而拖過一年的申請時效。實踐中的種種做法,不但沒有減少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并導致了諸多惡性事件的發生,直接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
從立法本義而言,設立時效制度是為了敦促義務人及時履行義務、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但實施效果并不盡如人意,反而起到了負面的效果,這也引發了關于工傷認定申請時效制度存廢的爭議。
關于時效制度的另一個爭議,是時效的屬性問題。有人認為“一年”是除斥期間,不得中斷、中止;也有人認為“一年”是時效限制,可以適用中止、中斷的情形。本次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規定,重申了“一年”為時效期間,并列舉了時效中止、中斷的情形,將工傷職工通過民事求償程序追索賠償的行為排除在時效限制之外,充分體現了保護工傷職工的立法宗旨,對于工傷處理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性意義。(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