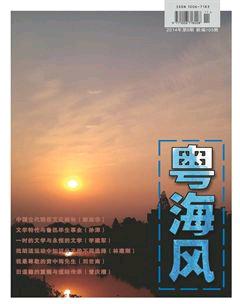書法閱歷的詩化
陳黨
在學書的過程中,我們都會有這樣的體會:同一本帖,在不同的人生階段臨摹,往往會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正如清代文學家張潮在《幽夢影》中寫到那樣:“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皆以閱歷之深淺為所得之深淺耳。”張潮把閱歷的深淺分為少年、中年和老年三個階段,并與“窺月”“望月”“玩月”三種境界相類比,不僅闡述了閱歷視域對讀書有重大的影響,而且把閱讀過程的艱辛詩化,令讀書閱歷頗有詩情畫境。畢淑敏也曾經談起她閱讀安徒生童話《人魚公主》的經歷。8歲時讀出了人魚公主的慘痛,18歲時理解了這是一篇寫愛情的童話,28歲時讀出這篇童話中的母愛,38歲時熱衷探討寫作技巧,48歲的時悟出這是一篇寫靈魂的故事。
張潮是講一生閱讀可分三階段,畢淑敏在做一生讀一本書的總結。而畢淑敏還從更廣深方面闡述閱歷,8歲是讀者身份的感悟,18歲是文本角度的體悟,28歲是作者立意層面的品讀,38歲是文學創作立場的言說,48歲是宇宙人生的諦思。她的《人魚公主》文學閱歷,始于反復咀嚼,證于熟讀深思,成于融會貫通。讀書閱歷如此,書法閱歷亦如此。書法閱歷之深之淺,不僅影響著學書的傾向,某些時候甚至關系到學書的效果。
概而言之,書法閱歷是學書法的經歷;細而言之,書法閱歷是學書得法,既體現書法的藝術性,又包含非藝術性;藝術性是書法內在問題,非藝術性是外在問題;但書法閱歷又是內在與外在關系問題,而歸根結底是人與書法關系問題。
學書經歷了遍訪名師、觀書法史千卷、池水盡墨等后知曉紙筆墨之性,懂得技進乎道,選帖關乎天賦才情。故書法閱歷玄妙,悟時是字帖、師從、技法等內外相融;惑時是人與書抵牾。倪蘇門的《書法論》指出,學書有“三關”:初段專一、次段廣大、三段脫化等。他認為初段一筆一畫和轍方可做中段,三段是“守定一家”,又“時時入各家”。這“三關”之論是循序漸進的學書之法,而第三段含有圓融反復之義。學書者望文便知“三關”是想當然的理想化論述,“三關”的時間概念空泛,指向不明。值得指出的是,他僅提出了學書的內在問題,尚未涉及學書的內與外的關系問題。更何況學書因人而異,其間反反復復的艱辛,冷暖自知。朱履貞的《書學捷要》說,書有“氣質、天資、得法、臨摹、用功、識鑒”等六要,他進一步說,六要俱備,方能成家。其中“氣質、天資”屬先天稟賦,“得法、臨摹、用功、識鑒”屬后天素養。誠然,先天和后天因素圓融交匯是指點學書之金針。
就個體而言,書法閱歷之要務,是知書帖與自性的契合,且要躬行踐履。陸游曾說:“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選帖到選好帖其間的筆墨功用確實是少壯功夫老始成。在準確把握書體特征后,須做到學以致用、知行合一去創作,才能更加深入地領悟臨摹的筆墨功夫與創作所蘊含的深意。
臨與創實踐的體悟,勢必因人深淺有別,原因在于書法學習并非僅是對字帖的簡單再現,而是人生經歷都會參與進來的過程。年輕的時候,書法實踐不夠豐富,洞察力、理解力等方面自然欠缺,所以在學書時往往容易只看帖的一點一劃,對帖中蘊含的豐富書法意義難以全面把握,如隙中窺月,難免有視野不寬、觀察不周的問題。故常學不得法,總是忙著找名師指點,而意見紛紛擾擾,難以取舍。隨著年齡的增長,眼界學識、經驗以及分析問題、理解問題的能力都有大幅度的提升,往往能夠從更高的層次、更寬的視角觀察書法,掌握些書法知識,如庭中望月、臺上玩月般,積學深思,書法閱歷豐富多了。
要么是專而博,或博而專;要么諸體皆能,要么獨擅一體,多年的書法實踐往往而是。若只有寫字的表象,歷煉成不了書法的素養,那么僅是書匠而已,只有書法閱歷之名,而無書法閱歷之實,盡管書法的學習與實踐并重,但并無多大益處。若經歷了學書的幾曲浮沉,曉得書道之玄奧,那么讀懂術業有專攻之理是臨透一家一帖,尚且學書者已有了必須的基本天賦、必備的思維能力、正確的用功方法,那也僅屬于書法閱歷的入門,要使書法想更上一層樓,仍需要書人相通的學書閱歷。
書人相通必備悟性。季維齊的《書史》說:“習書畫者最所需者,學養第三,用筆第二,悟性第一。骨法用筆,如父母賜汝身心。悟性則須參父母未生汝時是何事物。”用筆是字內功夫,屬于技巧,是“千古不易”的法則,學養是字外功夫,妙悟則技進乎道。
悟性者為何?學養蘊育悟性,技法與學養在法帖和交游中有所悟而得。從方法論角度而言,悟性是將已有的經驗嫁接的思維方式,或者說某個人理解一件事或物或某種抽象東西時的速度快,而悟的前提是取決于這個人已有的經驗知識足夠多,并且必須具備觸類旁通的思維方式。雖說悟性是當下性,鮮活且直觀,但也有對事物機智的理解和分析能力。癡呆或遲鈍是缺乏悟性的另一種說法,如常年對視自己作品,如坐井觀天般。突然的領悟或者是如佛家所說的豁然開朗是悟性,它不是抽象中漫長推論的產物,而是如在聽聞中或展廳中觀賞時看到自家的長處或短處時心中的明了,如月出東山般。
故悟性非僅指對書法筆法、結構的領悟。如果你習書時,能做到既看到紙面上的一個字,又留心紙面上一行或兩行等整體關系,那么你對作品的全面理解和深刻把握了,也足以說明你此時已達至“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孫過庭《書譜》)氣通人書的悟性,此乃是在表象的基礎上對書法經歷進行思考領悟、概括提煉,是直覺與思辨的有機統一,非一日之功。書人相通并不是與他臨帖、創作多少有關,或與其年齡大小有關,而是關涉書法界圈里圈外人事閱歷。
隨著書技增長,追求認同的欲望增強,就會尋找機會接觸書法界的人和事,會越來越多地獲得書法和書法界的經驗和教訓,對書法、書法家和書法活動等看法也逐漸明了,觀其為人知書法之道。不過書法圈里圈外的閱歷日趨豐富并不是絕對的,有的人學書日久,由于各種資源缺欠,站在書法圈外久而不得其門徑而入;有的人年齡雖然不大,卻行走在書法活動圈子里,耳濡目染,經過諸多歷練,體驗過各種身份和角色的人物對書法的見解,經歷過參賽的鍛煉和不同評價的磨礪,這種經歷同樣可以讓他擁有豐富的書法閱歷。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是說日臨萬卷紙,只是書內功夫,紙上學來終覺淺;仍然要在書外——書法圈里圈外活動活動,即使遠足千里也是件好事,與君一席話的碰撞,勝臨十年書是之謂也。
毋庸質疑,書法圈里圈外的人脈和學書經驗固然重要,而書法圈里圈外的審美趣尚對學書更有影響。
智永雖勤于藝事,但與同是僧人書法家的懷素相比,則明顯短于見識。懷素和尚在勤奮研習書法上,比智水禪師毫不遜色,但懷素不閉門學書,常出門遠游,拜謁名家,還注重師法自然,“觀夏云多奇峰,輒常師之”(唐·陸羽《釋懷索與顏真卿論草書》),終于創造出“以狂繼顛”的氣勢磅礴的狂草書,名噪一時。智永卻局于一隅,遵守一家,因而在書法史上的地位遠不及懷素和尚。清代金農入都應試未中,郁郁不得志,遂周游四方。他交友廣泛,上至名門公卿、富豪巨賈,下至賣漿引車的貧民百姓、主教九流,無所不有。浪漫的詩人情懷、不修邊幅的書畫家風度、無拘無束的野逸文人氣質是他首創的漆書資糧。金農以賣字賣畫為業,難免把商業習氣帶入藝術領域,故他的作品風格是順應了當時歷史文化發展的趨勢,在抒發個性、力倡新思維等方面影響下,他的書法別有新意。王鐸終生習二王,將二王尺牘拓而為大,是晚明大軸長卷時代的弄潮兒,得神筆王鐸之稱。
一直以來,不少書法家身上普遍存在著這樣一種現象:年輕的時候,雖選好帖臨寫多個時日,迫于現實,一門心思埋頭在字帖里,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臨圣賢書。人到中年以后,也取得書法成就,或是國家、省市級書寫成員都美夢成真。但精力、記性有所下降,書路基本定型,再加上幾十年的書法閱歷,什么人事沒見過,沒經過,早已洞察書壇,參透人情,不需要再到書法典籍中尋求書法真諦,閱讀的欲望往往就會減退,不少人甚至逐漸遠離書本,屬于成功后之困惑,此乃人生精神境界不高,而無法關聯書法內外。
書藝通天人,參造化,重玄悟,關乎性情之奧。書法發展史反復證明,但凡有成就者均幾度回歸經典法帖,重新披閱,它是獲取書法精神的重要源泉,也是提高激發能力的必經之路。如吳昌碩篆書成就極高,墨跡看有25歲臨作,有 46歲所作,有65歲所作,有84歲作,自25歲到84 歲的近六十年的時間里,《石鼓文》學習貫穿他整個書法生涯,所謂“一日不臨,自覺少意”。幾經勤奮實踐,將技法薈萃于胸,是熟而生、生而熟的回歸,有著落而無迷惑,似海納百川般廣收博取。無論為官、經商,還是讀書、治學,只重讀書重閱歷,而不重視交游,極易造成主觀臆斷,縱然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一旦涉及具體的書法層面,則往往因匠氣和怪氣十足而脫離書法藝術實際而變得寸步難行。而重交游,則會導致經驗表征,盡管老于世故、精于謀略,但由于缺乏書道之理指引常常流于窮鄉秀才寫門聯般平庸或落得迎合大眾世俗之習性。
書法閱歷,不僅僅書內書外功夫的錘煉,也不只是對世風把持,它又是文人墨客的狂惑寄托,非技高者不能至也。
喜歡書法、堅持書法的人,終其一生都希望書法有藝術的生命力,然而藝術的生命力和天賦與壽命關聯緊密,更是書法閱歷的天成自化。如唐伯虎和文徵明,一個短命,一個長壽;一個書入神品,一個書入能品;但都是書法史上名家,各有軒輊。唐伯虎清貧而專事自由讀書賣畫生涯,具時名卻淡泊名利,人格獨立過得清閑而超脫。文徵明考取功名仕途不順利,致力于詩文書畫,不再求仕進,以戲墨弄翰自遣,書法博習專精,以小楷造詣最高。唐伯虎的墨跡是風流才子人生閱歷的自性跡化;文徵明的書跡是書生勤奮汗水的凈化。他們游于藝,將人生狂惑自化于書跡,既博覽群書,又專于書道;既潛心學書,又出入文人墨客和市井生活圈。得造化之功,令人生閱歷而藝術;筆墨行走,深契于濁酒中的古今中外事。在翰墨飛揚中镕鑄人生閱歷,技見乎玄妙書道,書跡自是不朽之由也。
書法閱歷的境界貴在于書與人生閱歷參合。
王羲之少年時代師從衛夫人和王廙學書法,他的《題衛夫人〈筆陣圖后〉》、王僧虔的《論書》和庾肩吾《書品》都有佐證,這時期的作品形成了秀麗飄逸的風格;中年時期博采眾碑,即博覽秦漢以來篆隸大師們淳古撲茂、豪放奇肆的作品。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說:“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筆法之雄奇也,蓋所取資皆漢魏瑰奇偉麗之書,故體質古撲,意態奇變。”這時期的作品形成了質樸豐茂的風格。暮年變法創新,他敢于跳出守成博引眾長,其一,取法民間流傳書體章草;其二,精研增損鐘張草法。虞龢在《論書表》中說:“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瓘、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極。”他的書法閱歷在于將“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書斷》)“備精諸體”之“備”,既是天賦才情,又是集一生之所學,更是魏晉書學的眾望所歸,故他提撕閱歷,終于完成了“備”有隸意的質樸的書體蛻變,成就獨具遒勁瑰麗真書、行書、草書非“備”的王體面目,奠定了他“書圣”地位。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闡述的是其人生境界是人生閱歷漸豐而敏悟之力日增并與閱歷得以交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把人生分為三個階段:小時候看到眼前一片光明,是為“正”;二十多歲看到社會一片慘淡,是為“反”;到三十歲,“既不像十來歲時覺得眼前一片光明,也不像二十多歲時覺得一片慘淡”,是人生“合”的階段。“正反和”的人生境界與孔子不謀而合,共同闡明人生智慧在閱歷中歷練而圓滿,即妙在能離能和。王羲之博識蛻變是交匯諸體內在漸變而心裁別出,魏晉變局歷史的向他提出了“通古今之變”的要求。其書,既是個人天賦才情的結晶,亦是魏晉時代的表征,自是超越人與書的內外之界別。
中外名人基于不同理由把人生分成不同階段,闡述了人生閱歷的階段性和變化性,其豐沛意蘊對我認識書法閱歷的階段性頗有啟示。
書法閱歷的階段性在于學書有法。體現在學書法有書路的探索階段、有比賽獲獎的收獲階段、有深入自化的豐富階段和有個性的面目階段等,但不能流入“階段”法執,而以階段非階段名之,是書人天作之合。故有志于學書者,要正其心、堅其志、修其性、立其志、明書理,才能由書路的探索階段走向比賽獲獎的收獲階段;倘若能參合其中意蘊,由約致博,再由博返約而造化,自入書道坦途,能臻至深入自化的豐富階段;釋亞棲《論書》說,凡書通即變,所謂通即融會貫通,所說的變,即是有自家面目,但這個閱歷是一個長期且漸變得過程,也是一個調節與整合各個階段的過程,是以悟為前提,以法度為基礎,以功力為后盾,以膽識為條件,凡此方為不踐古人,自出新意而深俱個人面目,不過這都是身后事。
故此,我悟得,書法閱歷的詩化乃似儒家入世,書名幾經得失,知進退爾后在無何有之鄉中戲筆,似我非我之書頗有老莊逍遙游之意,卒去我相,在佛性中見真我之面目。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