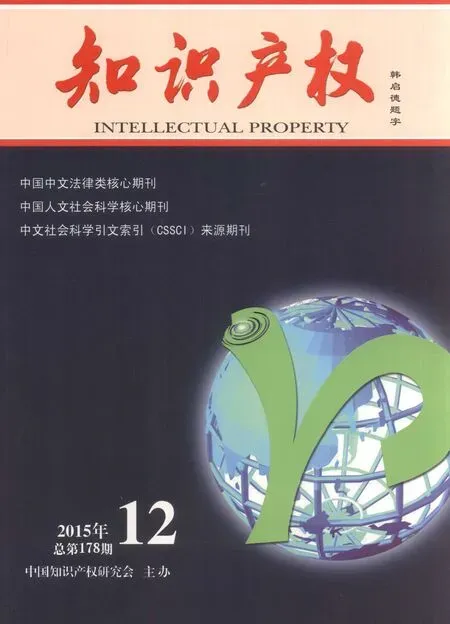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探析——以為網絡知識產權犯罪活動提供幫助的犯罪行為為視角
劉 科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探析——以為網絡知識產權犯罪活動提供幫助的犯罪行為為視角
劉科
內容提要: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中的“明知”僅包括“明確知道”,不包括“應當知道”。判定為網絡知識產權犯罪活動提供幫助犯罪行為中的“明知”時可以充分運用刑事推定,但行為人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所幫助對象從事信息網絡知識產權犯罪的除外。該罪中的“犯罪”不是指具備全部犯罪構成要件意義上的犯罪,而是指犯罪行為意義上的犯罪,因而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實施的信息網絡知識產權違法行為、具備刑事責任能力人實施的達不到特定犯罪情節或者結果要求的信息網絡知識產權違法行為等,均屬于信息網絡知識產權犯罪。不論是單純實施為他人信息網絡知識產權犯罪提供幫助的行為還是參與正犯行為,都應當遵循從一重罪處罰的法理。
關 鍵 詞:明知 網絡知識產權犯罪 罪數
Abstract:In Crime of Providing Assistance for Network Crime, “knowledge” refers to only “full awareness”rather than “should know”. When determining “knowledge”, the means of criminal presumption applies to anyone but those who can prove with evidence that he/she does actually not know the aiding object committing the Crime of Infrin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on the Network. “Crime” hereof means the crime in the meaning of criminal behavior, rather than the crime in the meaning of possessing all constitutive elements. Therefore, “the Crime of Infrin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on the Network” includes committing illegal acts without criminal capacity which infrin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on the network and performing unlawful act that fails to meet the requested specific criminal circumstances or criminal consequence and so forth. Whether purely providing assistance for the Crime of Infrin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on the Network or participating as a principal offender, these conducts should be bound by the principle of “giving severer punishment as one crime”.
Key words:knowledge; the Crime of Intring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on the Network; quantity of crime
《刑法典》第287條之二(根據《刑法修正案(九)》增設)規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2015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將該條文所涉罪名確定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該罪自起草之日即面臨著諸多爭議a參見周光權:《網絡服務商的刑事責任范圍》,載《法學雜志》2015年第5期。,然而,在刑法條文通過以后,“即使刑法有缺陷,我們也應當運用刑法解釋方法,將其解釋得正當、沒有缺陷”b張明楷:《刑法解釋理念》,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在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中,為網絡知識產權犯罪提供幫助行為較為典型,因此,本文運用刑法解釋的基本原理,以為網絡知識產權犯罪活動提供幫助行為為主要視角,對該罪中若干爭議問題的理解與認定展開研討。
一、“明知”的理解與認定
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首先需要具備“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要件,因而“明知”成為該罪構成要件要素。
(一)“明知”的含義
“明知”,顧名思義就是“明明知道”或者“明確知道”。在我國刑法中,“明知”與“應知”有時并列使用,兩者之間雖有緊密聯系,但既不包容,也不交叉。然而,晚近一些司法解釋在解釋“明知”時,經常將“應知(應當知道)”涵括在內c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1998年5月8日《關于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輛案件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2日《關于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04年《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因而使得學術界與實務界對“明知”的含義產生了不同的認識。
按照對“明知”范圍界定的由窄到寬,大體上可以將“明知”的含義分為三種:第一種觀點認為,“明知”就是“確知”,即明明知道、明確知道。d參見蔡桂生:《國際刑法中“明知”要素研究》,載《法治論叢》2007年第5期。如果行為人僅僅是模模糊糊地知道,或者僅有一定的合理懷疑,不能認定為“明知”。第二種觀點認為,“明知”包括“確知”和“可能知道”。“確知”是對他人有犯罪行為的確定性認識;“可能知道”是對他人有犯罪行為的可能性認識。行為人根據有關事項,知道他人可能有犯罪行為,但又不能肯定。e參見趙秉志、許成磊:《侵犯注冊商標權犯罪問題研究》,載《法律科學》2002年第3期。第三種觀點認為,“明知”是知道(“確知”)和應當知道(“應知”),這是司法解釋采納的觀點,為大多數學者所采用。f參見唐治祥:《對“明知他人有間諜犯罪行為”的理解》,載《成都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
本文認為,第一種觀點相對更為可取,理由是:首先,第二、三種觀點把明知解釋為包括“可能知道”與“應當知道”,而“可能知道”也就意味著“可能不知道”,“應當知道”的內在含義就是“不知道”,無論如何,把刑法上的“明知”解釋為包括“不知道”、“可能知道”在內,在構成要件的認定上可能欠缺主觀的違法要素,也存在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嫌疑,確實難以使人信服。其次,第一種觀點對“明知”的界定雖然存在缺陷,即“對明知的限定范圍過于狹窄,容易為狡猾的犯罪分子所利用,使得他們可以借口未被明確告知而不明知,從而逃避刑法的懲罰”g馮英菊:《論贓物犯罪中的“明知”》,載《人民檢察》1997年第12期。,但“明確知道”是“明知”的本來含義,不能為了克服其文義缺陷而違背刑法解釋的基本原理。再次,對于“明確知道”認定中存在的認定難等缺陷,完全可以通過刑事推定制度來解決。“推定行為人知道,其法律效果與行為人明確知道并無區別”h皮勇、黃琰:《論刑法中的“應當知道”——兼論刑法邊界的擴張》,載《法學評論》2012年第1期,第54頁。。根據社會一般常識進行推定,既符合認識的普遍規律和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又可以彌補“明知”認定中存在的缺陷。
(二)“明知”的認定
“明知”作為表現犯之表現,是行為之外需要證明的主觀違法要素,不能從其行為中直接得以確證。于是,司法實踐中辦理該類案件經常遇到以下難題:行為人往往聲稱自己僅僅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等技術支持工作,或者僅僅提供支付結算等一般的勞務幫助、業務合作,自己從事的是合法的網絡經營業務,對于被幫助人是否利用自己的幫助從事信息網絡犯罪并不知情。而脫離開行為人對被幫助人的犯罪行為的明確認識(“明知”),行為人的違法行為也就難以認定。
本文認為,“明知”的認定難題是所有的包含“明知”構成要件要素的犯罪認定中的一個共性問題。既不能因為“明知”的不好認定,而動輒要求立法取消“明知”的構成要素(取消“明知”要素,可能會違反刑法的責任主義原理),或者在取消“明知”要素之前,司法上消極等待、無所作為;也不能違背刑事訴訟中的程序正義,以刑訊等手段逼取“明知”的口供。正確的方法是,加強理論研究,依賴刑事推定制度來認定“明知”。
當前,我國一部分司法解釋及其他規范性文件明確了“明知”的推定規則。例如,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屬于《刑法》第214條規定的明知:(一)知道自己銷售的商品上的注冊商標被涂改、調換或者覆蓋的;(二)因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受到過行政處罰或者承擔過民事責任、又銷售同一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三)偽造、涂改商標注冊人授權文件或者知道該文件被偽造、涂改的;(四)其他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2012年頒布的《關于依法嚴懲“地溝油”犯罪活動的通知》之“二”規定:“認定是否明知,應當結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認知能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同案人的供述和辯解,證人證言,產品質量,進貨渠道及進貨價格、銷售渠道及銷售價格等主客觀因素予以綜合判斷”。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煙草專賣局《關于辦理假冒偽劣煙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座談會紀要》、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都有類似的規定。
在網絡知識產權犯罪中,也存在一個著名的推定規則(“紅旗標準”規則)。該規則的基本含義是:如果有關他人實施侵權行為的事實和情況已經像一面鮮亮的紅旗在網絡服務商面前公然飄搖,以至于網絡服務商不可能不發現他人侵權行為的存在,則可以認定網絡服務商存在“明知”。該規則緣起于美國,并已為世界各國普遍采納。采用該規則,可以判別當下許多熱門案件中網絡服務商的“明知”問題。例如,當下熱門的流行歌曲著作權人、唱片公司至今尚未授權任何一家網站在線免費提供歌曲的下載服務,這是常識,網絡音樂經營者不可能不知道。百度這類的網絡服務商只要“不經意地”掃一眼網頁中列出的歌曲名稱和演唱者姓名(例如“光良—童話”),就立刻能夠意識到被鏈接的文件是由受著作權法保護的音樂制品制成并由第三方網站未經許可而擅自上傳至網上的。這是任何一個與百度網站的編輯或者經營管理人員具有相同認識能力的理性人都不可能意識不到的事實。基于此,可以推定信息網絡服務提供者對于服務對象的侵權事實存在“明知”i參見王遷:《論“信息定位服務提供者”間接侵權行為的認定》,載《知識產權》2006年第1期,第11-18頁。。
結合網絡知識產權犯罪的實際,以下事實也可以作為推定行為人對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知識產權犯罪具有“明知”的認識因素:行為人明知他人由于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知識產權違法犯罪而承擔民事責任、受過行政處罰乃至刑事處罰,不認真核實其經營業務、經營范圍,仍然向其提供信息網絡服務的;收取的網絡知識產權服務費用明顯高于正常標準的;被服務對象存在偽造、涂改、轉借有關網絡經營業務資質證書的;有關交易文書明確記載該服務對象可能實施網絡知識產權犯罪的;服務對象實施信息網絡知識產權犯罪被發現后,行為人轉移、銷毀物證或者提供虛假證明的;所服務對象均從事或者主要從事信息網絡知識產權犯罪活動的;行為人與被服務對象存在商業合作或者利益分成關系的,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推定是人們基于經驗法則而來的。人們對社會上的某種現象進行反復認識之后,逐漸掌握了其內在規律,對這種內在規律的認識即經驗法則,具有高度的蓋然性。由于事實推定的機理基于蓋然性,因而得出的結論并非是必然的,而存在或然性”j何家弘主編:《證據學論壇》,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頁。。因此,為保證推定結論的正確性,應允許行為人反駁和作出合理解釋。行為人反駁只要達到合理程度即可否認“明知”的存在。例如,在收取的服務費用明顯高于正常標準的情況下,行為人只需證明其對知識產權違法犯罪活動提供服務收取的費用與對合法業務活動提供服務收取的費用一致,或者其提供的服務質量明顯高于同類服務商等,即可以認為其作出了合理解釋,從而否定“明知”的存在。相反,如果行為人針對合法業務活動收取的費用低而針對知識產權違法犯罪活動收取的費用高,而且服務質量沒有顯著區別的情況下,針對從事知識產權違法犯罪活動的被服務對象收取的高額服務費即可以用來推定其“明知”。
此外,在證據法上,推定與推論并非相同概念。推論是指根據現有證據,采用邏輯分析與經驗判斷的方法,對是否明知進行內心確證。對于明知的認定來說,推論是最為常見的方法。網絡版權法中的“通知與移除規則”即是運用推論證明“明知”的有效辦法。該規則為1998年美國《千禧年數字版權法》首創,并為世界各國普遍接納。其基本含義是:如果權利人向網絡服務商發出通知,告知其儲存或者鏈接的內容侵權,則該通知能夠起到讓網絡服務商明知的作用。在收到權利人的通知之后,網絡服務商如果不移除或者斷開侵權內容的鏈接,則除非其能夠證明權利人的指稱虛假,否則,就應當被認定為是在明知他人侵權行為的情況下,以保留侵權內容和鏈接的方式幫助其擴大侵權損害后果,應為此承擔連帶責任。在這種歸責方式中,收到通知,即為證明其存在明知的有力證據。
(三)“明知”的認識錯誤
“明知”的認識錯誤,即行為人對被幫助的人是否實施信息網絡犯罪產生認識上的錯誤。這又包括兩種情況:其一,將他人不實施信息網絡犯罪的行為誤以為想實施信息網絡犯罪而進行幫助。這種情況下,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犯罪故意,客觀上也實施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的行為。但由于被幫助的信息網絡行為不是犯罪行為,不符合客觀構成要件,也不會對信息網絡管理秩序造成破壞,因而不構成犯罪。其二,將準備實施信息網絡犯罪的行為誤以為不是實施信息網絡犯罪的行為,而進行幫助。這種情況下,行為人由于主觀上不具有幫助實施信息網絡犯罪的故意, 缺乏該罪的主觀構成要件,也不構成犯罪。
二、“犯罪”的理解與認定
關于此處的“犯罪”可能存在的爭議是:“犯罪”是指完全符合犯罪構成意義上的犯罪(在我國傳統的四要件體系中,符合犯罪構成的四個要件;在大陸法系三階層體系中,符合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和有責性三個要件)還是指犯罪行為意義上的犯罪(在我國傳統的四要件體系中,符合犯罪客觀方面的行為要件;在大陸法系三階層體系中,符合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要件k也有學者將構成要件符合性與違法性要件合稱為“不法”要件。)?對該問題的不同認識,顯然會導致對許多具體問題的不同回答:如果認為“犯罪”是指完全符合犯罪構成意義上的犯罪,那么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實施的信息網絡知識產權違法行為、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實施的情節不夠嚴重的信息網絡知識產權違法行為(例如,被幫助人實施的侵犯著作權罪沒有達到“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被幫助人過失實施的信息網絡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等,就不屬于該罪中的信息網絡犯罪,進而為這些信息網絡知識產權違法行為提供幫助的,也不構成該罪。如果“犯罪”是指犯罪行為意義上的犯罪,則所舉上述情形均屬于信息網絡知識產權犯罪行為,對這些行為提供幫助的,均可以構成該罪。例如,網絡服務商A明知甲乙丙丁四人各自單獨實施網絡盜版行為,該四人行為單獨來看都達不到著作權犯罪的定罪標準,又不是共同犯罪,A分別實施了幫助行為,綜合起來看,A的情節達到嚴重程度。對此,如果認為“犯罪”是指完全符合犯罪構成意義上的犯罪,就會認為A的行為難以構成犯罪;如果認為“犯罪”是指犯罪行為意義上的犯罪,就會認為A的行為仍可以構成犯罪。事實上,在甲乙丙丁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或者過失實施信息網絡知識產權違法行為的情況下,對“犯罪”的不同理解也會導致得出不同的結論。
由于《刑法修正案(九)》剛剛通過,學界尚未圍繞這些問題展開深入討論,但是,上述問題也并非空穴來風。事實上,在我國刑法典規定的轉化型搶劫罪、窩藏罪等犯罪中,由于涉及對前罪的理解問題,因而始終存在爭議。例如,不屬于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且盜竊數額不大的盜竊行為,以及數額不大的詐騙、搶奪行為,是否屬于轉化型搶劫罪中的“盜竊、詐騙、搶奪罪”?理論上存在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只有搶奪、盜竊、詐騙了數額較大的財物,才可能轉化為搶劫;有人認為,不要求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構成犯罪,但也不包括數額很小的情況;還有人認為,不要求盜竊、詐騙、搶奪的數額較大,也不宜排除數額過小的情況l參見高銘暄、王作富著:《新中國刑法的理論與實踐》,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本文認同“犯罪行為意義上的犯罪”說,理由是:其一,從刑法典的用語來看,“犯罪”具有多重含義,并不一定要求符合全部犯罪構成要件。一般來說,犯罪是指具備了成立犯罪的全部條件的行為。但是,犯罪的本質是法益侵害,在此意義上說,只要是侵犯了法益的行為,就具備了犯罪的本質。而行為是否侵犯法益,只需要進行客觀判斷。例如,已滿14周歲的人殺人,與未滿14周歲的人殺人,在侵害他人生命這一法益上沒有任何區別。只是出于責任主義與刑事政策的理由,對后者不按照犯罪論處而已。所以,刑法典上的“犯罪”,在有的場合就是指構成要件行為,而不是指符合全部構成要件的犯罪。如果不這樣理解,刑法典上的許多“犯罪”術語就難以得出準確的解釋。m參見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頁。其二,信息網絡犯罪行為往往要求一定的情節、結果(如網絡盜版犯罪中的“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才能構成犯罪,如果把此處的“犯罪”理解為完全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則會一定程度上放縱該罪的發生。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在深度鏈接網絡共同犯罪中,實行犯是虛擬世界中成千上萬的“點”,這些“點”或者因網絡的虛擬性難以查找或者因數額未達到起刑點而難以定罪。但“網絡技術幫助犯”卻實實在在地客觀存在。沒有網絡技術幫助犯,實行犯的侵權行為難以順利實施。可以說,在網絡世界中,網絡技術幫助犯更類似“組織犯”,它將散布于網絡世界中成千上萬個“點”組織、聚合起來,其危害性遠甚于“點”(實行犯)。n參見徐松林:《視頻搜索網站深度鏈接行為的刑法規制》,載《知識產權》2014年第11期。如果要求其組織的“點”達到犯罪情節標準才能對知識產權網絡技術幫助犯定罪,這無異于要求只有被組織的賣淫嫖娼行為構成犯罪,才能追究組織賣淫罪的刑事責任,這顯然是荒謬的。其三,該罪的構成要件要求具備“情節嚴重”條件,把“犯罪”理解為犯罪行為意義上的犯罪,并不會導致網絡知識產權服務商動輒得咎的結果。有人可能認為,如果被幫助的人僅僅實施了信息網絡知識產權違法行為,情節輕微難以構成犯罪,而共犯行為(幫助行為)卻構成犯罪,會不會違背罪刑均衡原則?本文認為,本罪的成立具有“情節嚴重”的要求,也即是說,如果其所幫助的全部信息網絡知識產權違法行為整體來看尚屬情節輕微(如次數較少、網絡點擊量小等),就不應構成犯罪,從而不違背罪刑均衡原則。
基于上述分析,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實施的信息網絡知識產權違法行為、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實施的達不到特定犯罪情節或者結果要求的信息網絡知識產權違法行為(如被幫助人實施的侵犯著作權罪沒有達到“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標準)、被幫助人過失實施的信息網絡知識產權違法行為、不具有違法性認識可能性的被幫助人實施的信息網絡知識產權違法行為等,均屬于該罪中的“信息網絡犯罪”。
三、罪數問題
該罪規范的是為他人信息網絡犯罪提供幫助的行為。在為網絡知識產權犯罪提供幫助行為的犯罪中,行為人既可能僅僅實施幫助行為,也可能同時參與實施他人的信息網絡知識產權犯罪行為(即參與正犯行為),或者實施幫助行為后,行為人又從事其他的信息網絡知識產權犯罪行為。不同情形下,犯罪行為方式、主觀故意均有不同,相應地罪數關系也有不同。
(一)單純實施為他人信息網絡知識產權犯罪提供幫助行為的罪數問題
該行為毫無疑問構成該罪。但是,該罪設立的刑法理論基礎是“共犯行為正犯化”理論,而該理論的一大特色就是承認成立犯罪(該罪)的基礎或者前提是存在共犯行為,因此,單純實施為他人信息網絡知識產權犯罪提供幫助行為在構成該罪的同時,還構成相關犯罪的共犯行為,對此,如何解決其罪數形態問題?
本文認為,借鑒“共犯的競合”理論,對此情形原則上按照正犯行為定罪處罰,即按照該罪定罪處罰。以網絡盜版為例,如果行為人明知他人設立的網站為盜版音樂網站,應該網站請求,為其提供鏈接、支付結算等服務,則一方面構成該罪的正犯,另一方面構成侵犯著作權罪的共犯,鑒于刑法典已經將為他人實施信息網絡犯罪提供幫助的行為獨立規定為犯罪,因而原則上應將其認定為該罪。
例外的情形是,如果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嚴重的知識產權犯罪(法定刑在3年以上7年以下的犯罪),而仍提供幫助的,應當按照正犯(本罪)處理,還是按照知識產權犯罪的幫助犯處理?不同于前述情形的是,按照該罪處理,有可能罪責刑不相適應:甲實施量刑檔次在3年以上7年以下的知識產權犯罪,委托乙利用其成立的網絡服務機構從事互聯網接入服務發布相關信息。按照該罪(正犯)處理,只能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如果將乙作為甲的幫助犯處理,即使認定其為從犯,量刑也可能重于按照該罪的正犯量刑(對于幫助犯的處罰規則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除了假冒專利罪與銷售侵權復制品罪以外,其他類型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幫助犯的處罰完全可能在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范圍內)。因此,如果按照該罪(正犯)處罰,就有可能導致罪責刑不相適應。
本文認為,該罪第3款“有前兩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規定中的“其他犯罪”,既包括其他犯罪的正犯形態,也包括其他犯罪的共犯(幫助犯)形態。如果按照該罪的正犯形態處罰,難以做到罪責刑相適應,完全可以適用其他犯罪的共犯形態來處理,從而做到罪責刑相適應。即綜合全案事實,即使考慮幫助犯的從輕情節后,仍應該在3年以上的量刑幅度內量刑的,則可以選擇按照他罪的共犯形態予以定罪量刑。
(二)教唆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知識產權犯罪行為并提供幫助,或者為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知識產權犯罪行為提供幫助并實施該正犯行為的罪數問題
上述情形屬于刑法理論上的 “共犯的競合”,即在共同犯罪中,行為人既實施教唆行為,又與被教唆者共同實施該正犯行為的,或者既實施教唆行為,又實施幫助行為的,又或者既實施教唆、幫助行為,又實施正犯行為的,屬于包括的一罪,僅以一罪論處即可o參見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33頁。。例如,行為人唆使他人建立盜版網站、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盜版犯罪,并為其提供技術支持或者收取費用等幫助的;或者行為人為盜版網站提供技術支持或者收取費用等幫助,并在該盜版網站上從事盜版活動的;又或者行為人唆使他人建立盜版網站后,又為盜版網站提供技術支持等幫助,并在盜版網站上從事盜版活動的,等等。按照“共犯的競合”這一吸收犯的法理,均應按照一罪定罪處罰。至于是按照該罪定罪處罰,還是按照被幫助、教唆、參與實施的犯罪定罪處罰,仍應遵循“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的規定。
(三)既實施本罪行為,又利用信息網絡從事其他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罪數問題
行為人既可能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知識產權犯罪(A罪)而為其提供幫助(構成該罪),也可能同時利用信息網絡實施其他類型的知識產權犯罪(B罪),此時行為人可能同時觸犯該罪、A罪的幫助犯以及B罪。對此,對于A罪的幫助犯與該罪遵循“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選擇罪名,再與B罪進行并罰即可。例如,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侵犯著作權罪(A罪),而為其提供幫助(構成該罪),同時親自利用信息網絡實施銷售侵權復制品犯罪(B罪),分別構成該罪與侵犯著作權罪(幫助犯)、銷售侵權復制品罪。此時,應先選擇適用該罪還是侵犯著作權罪的幫助犯(擇一重罪處理),然后與銷售侵權復制品罪進行并罰即可。
基金項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項目批準號:14YJC820034)成果。
作者簡介:劉科,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教授,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