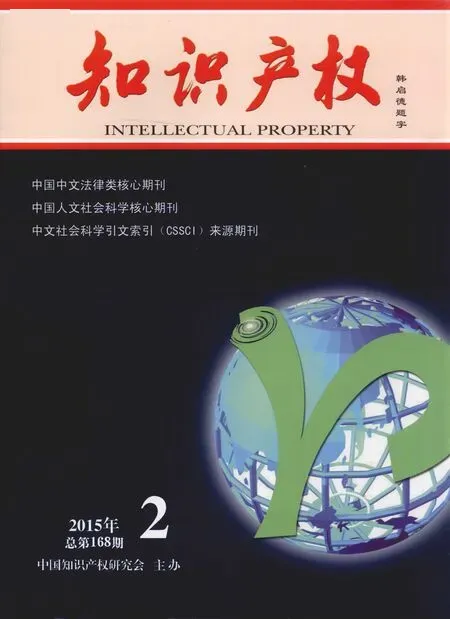從現代性和文化多樣性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律保護
蔣萬來
從現代性和文化多樣性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律保護
蔣萬來
工業革命以來,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一樣,也遭受著所謂現代性的侵蝕。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要求締約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然而對其保護對象在規定上因抽象性不強而留有爭論,此也影響到我國立法。從文化本身、立法目的和保護措施等方面,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對象進行論證表明,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質是一種生存樣式(方式),其保護的不僅是基于該生存方式而生的知識或形式,也更是針對創造這種形式的能力,以及運用這種能力的生存方式本身。但是,在現代性的背景下,保護面臨極大困境,因不當商業化和民間信仰的普遍缺失等原因,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規定的“真實性”、“傳承性”和“整體性”保護要求實際難以達到,從而影響保護效果。從長遠看,這是立法和司法實踐以及法學界應長期思考的未決問題。
文化多樣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對象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困境
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文本,于2003年10月17日經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通過。我國也于次年8月24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加入該公約,并于同年12月2日向教科文組織總干事正式提交了批準書,從而成為該公約的第六個締約國。但是,該公約的簽署過程本身卻充滿爭論,爭論的核心與其說是法理和邏輯問題,不如說是政治和利益問題。前者強調嚴謹和透徹,后者則講究審慎和務實,兩者顯然難于完全圓滿契合。結果是,懸而未決的某些爭論繼續留給了各締約國的國內立法和學術界,比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對象即是其中之一。2011年,我國頒布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其保護對象規定在第2條,表面上既有概括,又有列舉,林林總總,但因基本沿襲公約的表述,故而實際上仍不夠明確。對象未明確,無疑會直接影響到我們對其保護方面的認識。為此,本文將以工業革命以來所謂“現代性”對文化多樣性的影響為背景,考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立法宗旨,探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對象,并反思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存在的某些問題。
一、現代性的擴張與文化多樣性的立法追求
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在序言中表明,其制定是考慮到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規定,并為落實2001年《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需要有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的新規定有效地予以充實和補充而制定的,于是,文化多樣性成了不可回避的一個關鍵詞。《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指出:“文化多樣性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于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應當從當代人和子孫的利益考慮予以承認和肯定。”在此,文化多樣性也與生物多樣性發生了某種聯系。
一般來說,生物多樣性包括了動植物和微生物的物種以及它們的基因和生態系統方面的多樣性。其意義不僅在于物種本身,更在于人類的生存。它們在物種、基因和生態系統內部所形成的多元互補關系,有助于物種的保存和優化。但是,工業革命以來,社會的廣泛市場化,催生了人們對大自然進行無限掠奪和攫取的貪婪動機;而科學技術在物質生產和社會生活領域的支配,則提供了人們滿足自身控制自然這一貪欲的有效手段。這兩方面的結合導致的實際后果之一,就是生物多樣性的逐漸縮減。①何中華:《從生物多樣性到文化多樣性》,載《東岳論叢》1999年第4期,第74頁。這種后果不言而喻:它直接減弱甚至動搖了人類生存的基礎。因為物種的減少將使人類的食物資源、醫療資源和工業原材料等面臨威脅,而這些資源又基本上來源于生物資源。生態系統的惡化則使得人類未來的生存環境,更是面臨一種恐怖的景象。表面上,服從于人類科學技術支配的自然界,實際上卻不斷蘊積著對人類的報復,與人類的貪婪欲望形成了強烈的對立。其實,18世紀浪漫主義思潮的先驅,早已開始對工業文明懷有深切的憂慮和恐懼:盧梭懷疑科學和文明不會給人類帶來幸福,而只會帶來災難;席勒看到的則是,工業文明把人束縛在整體中孤零零的斷片上,機器的輪盤使人失去生存的和諧與想象的青春激情。②劉小楓著:《詩化哲學》,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3頁。這也是所謂浪漫主義思潮對“現代性”的批判。
“現代性”的實質是“理性”,而近代工業文明的哲學基礎正是這種“理性”。在浪漫主義者看來,當這種“理性”滲透到人類生活之中,改變著人與世界、人與人、人與自身的時候,舊的荒誕還沒解決,新的荒誕已經出現了。③劉小楓著:《詩化哲學》,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頁。人們對物的追求意志越是強烈,向外部世界攫取越多,也就越迷惘,內在的靈性也就越少。莊子“沉于物、溺于德”的見解得到了歷史的證實。科學技術也就成了一種異在的客觀力量,反過來窒息著人的生存價值和意義。“現代性”所蘊含著的理性及其體現的抽象普遍性,通過全球范圍內的現代化運動,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兩個維度進行全面擴張,對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形成了日益嚴重的沖擊。④何中華:《從生物多樣性到文化多樣性》,載《東岳論叢》1999年第4期,第75頁。人們對這種沖擊的回應,如果說在哲學上是以浪漫主義的思想武器為先聲,那么也可以說,在具體的措施上仍然是以另一種理性為依歸,這就是作為調整人們規范的法律。1992年聯合國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并頒布了《生物多樣性公約》,它已經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提高到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層面來認識。而1972年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2001年的《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和2003年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則表明了國際社會對文化多樣性的高度重視。
現代性背景下的人對自然戡天役物在人與人的關系上表現為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侵略和并吞,尤其是西方文化霸權的確立,它的理論基礎是物種進化論在社會進化中的翻版。伴隨著政治和經濟上的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作為一種更為陰險的控制形式,在其產生之后,不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體,更是征服了他們的心靈。通過理性主義的擴張,西方文化利用一整套的文化話語,在經濟、政治、語言、教育、藝術、文學、宗教、法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等各個方面,全方位地消解著非西方民族的文化個性和歷史傳統。⑤同注釋④ 。西方列強基于其民族優越感和文化中心主義,我慢自雄,不可一世。我國思想家章太炎認為,這是拘泥于競爭之說而強行改變物之自性,是不聞莊子的“齊物”大道。他主張不同的文化“短長相復”,通過交流和比較達到相互理解,進而互補互益。他在《齊物論釋》中援佛解莊,表明了對不同文化應持兼容和齊物的態度。他強調文化平等的普遍性,必須打破文野、智愚、尊卑的界限,指斥“志存兼并”。其“應物之論,以齊文野為究極”的核心論旨,頗顯示出他反對文化霸權、主張文化多元的思想。⑥戴明璽:《章太炎與二十世紀初中國思想裂變》,載《南京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第37頁。這種思想可謂具有普遍意義,表明了人們對文化兼并的抵抗態度,它既是文化多樣性主張的最初動因,同樣也是對人與人關系上現代性的深刻反思。
從哲學思潮的先導到法律規范的實施,人們在對現代性批判反思的問題上,是符合邏輯上的連貫性和一致性的。如果說,生物多樣性的消失,其惡果主要在于它給整個人類的物質生活帶來直接的共同威脅,那么,文化多樣性的消失則是給不同人類族群的精神生活帶來各不相同的損害。一方面,它不僅導致不同文化形態的互補性喪失,同時也導致基于這種互補而生的文化創新的可能性減弱,而最終使得文化形態走向貧乏和單一。在此,不論強勢文化或弱勢文化,都不可能有最后的贏家。另一方面,走向消失的文化,使得原來擁有該文化傳統的人們對歷史的認同感趨于淡漠,從而也使得其精神家園喪失。所以,生物多樣性的立法是為了維系生物平衡,它要解決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文化多樣性的立法則在于維護不同文化之間的平衡,其直接目的是為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是,不論有關生物多樣性還是文化多樣性,其立法的最終目的,都是解決作為人類整體的人與自身關系問題。尤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立法,傳承精神價值和信仰是其極為核心的關鍵因素,它被強烈地挹注了對人類自身精神家園的終極關懷,這也正是它作為立法所追求的法律價值所在。
二、現行立法對保護對象定義的模糊表述
1972年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除自然遺產之外,對文化遺產方面的規定,是從歷史、藝術、科學、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考慮,將具有普遍價值的文物、建筑群和遺址等列為保護對象。此處的“普遍價值”是指什么?盡管顯得抽象,但是,該公約僅僅羅列了這些物質性的文化遺產,在邏輯上肯定既不周延,經驗上也與實際生活有所不符。所以,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的提出,正如《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序言所言,是對《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有效地予以充實和補充”。
從某種意義上說,2003年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是以1972年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為藍本制定的。不過,兩者畢竟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便在于前者所謂的非物質性的文化遺產,不但是當下的、活生生的,而且與特定人群的生存方式相聯系。⑦梁治平:《誰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載鄭培凱主編:《口傳心授與文化傳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5~46頁。這種活在當下的文化,之所以也像后者一樣被稱之為遺產,是因為它同樣也是源自歷史而世代相傳。《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第2條第1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是:“被各個群體、團體、有時是個人視為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以及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被不同的社區和群體在適應周圍環境和自然的過程中、在與其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持續的認同感,從而增加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在該公約中,只考慮符合現有的國際人權文件,各社區、群體和個人之間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順應可持續發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該條文第2款則緊接著以列舉的方式規定,“按上面第一段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以下方面:1.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2.表演藝術;3.社會實踐、禮儀、節慶活動;4.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5.傳統手工藝。”
從該定義對保護對象范圍的列舉性規定來看,本身即表明其抽象性不足,各個被列舉對象之間缺乏邏輯上的連接點;而從該定義條文的限制性條件來看,它也隱藏著一系列內在的矛盾。具體而言:
首先,該條文第2款以列舉的方式規定的五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實際上也就是第1款所說的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在此處,除了非物質的共性之外,鏈接它們之間的共同特征或者說邏輯起點究竟是什么?這似乎并不明確。這些紛繁復雜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秘書處關于“傳統知識”的表述極為相似,但“傳統知識”本身也是一個較為復雜,且未獲得統一解釋的概念。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認為,它最大的特點在于其不是系統的,而是根據個體或集體的創作人對其文化環境的回應和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知識。⑧Para.2,WIPO/IPTK/MCT/02/INF.3.這仍然是一個非常模糊的解釋,在此,什么是“對文化環境的回應和交互作用”?什么是對這種回應和交互作用“形成的知識”?等等,都未能得到清晰的闡述,可謂是一個模糊概念建立在另一個同樣模糊概念之上。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文件框架中,許多問題并未有效地得到解決,概念和術語上前后不一致甚至相互沖突,使得人們對傳統知識的保護難以真正落到實處。⑨轉引自管育鷹著:《知識產權視野中的民間文藝保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頁。這種模糊情形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同樣存在,這無疑給概念本身的理解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其次,在該公約中,只考慮符合現有的國際人權文件,各社區、群體和個人之間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順應可持續發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些學者對此表示出極大的疑慮。他們認為,不具備這些條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應該自生自滅,還是被歧視甚至被消滅?那些文化的創造者又當如何?如果只承認人權、可持續性和相互尊重,不僅要求過分,而且也導致邏輯與實踐的不一致。比如,公約保護瀕危的傳統文化,而瀕危的恰是那些不可持續的文化。又比如,世界上許多敘事詩和史詩都歌頌本民族的偉大、戰爭的勝利和敵人的失敗,并沒有表示對其歷史上敵人的尊重,它們是否應被公約的定義排除在外呢?所以,定義中的道德要求會成為加于各種傳統及其實踐者的毀滅性的負擔。⑩梁治平:《誰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載鄭培凱主編:《口傳心授與文化傳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54~55頁。
所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或者說其保護對象,是模糊的,甚至可以說是充滿著歧義和矛盾的。作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締約國,我國無疑也應符合公約要求,將其原則和規范轉化為內國法。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1條規定,“為了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存工作,制定本法。”不過,它將公約本身的缺陷也基本按原樣復制過來了。在保護對象的問題上,第2條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除有意淡化或回避人權等因素,從內容看與公約表述在實質上并無不同。①參見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2條:本法所稱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所。包括:(一)傳統口頭文學以及作為其載體的語言;(二)傳統美術、書法、音樂、舞蹈、戲劇、曲藝和雜技;(三)傳統技藝、醫藥和歷法;(四)傳統禮儀、節慶等民俗;(五)傳統體育和游藝;(六)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實物和場所,凡屬文物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
三、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對象的理解
由于某種原因,《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和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或者說對其保護對象,均未予以明確,那么,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本文認為,作為前提或基礎的“文化”本身,在人類學上的第一性意義,自是不能被忽視之外,當其進入法權領域,成為一個法律上的概念時,還應必須考慮其立法目的,同時也必須考慮法的實施等因素。
首先,文化的概念雖難定論,但是將其表述為一種包括人類知識、信仰及人們所獲得的各種能力、習性在內的復合體等,基本為學界所公認。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中的解釋,幾乎為各類相關論文和著述所引用。他認為,文化是包括人類知識、信仰、道德、法律、藝術、風俗習慣以及人們所獲得的各種能力、習性在內的一種復合體。②轉引自高福進著:《地球與人類文化編年:文明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這種復合體實質即是與生存、生活相聯系的整個生活方式的總和,是某個人類群體獨特的生活方式,它們是整套的“生存式樣”。③克魯柯亨:《文化概念》,載莊錫昌等編:《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頁。非物質文化,既屬于文化中的一部分,也是整個生活方式或者生存式樣的一部分。所以,相應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對象,正是作為特定群體部分瀕危的生存方式。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除了非物質的共性之外,鏈接它們的邏輯起點或者說共同特征也正是在于:它們都屬于一種生活方式的范疇。在這種含義寬泛的生活方式之下,具體到某一方面,它們到底是表演、實踐、表現形式,還是別的什么,可能并不重要,因為事實上它們彼此之間,常常相互很難截然分開,但它們都與知識、信仰、習性或者能力有關。
其次,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法律上的含義,既不可能完全脫離作為母體的文化在人類學上的本來含義,同時又必然受到法的價值目的的限制。這就意味著,需要立法對作為某種生活方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調整范圍上進行有選擇性地取舍規范,如果對這種被視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活方式,不加限制地一律予以保護,無疑是要竭力維護一切舊有的生活方式,阻礙新的生活方式,這顯然是違背歷史發展必然規律的,同時也是荒誕不經和絕無可能的。所以,公約對“被各個群體、團體、有時是個人視為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以及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進行諸如“再創造”、“持續的認同感”、“文化多樣性”以及所謂“人權”、“相互尊重”和“可持續發展”等因素的條件限制,實際上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個法律概念設置的條件限制。盡管在實踐中,已如前述,這些限制性條款可能存在著矛盾,有難以把握的情形,但畢竟為將一般意義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認定為應受法律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了法定依據,故有其不可或缺的積極意義。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2條所稱非物質文化遺產,表面上雖無直接規定此類條件限制,但在第3條涉及到了認定問題,并在第4條則明確了文化認同等方面的內容。④參見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3條: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采取認定、記錄、建檔等措施予以保存,對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采取傳承、傳播等措施予以保護。第4條: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當注重其真實性、整體性和傳承性,有利于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有利于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和可持續發展。
再次,從法的實施角度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根據《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規定,主要是“指采取各項措施,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命力,包括這種遺產各個方面的確認、立檔、研究、保存、宣傳、弘揚、承傳(主要通過正規和非正規教育)和振興。”⑤詳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第2條第3項。公約第三部分“在國家一級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第四部分“在國際一級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條款中,其字里行間也無不體現了要求國家和國際組織強烈干預,欲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弘揚和承繼的立法訴求。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傳統知識,盡管兩者非常接近,甚至部分對象重疊交叉,但也有明顯不同之處,比如:傳統知識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相關法律文本里被提出,這說明它的保護問題主要還是在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制度框架之內落實的。而非物質文化遺產則要復雜得多,范圍也更為廣泛,比如其中的某些社會實踐、禮儀、節慶活動等就與傳統知識格格不入,顯得非常獨特,難以被視為知識產權對象而納入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予以保護。眾所周知,知識產權對象就是“知識”本身,其本質是“形式”,創造是“設計形式”的活動。⑥詳見劉春田主編:《知識產權法》(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11頁。這種傳統知識也無疑是一種知識或形式。對這種知識或形式的保護,在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制度下進行時,其適用的主要是私法的調整方法,包括事前法律關系的確認和事后權利被侵害時的救濟。至于該權利如何生成,法律并不積極主動予以干預。超越此形式的意義,比如,對于創造這種形式的能力,知識產權制度既無可能也無必要對此進行保護。
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所體現出來的追求文化多樣性為目的的立法宗旨與2001年《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以及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一脈相承,而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對傳統知識的保護迥然有異。本質上為生存方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其所要保護的不僅是基于該生存方式而生的知識或形式(此一部分與傳統知識的保護重疊交叉保護),更是針對創造這種形式的能力,即所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命力),以及運用這種能力的生存方式本身。
所以,不論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還是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盡管在各自的表述上略有細小的區別,但綜合各方面的因素而概括地看,它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對象,可分為兩個方面:首先,是群體、團體或個人的世代傳承的一種生存方式,包括傳承和再創造某種非物質性生活方式的能力和意愿,以及運用這種能力和意愿所需的一切必要的外在物化因素;至于何種非物質性的生活方式(也即被視為文化遺產的)的傳承和再創造能力需要被保護,則是一個認定的問題。從保護的措施來看,針對這部分保護對象,主要通過公法進行,也即國家運用公權力促使特定群體、社團或個人既有愿望也有能力使得該種生活方式得以延續,傳承和再創新。其次,是基于這種傳承和再創造能力所創造出來的作為有形的文化符號的形式,這正是很多學者經常討論的需要知識產權制度予以保護的部分。對此,《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似無涉及,而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僅在附則第44條作援用條款規定。⑦參見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44條:使用非物質文化遺產涉及知識產權的,適用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對傳統醫藥、傳統工藝美術等的保護,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四、現代性背景下的保護要求及其困境
無論人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或保護對象認識如何變化,其總是“有不斷豐富和深化的過程,表現出經驗性、實踐性、可操作性及開放性和衍生性。任何界定和劃分都不會是凝固不變的,隨著認識的深化,我們會發現更多現存文化事象的歷史、藝術、科學和精神價值,也就會有新的種類進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類別系列。”⑧王文章、陳飛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國家文化發展戰略》,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第87頁。這種觀點不拘泥于立法上并非十分科學的定義限制,以務實的態度避免了一些無謂的爭議,固然有可取之處。但是,無論如何,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不斷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賴以存在的自然和社會壞境將面臨喪失的危險,從而可能走向式微不歸,這一事實難以否認。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非物質文化遺產因其瀕危而可能逐漸走向消亡,可謂是歷史發展的大勢所趨。
面對這種趨勢,法律保護的作用是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真正弘揚、傳承和振興,并非僅僅止于茍延殘喘。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4條中規定:“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當注重其真實性、整體性和傳承性,有利于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有利于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和可持續發展。”其中“有利于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等,已如前述,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上的要素之一,也是保護的追求目標,而“應當注重其真實性、整體性和傳承性”,則應該是保護措施方面的原則要求。但是,在現代性的大背景下考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特別是在像我國這樣尚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這種保護要求常充滿悖論,難以實現。
(一)真實性問題
從國際條約到我國立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實性究竟是什么,均未作明文規定。但從民俗學的角度看,每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都具有獨特的地方性,有一個真實的本原,正是它處于瀕危狀態而需要保護。于是,原生態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語境下的本真性訴求得以被提出來,⑨劉曉春:《誰的原生態?為何本真性?》,載《學術研究》2008年第2期,第154頁。并被大眾所熟知。這種民俗學上的本真性,對應在法律語言中應該是所謂的真實性。我們知道,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傳統生存樣式或生活方式聯系在一起,基本上都是傳統鄉民社會的產物。而如今絕大多數傳統鄉民社會被現代都市社會所代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均發生巨大變化,于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故“對傳統民俗的保護,通常是希望使那些仍然保留著較多傳統民俗的文化群落盡量不受或少受當代文化影響,繼續固守他們原有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對于瀕危的民間藝術、工藝等具體文化活動的保護,通常要靠資助傳承人的方式使這些文化活動得以延續。”⑩高小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否只能臨終關懷》,載《探索與爭鳴》2007年第7期,第62頁。這種刻意制造所謂原生態的保護模式,正如許多學者批評的那樣,幾乎等同于臨終關懷,只是使得這些文化形態勉強延續一段時間而已,并不符合非物質文化遺產被不斷地再創造,為社區和群體提供持續的認同感的要求。①同注釋⑩ 。它將保護狹隘地局限在保存層面,忽視了“宣傳、弘揚、承傳和振興”方面的內容,從而也被視為一種標本化的僵硬的保護模式。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可謂是,以特定社區或族群維持其農耕社會舊有生活形態,制約其社會經濟生活發展為代價,從而滿足現代人發思古之幽情的獵奇心理,不僅在保護的實效性上強差人意,甚至在道德的正當性上也值得懷疑。所以,這種真實性的注重如果以所謂靜態的原生態形態出現,肯定難有作為。雖然,在全球化的現代性面前,地方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可被視為地方的文化自覺,對本真性的追求,可構建一個民族(或族群,社區等)自我的本真形象,或即所謂的文化認同感,但是,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地方在發掘原生態文化的時候,不僅僅是在展示,同時也是在表述,是為了使他們所構想的認同能被更大的世界所承認。在這一文化創造的過程中,問題的關鍵是為他人生產自我,還是為自己生產自我。遺憾的是,在當下的原生態文化發掘中,更多的是表現為前者。”②劉曉春:《誰的原生態?為何本真性?》,載《學術研究》2008年第2期,第157~158頁。同時,除了文化認同的功能之外,非物質文化遺產也被視為一種文化資源和資產,商業因素的參與,都不可避免地使得它脫離其生存的文化生態,而成為被展示、被欣賞、被塑造的對象,于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化過程“進入了一個被生產、被構建的陌生化過程,這一過程使非物質文化越來越遠離日常生活形態的本真樣貌。”③劉曉春:《誰的原生態?為何本真性?》,載《學術研究》2008年第2期,第155頁。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要求,從其立法的價值目標或者立法宗旨來看,本應是人們對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異化或物化的反思,但是,落實到法律的具體保護措施上,卻又因保護實踐中的矯枉過正而烙下深刻的人為造作痕跡,以致于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反而失真被異化。于是,現代化的滾滾潮流下,不僅人類遭受異化,甚至連用以抵制人的異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自身也遭受異化,這確是一個頗為令人尷尬的諷刺。所以,從某種意義上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幾乎就是個幻象。但是,它卻恰恰又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為追求民族文化認同而設定的一個保護措施的要求,這顯然是一個矛盾。
(二)傳承性問題
為破解上述矛盾,人們基于人類學中文化變遷理論和文化生態理論,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應強調動態(活態)保護,即以傳承、變化和發展的眼光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變動不息的特點使得所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在歷史長河中‘層累地造成’的,很難將其追溯到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因而也很難確定究竟要保護哪一階段的形式。”④劉志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人類學透視》,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4期,第28頁。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固定形式,雖被稱之為“遺產”,但是卻仍然活在當下,并未死亡,它在動態中生存,在活態中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性,從本質上表現為它是有靈魂的。“這個靈魂,就是創生并傳承它的那個民族(社區)在自身長期奮斗和創造中凝聚成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集中表現為共同信仰和遵循的核心價值。這個靈魂,使它有吐故納新之功,有開合應變之力,因而有生命力。”⑤賀學君:《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思考》,載《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第104頁。盡管非物質文化在不斷變遷,但萬變不離其宗,其提供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的核心價值,即是傳承性保護中的靈魂所在,只要符合這些要求,法律就應予保護,也就都可以被認定為是真實的、傳承的。
然而,目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實踐中,常常因為缺乏信仰和價值方面的要素,使得文化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失去精神和心理基礎,這也就是前面所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真實性的喪失問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第13條(d)項(ii)提出的“尊重習俗”和第2條第2款中“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指的無不是民間信仰問題。農業社會遺留下的某些傳統風俗,常帶有民間信仰的色彩,它們都是某個歷史時期的文化符號,也是最能代表農業文明的最具震撼力的文化,而這些卻常常被誤認為是封建迷信而未能被認定在保護項目之內。事實上,世界上約2/3左右的項目都與巫術和民間信仰有關。⑥轉引自戴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困惑》,載《瞭望》第2005年第30期,第59頁。我國近年申報的項目絕大多數均不過是歌舞表演和一些傳統技藝之類,這些表演技能如果缺乏信仰或精神要素支撐,則也會因商業化而完全異化,變得面目全非,這無疑與文化認同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馳。因為,有為數不少的民俗儀式和傳統技能,其“最狹義的文化特質可能是存在于男女之間的完全不具有商業性質的情感交流活動,比如女孩為情郎繡的荷包、鞋面之類,這種技能的傳承需要一個較大的社會壞境。”⑦高小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否只能臨終關懷》,載《探索與爭鳴》2007年第7期,第64頁。某種意義上,現代社會移風易俗,即是對傳統社會生活方式的極大背離,傳統價值和信仰自然被空心化。如此一來,關于傳承性的保護,也就容易流于口頭上的宣傳,事實上難以實現。
(三)整體性問題
正如前述,傳承性保護需要整體的社會和自然環境,故這兩者是緊密聯系的。“如果脫離了整體文化生態環境單獨談論某種文化事象,就不能獲得對其內涵的真切理解。如果我們進而將其剝離出去,置于不同的文化場域或使其游離于現實生活之外,也就隔斷了它與社會生活環境的血肉聯系,失去了最為核心的生命力。”⑧劉志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人類學透視》,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4期,第31~32頁。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頒布之前,在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中,針對一些傳統文化積淀豐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較為集中、特色鮮明、形式和內涵保持完整、自然生態環境保護良好的特定區域,人們已提出了整體性保護的方式,即設立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在非遺保護中建立起一種整體保護的思路和理念。我國于2007年正式批準閩南文化生態保護試驗區,將泉州、漳州、廈門三地聯動起來,涵蓋閩南方言文學、民間音樂、戲曲、民間舞蹈、民間美術、民間手工技藝、民俗、傳統體育競技、民間信仰、消費習俗10個項目。據稱,目前我國已建立8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⑨金昱彤:《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整體觀》,載《探索》2013年第1期,第124頁。諸如此類,雖名為整體保護,但是從實際情形來看,其所謂整體似乎并非針對保護對象的生態環境而言,而是在于保護對象本身的密集疊加。不可否認,各種不同種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有時也可互為生態環境要素,但是他們畢竟與自然或社會結構方面的文化生態大環境顯著不同。整體性保護,如果是此類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模式,即所謂多地區聯動,多項目集中,則與前述所謂原生態保護模式并無本質區別,只是數量上密集化而已,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和傳承性似乎并無增益。如果整體性保護的是文化生態環境,然則又如何保護?只要置于現代性的大背景下,這種文化生態的所謂整體性的保護,絕非僅僅局限在法律規定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所”,而是指整體的社會和自然環境。故如此之高的要求,幾同紙上談兵,前景并不樂觀。
綜上所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在要求上,其脈絡逐漸呈現:真實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前置性的要求。如果喪失真實性,即是喪失民族文化自覺的本源,立法所追求的文化認同也將成為無源之水。但是,真實性又因文化的變遷而相對化,特別是現代性的商業因素也極易促使其異化,故而需要動態保護,以傳承發展的眼光看待,即不必拘泥所謂靜態的原生態,只要其核心的精神內涵和信仰不變即可。目前的主要問題恰恰是缺乏精神和信仰內核,致使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常常淪為純取悅商業利益的惡俗表演,根本無從談起所謂文化認同,以增加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等。為此,又需要整體地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態環境,以固守其共同信仰和核心價值,但是,整體性保護于操作性上,卻是最具難度的。很顯然,這種保護即是要求人們維持甚至復原舊有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以保有和傳承作為遺產的非物質文化,這雖不能說絕對與社會現代化進程相沖突,但大體而言,其畢竟以阻止現代性的擴張作為目標。工業革命以來,在現代性擴張的背景下,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不斷遭受沖擊。盡管浪漫主義早就對本質上作為“理性”的“現代性”進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但是,正如有學者指出:“從歷史上看,浪漫主義對現代性的批判并未能實際地阻止現代性的不斷擴張。”⑩何中華:《從生物多樣性到文化多樣性》,載《東岳論叢》1999年第4期,第75頁。那么,作為“理性”的法律,其是否可能有針對性地阻止現代性的擴張呢?從此“理性”到彼“理性”,是展現了人類“理性”自身不屈的自信,還是反映了人類“理性”膠柱鼓瑟的無奈窘境呢?實耐人尋味。
眾所周知,法律并非萬能,它作為調整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的一種規范,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是人們不得已的一種措施而已,而絕非等同于真理本身。但是,法律面對涵義如此復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保護任務如此之重大,仍必須有所擔當,以期建立人們所希望的某種理想秩序狀態。“作為人類的行為規范,法律的制定或者接受既然本來就是‘有所為’而來,則法律的制定、接受,甚至在探討時,人們對之莫不‘有所期待’,希望借助法律,達到‘所為’的目的:促成公平之和平的實現。因此在法律概念的構成上,‘必須’考慮到擬借助法律概念來達到目的,或實現的價值。亦即必須考慮所構成之法律概念是否具備實現所期待之目的或價值的功能。”①黃茂榮著:《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6頁。從目前看,不論《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還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的概念和保護措施等均有諸多值得繼續深化的空間。尤其是面臨商業化對民間信仰和精神方面的侵蝕,法律并未作出令人信服的強有力的回應。就像上帝不能引導缺乏虔誠信仰的信徒通達善和幸福一樣,囿于欲望的理性也難以真正引導我們通達善和幸福,這種善和幸福乃是幻想鎖鏈的遙遠彼岸。真正欲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為社區和群體提供持續的認同感,從而增加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如果法律無力培育精神價值和信仰以固其根本而念念相續,那么,其保護恐怕亦復如是,只能停留在幻象鎖鏈的遙遠彼岸。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ame as the biodiversity, the cultural diversity has been eroded from the so-called modernity.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States Parties are required to safeguar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ereas the controversy on its safeguarding objects exists as the result of insuffi cient abstractness of the provisions, which also affects the legislation of our country.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safeguarding objects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such aspects as culture itself, legislation intent, safeguarding measures and so on. It holds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 survival mode. The safeguarding scope includes not only the knowledge or forms based on the survival mode, but also the capability of creation, and the survival mode itself which could apply the capability.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the safeguarding faces great predicament. On account of the improper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general lack of folk belief, together with other reasons, it is hard to achieve the safeguarding requirements, which are the authenticity, the heritage and the integrity prescribed in ICH Law of our country, thus affecting the safeguarding effect. On a long view, it leaves the legislation, judicial practice, and jurisprudential circle, with an open issue needed to be thought about for a long time.
cultural diversity; safeguarding objects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afeguarding predicamen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蔣萬來,寧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