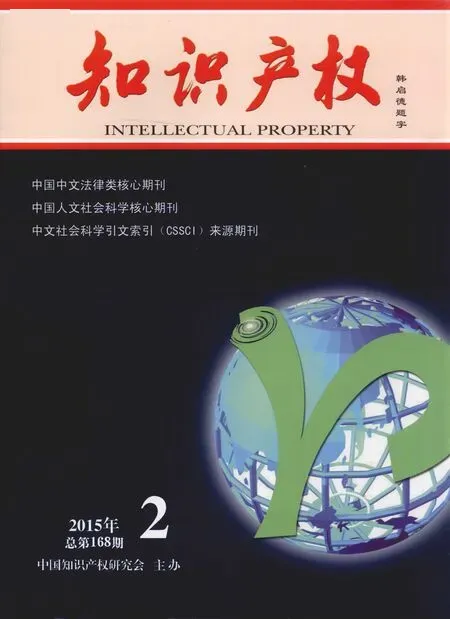論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反壟斷規制
李 陶
論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反壟斷規制
李 陶
由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牽頭起草的《禁止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定(征求意見稿)》第14條細化了反壟斷法在規制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作用和調整對象。但對于如何認定集體管理組織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以及如何協調著作權法與反壟斷法在規制集體管理組織壟斷行為時的關系問題,立法者和學界的認識存在偏差。鑒于集體管理組織在平衡著作權法各主體利益上的制度功能,應優先適用著作權法專門性監督。反壟斷一般執法作為補充,可在專門性監督無法有效發揮作用時,在個別情況下適用。
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反壟斷一般執法監督 著作權法專門性監督
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作為權利人與使用人之間的中介機構,其壟斷地位同時體現在權利管理市場(集體管理組織與權利人之間)和授權市場(集體管理組織與使用人之間)。①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Copyright, Competition and Development, 12. 2013 München, pp.210.我國《反壟斷法》的調整對象囊括了“其他組織”。因此,從理論上講,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屬于反壟斷法所調整的對象。2014年6月,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起草的《禁止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定(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知識產權反壟斷執法指南(草案)》)在第14條中,將集體管理組織的反壟斷規制單列一條,增大了對集體管理組織反壟斷一般控制的可操作性,但具體標準和措詞還需商榷。
與此同時,他國對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反壟斷規制的路徑存在三種模式:一是僅通過反壟斷法對著作權集體管理的壟斷行為進行防控(美國);二是通過著作權專門法和反壟斷法共同對集體管理組織的壟斷行為進行防控(德國、法國為代表的歐盟國家);三是排除反壟斷法對集體管理組織之適用(俄羅斯、加拿大)。從我國已有的制度結構形態和立法者對集體管理組織反壟斷控制整體布局分析,我國存在著作權法專門性監督(《著作權法(草案)》、《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與反壟斷法一般性控制(《知識產權反壟斷執法指南(草案)》)兩種方式共存的情況,類似于歐洲國家對集體管理組織反壟斷行為規制的方式,由此產生了如何協調兩種規制手段關系的問題。因此體系上,應著重系統研究歐盟在監督機制的設置與協調法律適用的方法;內容和標準上,美國在判斷集體管理組織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經驗,對我國制度設計和理論研究也具有借鑒意義。
本文以歐盟委員會、歐盟法院、德國、美國有關集體管理組織反壟斷的調查及判決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總結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表現之認定,確定我國應以何種標準認定集體管理組織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并提出如何協調著作權法專門性監督與反壟斷一般執法之間的適用關系。
一、集體管理組織與權利人之間——權利管理市場之反壟斷控制
(一)禁止歧視
從競爭自由和理性經濟人的角度來看,集體管理組織對權利人進行差別對待存在合理性因素:首先,管理商業價值不高的作品所付出的成本無法從管理此類權利產生的收益中收回;其次,集體管理組織總是會基于各自特點和優勢,傾向于管理某類作品;第三,對于外國權利人的管理,執行成本和監督成本均高于本國權利人。因此,歷史上集體管理組織排斥管理外國會員。②同注釋①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p.234.但考慮到集體管理組織作為自然壟斷行業的特點,以及其基于法經濟學和法哲學功能,③參見Drexl,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s and the EU Principle of Free Movement of Services after the OSA Judgment, Springer 2014, p. 464.其單方選擇會員的權利必須受到限制。
從美國集體管理組織發展的歷史上看,有選擇的吸收會員是導致司法部發起針對美國音樂集體管理組織ASCAP反壟斷審查,并設立與之對抗的集體管理組織的原因。④美國1930年建立的第二家集體管理組織SESAC就是由當時被ASCAP拒絕接納的來自歐洲的權利人組建。參見:Para. X. A. of the ASCAP Consent Decree, supra n. 737.德國為防止集體管理組織有選擇地吸收會員,在1965年《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法》誕生時就設置了“集體管理組織對權利人的管理義務”(也稱為“強制管理義務”Wahrnehmungszwang)。德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法》第6條規定:……集體管理組織有義務根據權利人的要求,以適當條件管理屬于其業務范圍內的權利,滿足權利人(被管理)的要求。該制度設計的核心精神是:但凡權利人要求集體管理組織管理其權利的,集體管理組織必須管理,不能拒絕。權利人可以選擇是否入會,但集體管理組織不能對要求入會的權利人進行篩選,并進行差別對待。⑤參見:Schack, Urheber- und Urhebervertragsrecht, 6. Auflage (2013), S.628.我國立法者對該原則進行了移植,根據《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19條,集體管理組織有義務接受符合入會條件的申請人入會的申請,不得拒絕。
由于歐盟內部存在統一的憲法性綱領文件和競爭法,因此“無差別吸收權利人”在歐盟內部可適用于不同國別的權利人。⑥參見歐盟委員會GEMA和GVL兩個判例中的決定:Decision of the Commission of 2 June 1971, Case IV/26.760 - GEMA, [1971] OJ 134, p. 15;Decision of the Commission of 29 October 1981, Case IV/29.839 - GVL, [1981] OJ No. L 370, p. 49.而在世界上其他國家該原則只適用于本國權利人。
(二)對會員退出的限制
在GEMA Ⅰ案件中,歐盟委員會認為,德國音樂著作權協會(GEMA)設置6年管理周期的做法,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GEMA則主張,6年的管理期是為了保證曲庫的穩定,以便在與使用人談判中提供周期較長的授權許可,以此獲得有力的談判地位。但歐盟委員會認為該理由不能成立,最終德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同意將退會周期更改為3年。⑦Goldmann, Die kollektive Wahrnehmung musikalischer Recht in den USA und Deutschland, 2001 München, S. 301.在BRT訴SABAM的案件中,歐盟法院認為,比利時作家、作曲家、出版商協會(SABAM)在權利人退會后,設置5年的管理過渡期屬于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⑧歐盟最高法院判例:Case 127/73 BRT v SABAM [1974] ECR 313. supra 113, para. 12.愛爾蘭競爭委員會認為,本國集體管理組織在權利人退回后,設置3年的過渡期過長,且阻礙了著作權集體管理市場上競爭的可能,要求將其設置為1年。⑨Competition Authority, Decision No. 326 of 18 May 1994, Notification No. CA/2/91E-Performing Right Society and individual creators/publishers (Assignment of Copyright), paras 87-88, 107.美國通過早先的判例要求集體管理組織(ASCAP)不得拒絕會員退會的請求,且權利人需要在每年的年底提出。⑩Para. XI. B. 3. of the ASCAP Consent Decree, supra n. 737.
事實上,限制會員退出也存在其合理的原因:首先,只有獲得相對穩定的數據庫才能增加集體管理組織與使用人談判的籌碼。其次,從版權使用費的結算層面,集體管理組織對權利人版權使用費的結算具有滯后性,向權利人發放授權費往往需要2-3年。①參見林秀琴、李晶:《構建著作權人與作品使用人共贏的著作權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一個法經濟學的審視》,載《政治與法律》2013年第11期,第32頁。第三,從使用人的角度,相對穩定的數據庫也便于使用人申報作品使用和取得使用權。倘若曲庫頻繁改變,雙方不得不頻繁修改合同,權利人的頻繁“轉會”和“退會”會增加使用人的搜尋和協商成本,增大取得授權的難度。
因此,從上述退會時間上來看,德國、法國等作者權法系國家,從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在著作權法中平衡不同主體利益的功能出發,通過設置較長的管理期,堅持并呼應集體管理制度的著作權法上的功能性設計——維護作者利益,防止作者被作品傳播者脅迫而頻繁轉會。而美國和愛爾蘭則是更加關注作品傳播者和私人自治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過度的私人自治不利于整個社會對作品的開發利用。就我國而言,管理期和會員退會后管理過渡期的設置應首先尊重會員大會的決定。具體標準須在會同產業界、學界和司法界專家論證的基礎上通過會員大會產生。在此過程中,國外在確定退會周期時背后體現的制度成因、我國著作權法保障作者利益的價值選擇、產業界和使用人的商業訴求等應被重點關注。
(三)管理權利的類型與范圍
首先,從權利轉讓的類型上看,學界和實務界習慣用“小權利”來定義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之范圍,但何為小權利,立法者并沒有給予明確的清單。在德國,學界和實務界將小權利理解為“通過個體管理難以實現的權利”。由于概念模糊,不同的集體管理組織對于管理的范圍各不相同。以德國三大集體管理組織為例,除了實施德國《著作權法》規定的只能由集體管理組織管理的權利(法定報酬請求權或稱獲酬權)以外②強制性集體管理,立法表述為:“該報酬請求權不能放棄,且只能通過集體管理組織管理”,包括:德國《著作權法》第20b條(有線轉播權)、第26條(追續權)、第27條(對出租與出借的報酬請求)、第45a條(針對殘障人士的合理使用)、第49條(報紙文章和廣播電視評論的合理使用)、第52a條(為課堂教學和科研的網絡傳播)、第52b條(在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的電子閱覽處再現作品)、第53a條(公共圖書館寄送復制品)、第54h條(基于私人復制產生的法定報酬請求權)、第137l條(對新使用方式的報酬請求權)。,德國音樂著作權協會(GEMA)管理的權利包括,對音樂作品的表演權、播放權、通過銀幕、擴音器、廣播及電視的再現權、機械復制和發行權、對音樂作品的在線使用權(德國《著作權法》第16、17、19、19a、20、21、22條);③Melichar, in Loewenheim, Handbuch des Urheberrechts, 2. Auflage 2010, 第46條,第4段。德國文字著作權協會(VG Wort)所管理的權利包括:作者和出版社通過銀幕、擴音器、廣播及電視的再現權、作品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德國《著作權法》第19a、21、22條);德國鄰接權集體管理公司(GVL)管理電視臺對節目的傳輸,接收、復制、播放,音像音樂生產者、電影生產者的鄰接權,但不含信息網絡傳播權。④同注釋③ ,Loewenheim書, Melichar文,第46條,第10段。除了法律規定的只能有集體管理組織主張的權利以外,上述小權利的范圍由會員大會確定。所以,根據作品類型的不同,通過確定符合本行業權利人和作者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范圍,是確定管理權利類型的標準。
其次,從權利轉讓的程度上,集體管理組織是否能要求權利人轉讓其在世界范圍內、針對現有和將來(管理合同有效期內)所有作品的,所有使用方式的管理權?通過GEMA Ⅰ和BRT訴SABM兩起反壟斷調查,歐盟委員會對上述問題進行了認定:
第一,根據歐盟委員會的觀點,德國音樂著作權協會(GEMA)要求權利人轉讓其在世界范圍內管理作品的權利屬于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權利人有權通過個體管理或者選擇加入國外集體管理組織的方式,自由靈活地就版權使用的方法和對價與國外相對人進行協商。概括性的轉讓在世界范圍內的管理權,剝奪了權利人在其他文化市場的定價權和經營權。⑤同注釋⑥ ,GEMA I, supra n. 804, at II. C. 2. a) (p. 22).
第二,同樣在GEMA Ⅰ的反壟斷調查中,歐盟委員會認定,GEMA要求權利人轉讓所有對作品利用方式的要求屬于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表現。因為就同一件作品,權利人有權把不同的權利類型信托給不同類別的集體管理組織分別進行管理(如:將一件音樂作品的廣播權交由一家集體管理組織管理,而將在電影中使用該音樂作品的管理權交給另一家集體管理組織)。⑥同注釋⑤ 。歐盟法院在幾年后BRT訴SABM案的判決中以判例法的形式確認了該標準,但同時也強調:盡管概括性地要求權利人轉讓所有權利限制了權利人的選擇權,但選擇權的行使需要以存在可選擇的集體管理組織為前提。對權利轉讓中具體權利類型的轉讓,需要考慮所在版權市場中已有集體管理組織類型的分布。本國法院在具體個案中,有權決定集體管理組織要求權利人轉讓權利類型的范圍。⑦同注釋⑧ ,BRT v SABAM, para.13.
第三,對于集體管理組織要求權利人轉讓既有作品和將來(管理合同有效期內)所有作品的要求,歐盟委員會則認為其不屬于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根據歐盟委員會1970年作出的決定,權利人在委托集體管理組織管理的過程中,不能僅保留具有高回報率的權利和作品,而把難以管理和回報率低的權利類型和作品交給集體管理組織,此種方式有違集體管理組織內部的“團結契約原則”(the principle of solidarity)——這一集體管理組織形成的基礎和基本共識。⑧歐盟委員會反壟斷調查:Decision of 12 August 2002, Case COMP/C2/37.219-Banghalter & Homem Christo v SACEM, supra n. 583, p.11.根據“團結契約原則”,作為利益共同體,集體管理組織的收支需要通過對不同作品授權費的收取,實現相對的動態平衡。同時,穩定和巨大的曲庫是集體管理組織與國際媒體巨頭談判的籌碼。另外,管理作品規模的預期也是吸引更多權利人加入集體管理組織的誘因。⑨同注釋⑥ ,GEMA I, supra n. 804, at II. C. 2. a) (pp. 22 et seq.).而這種規模效應能夠有效降低邊際成本,形成內部和外部的雙向均衡。此外,對于每創作一件新作品就要重新簽一份授權合同的做法也難以在實踐中執行。依據美國司法部在處理ASCAP和BMI糾紛時做出的決定,為減少交易成本而建立的集體管理組織應僅就 “公開表演權”進行管理。一次性轉讓所有作品的做法在美國也得到了認可。⑩同注釋⑦ ,Goldmann書,S.299.但美國判例法在處理集體管理組織壟斷行為問題上,并不考慮其在保護作者面對強大的合同對方時在利益平衡上的作用。①同注釋①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p.241.
就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的建設而言,歐洲普遍接受的“團結契約原則”并沒有得到學者的關注。媒體和部分學者常常將集體管理組織要求權利人轉讓針對所有作品和將來作品的要求誤讀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事實上,集體管理組織具有保持文化多樣性和維護作者利益的多重功能,在限制集體管理組織自由選擇會員和曲庫的情況下,不能再進一步剝離收益率高的作品,而僅僅將難以管理的作品和權項交由集體管理組織管理。
(四)過高管理費
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音集協)管理費居高不下的問題,一直以來被廣泛關注。從目前協會分發管理費的數據分析,在扣除營業及附加稅、文化部“全國娛樂場所陽光工程”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監管平臺(中文發公司)8%的費用后,向權利人分配為50%費用(其中20%支付給MCSC,30%向CAVCA會員分配),天合公司服務傭金為25%,協會本身行政開支為17%。卡拉OK領域管理費用高昂的原因在于:為了開展收費,音集協委托的天合集團在全國的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子公司,員工總數達到450余人。同時,音集協先后在18個省市就卡拉OK侵權提起了960多起行政投訴和民事訴訟。此外,用于協會初期曲庫建設、宣傳、市場監督的需要,前期投入已達3.6億元。服務商天合集團的投入已達到5.6億元。②參見王秋實:《音集協3年收卡拉OK版權費1.7億一半被消耗》,載《環球時報》2010年1月26日。
歐盟實踐方面,權利人目前沒有專門就管理費的比例提起過異議。但在其他案件中,曾附帶對管理費的比例做過審查(見本文二、(三)許可費的異議與監督)。根據德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法》第6條,集體管理組也應當在“適當條件”下,履行管理職責。管理條件是否“適當”屬于德國專利商標局所應當監督的范圍(德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法》第19條)。對于管理費的收取,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認定許可費標準的案例中認為:基于權利人與集體管理組織之間的信托關系,集體管理組織應當在管理作品的過程中盡可能減少管理的額外開支,盡可能優化管理結構,降低管理費的比例,將管理費控制在可預期的范圍內。③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BGH GRUR 2002, 332/334; BGH ZUM 2005, 739/743.以德國三大集體管理組織為例,根據2013年年報,其管理費比例分別為:德國音樂著作權協會(GEMA)15%左右,德國文字著作權協會(VG Wort )9%左右,德國鄰接權集體管理協會(GVL)7%左右。
在我國,由于分配計劃和管理費的收取比例由會員大會討論決定,我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在經營過程中,隨著成本的收回,應主動逐漸降低行政開支的比例。對此,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應當通過修法,賦予權利人對過高管理費的異議權,國務院著作權管理部門應對管理費的合理性進行監督。但我國在卡拉OK領域收費問題上,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行政能力有限,在協調同級部門(如文化部)利益時,行政執法能力薄弱,有必要在反壟斷法中也賦予權利人在著作權管理部門不能有效監督情況下的異議權,就管理費過高問題展開反壟斷調查,打破相關部門的行政壟斷。
二、集體管理組織與使用人之間——授權市場之反壟斷控制
(一)禁止歧視
如前所述,根據自由競爭和利益最大化的經濟學分析,集體管理組織也有充分的理由對不同的使用人施以不同的標準。但考慮到集體管理組織作為自然壟斷行業基于法經濟學和法哲學功能,其在發放授權時的單方決定權應受到限制。
1940年,美國ASCAP意圖向廣播電臺征收雙倍的使用費,這直接導致了廣播電臺抵制ASCAP并建立美國第三個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BMI。④同注釋①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p.217.而德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法》出于預防差別性發放授權,在設置本文所述的“集體管理組織對權利人的管理義務”的同時,在使用人與集體管理組織之間,也設置了“集體管理組織對使用人的授權義務”(也稱為“強制締約義務”Abschlu?zwang)。德國《集體管理組織法》第11條規定:……集體管理組織有義務就其管理的權利,以適當的條件,向任何提出要求者授予使用作品的權利。該制度設計的核心精神是:但凡使用人在普遍使用的適當條件下,向集體管理組織提出使用作品的要求,集體管理組織必須授權,不能拒絕。在個體管理的過程中,權利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選擇是否授權以及向誰授權,同時還可以與使用人協商授權的條件及費用。但問題在于,有些權利人會出于競爭或以獲取高額回報為目的,有意選擇授權的對象,并提出苛刻的合同訂立條件,或拒絕授權。作品使用人和其下游產業為此所付出的成本增加,下游產業的發展會因此受到制約。而集體管理組織通過間接地限制權利人濫用權利,在高效管理權利的同時滿足權利交易市場對作品使用的剛性需求,繁榮文化產業。⑤同注釋⑤ ,Schack書,S.634.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23條也有類似的制度設計。
歐盟司法層面,2008年在Kanal 5 ltd 和TV4AB訴瑞典音樂著作權協會(STIM)的案件中,兩家私人電臺認為,瑞典著作權協會(STIM)與其簽訂的“從收入中抽取百分比”的許可合同,區別于其與公立電臺“按一攬子合同固定數額”的許可合同。兩家私立電臺認為,STIM濫用了市場支配地位,對使用人進行了“公立電臺”與“私立電臺”的區分,進而實施了差別性對待。歐盟法院認為,無論是“按照營業額的百分比”收取許可費;還是按“一攬子合同的固定數額”收取許可費,都是合理的收費方式。⑥歐盟最高法院判例:Case C-52/07 Kanal 5 et al. v STIM [2008] ECR I-9275, para. 37.但由于各成員國對認定公法主體與司法主體在競爭層面是否構成競爭關系的立法保留,該案中,歐盟法院將“公法主體與司法主體競爭關系”的認定留給瑞典法院。但在瑞典法院作出判決之前,兩家私人電臺與STIM就音樂作品的使用達成了新的適用標準,撤回了訴訟請求。
(二)一攬子合同
國內部分學者對一攬子合同的合法性基礎存在誤讀,在《知識產權反壟斷執法指南(草案)》第5稿中,立法者更是將其錯誤地認定為實施壟斷行為中的一種。事實上,一攬子許可合同屬于許可合同的一種,特別適用于對作品需求量大,按作品使用數量實施單獨收費不經濟的領域。歐洲學界和實務界普遍認為,利用一攬子合同能夠理順授權渠道,提高交易安全,減少使用人的交易成本和使用成本。⑦同注釋①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p. 212-213.同時,從國外司法實踐來看,歐洲和美國的一系列判例肯定了一攬子合同的價值和正當性。⑧參見Broadcast Music, Inc. v. CBS, Inc., 441 U.S. 1 (1979).歐盟法院在Tournier訴SACEM的案件中認為,鑒于一攬子合同在節省協商成本與監督成本上的作用,若要認定集體管理組織實施一攬子許可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使用人需要證明存在其他授權模式,而該授權模式在維護權利人利益與節省授權和管理成本上具有與一攬子許可同等效果。⑨歐盟最高法院判例:Case 395/87 Tournier [1989] ECR 2521, para. 45.德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在執行一攬子合同過程當中,則是以一攬子許可為基礎,輔之以營業場地面積、客流量等其他參數適用不同的費率。
(三)許可費的異議與監督
設置專門性監督機構,受理使用人對許可費標準的異議是國際社會通行的做法,如英國的版權仲裁庭、法國的文化部。在德國,針對費率異議的仲裁制度及相關程序建立于1985年,其在實踐中的作用得到了多方的肯定。⑩Reinbothe, Schricker/Loewenheim, Urheberrecht, 4. Auflage ( 2010), S.2349-2350.仲裁委員會雖設在德國專利商標局,但其獨立于德國專利商標局,直接受德國聯邦司法部領導。仲裁委員會具有很高的專業性,他們協調的方案若雙方接受則具有強制執行力(德國《著作權集體管理法》第14條a第4款)。若雙方不能達成協議,則可以選擇繼續協商或進入司法程序。仲裁程序是啟動司法程序的必經前置程序,受理費率糾紛的法院為慕尼黑高等法院,法院不審查仲裁過程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但由于法官缺乏專業知識,在訴訟過程中很大程度會依賴仲裁委員會的方案。①參見《德國專利商標局2012年工作年報》第48頁。
我國法律制度的引進往往只注重規范,與實體法制度相關的程序性設置未能給與足夠重視。在費率的確定與異議問題上,現行的《著作權法》和《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并沒有為權利人以及使用人創造異議費率的途徑。在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過程中,根據2014年公布的《著作權法(草案第三稿)》第62條,立法者意圖通過著作權實體法及日后的《著作權實施條例》創設費率異議機制,此舉值得肯定。
歐盟司法實踐層面存在利用反壟斷法規制高額許可費的判例。在Tournier訴SACEM②歐盟最高法院判例:Case 395/ 87 Tournier [1989] ECR 2521.和Lucazeau訴SACEM③歐盟最高法院判例:Cases 110/88, 241/88 and 242/88 Lucazeau [1989] ECR 2811.兩起案件中,在橫向比較同類場所歐盟其他成員國的費率之后,歐盟最高法院認為,法國音樂著作權協會(SACEM)針對酒吧,迪廳等娛樂場所所征收的音樂作品的許可費不合理的高于歐盟其他成員國的平均水平,屬于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④同注釋②、③, 歐盟最高法院判例:Tournier, supra n. 867, para. 38; Lucazeau, supra n. 868, para. 25.
就費率異議問題所體現的著作權專門性立法和反壟斷法立法目的功能上來看:反壟斷執法機構對費率的審查是從對排除、限制競爭的角度進行。而著作權行政管理機構對費率的審查則是從平衡各方利益、費率的適當性的角度進行,反壟斷法對價格的控制旨在防止集體管理組織利用市場支配地位侵占相對人利益,妨礙和扭曲正常的競爭秩序;而著作權法所保障的費率異議機制則是從制度上滿足不同群體對參與費率制定的訴求;此外,囿于著作權法行政管理機關職能和行政能力的局限,在監督救濟措施的執行層面上,反壟斷執法機關能發揮的作用更大。我國當下最緊要的任務是建立費率異議機制,同時通過反壟斷執法指南引入必要的渠道,以便在專門性監督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利用反壟斷執法機構所具有的更強的執法手段對著作權法專門性監督的執行進行補充。
三、相關建議
對于處在發展初期的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國家應在較短時間內,理清誤解,扶植制度建設,加強監督。建議對集體管理組織壟斷行為的控制,從集體管理組織在著作權法中的功能出發,在肯定壟斷的前提下,關注如何規制壟斷。通過國際經驗的分析,本文建議:
第一,價值論層面:歷史地看,集體管理組織作為作者權利覺醒與擴張時期的產物,其功能上具有平衡創作與作品傳播者利益和平衡權利人與使用人利益的雙重價值。它不僅是一個法經濟學上成本控制的工具,更具有法哲學上捍衛作者根本利益,促進作品傳播與保存文化多樣性的社會功能。而壟斷地位則是實現其功能的前提和基礎。所以,對濫用壟斷地位的規制與認定,必須以實現其上述法經濟學和法哲學功能的著作權法價值訴求為先導。
第二,立法論層面:通過《著作權法》和《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的修改,明確監督機構,完善對集體管理組織設立及日常活動監督的條款。進言之,在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設立問題上,在保持現行《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9條、第10條申請備案制度的前提下,淡化民政部在社團登記層面的征求其他相關部門的權力,強化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私人自治,特別是會員大會的功能。防止除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以外的行政機構干涉集體管理組織設立。其次,在《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5章中應設立針對著作權費率異議的裁判機構。
第三,法律適用和協調層面:在《知識產權反壟斷執法指南(草案)》具體監督的條款設計中,應首先尊重著作權法賦予集體管理組織的合理的壟斷,不應細化認定壟斷行為具體的標準和數字,僅需提供一般性、概括性的適用可能。在《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中,應明確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和反壟斷執法機構在處理同一案件時的職責——兩部門分權但應合作。同時明確反壟斷執法機構在對相關案件進行調查處理時,應當征求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的意見。在適用順位上,鑒于集體管理組織具有平衡著作權法中不同權利主體的制度功能,應優先適用著作權法專門性監督。但鑒于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所處的發展階段,針對集體管理組織的反壟斷調查,應持審慎和克制態度。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drafted “Act of Prohibition of Ab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Eliminate or Restrict Competition”,art. 14 of which specifies the role and object of Antitrust Law to regulate 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CMOs). However, there exist different perception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abuse of the market dominant position of CMOs and the relations coordination between Copyright Law and Antitrust Law when regulates the monopolistic behavior of CMO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unction of CMOs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each party of Copyright Law,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pecialized supervision of Copyright Law should be applied preferentially, and complemented by general enforcement of Antitrust Law in individual cases when specialized supervision is unable to play an effective role.
CMOs; abuse of the market dominant position; general supervision of Antitrust Law;specialized supervision of Copyright Law
李陶,慕尼黑大學法律系博士研究生,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創新與競爭法研究所(MPI)客座研究員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