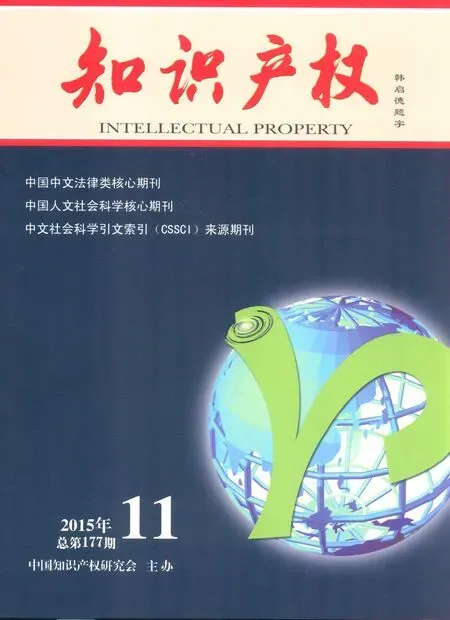體育賽事節目著作權保護問題探討
王自強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關于奧運賽事傳播問題(2008年北京奧運會),國際足聯、美國職業籃球聯盟(NBA)、英國足球超級聯賽等關于體育賽事電視、網絡傳播問題,均涉及到當事方的重大經濟利益。這些機構以知識產權為由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引發的體育賽事節目著作權保護問題備受爭議,本文試圖以基本概念入手進行探討。
一、本文涉及的幾個基本概念
本文涉及到競技體育、體育賽事、體育(廣播電視)節目、體育賽事作品幾個概念。
——競技體育:亦稱競技運動,是體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以體育競賽為主要特征,以創造優異成績、奪取比賽優勝為主要目標的社會體育活動。
——體育賽事:即競技體育比賽活動,如足籃排比賽、田徑比賽、體操比賽、游泳比賽等。
——體育(廣播電視)節目:其可以拆分為兩個概念,一個是節目,即指文藝演出或者廣播電臺、電視臺播送的內容項目(主要針對表演和播放兩種情況);另一個是體育廣播電視節目,即指播電臺、電視臺以體育賽事為內容的播送項目。
——體育賽事作品:是指基于體育賽事或者以體育活動為題材創作的作品。比如對賽事過程的文字報道和評論、反映體育比賽的攝影圖片、對賽事過程固定機位的機械錄制或者活動機位的選擇攝制影像、以及以體育為題材創作的影視劇等。
明確以上幾個基本概念,有助于分析“體育賽事節目”著作權保護問題。
二、有關體育賽事節目著作權保護問題分析
(一)關于競技體育和體育賽事
競技體育與體育賽事是同一屬性不同層級的概念。競技體育是對以體育競賽為主要特征、創造優異成績、奪取比賽優勝為主要目標的社會體育活動的總體描述,而體育賽事則是競技體育項目比賽的具體化。兩者都不是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的智力成果,不是著作權保護的客體,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雖然體育賽事不是著作權保護的客體,但中超5年的賽事轉播“版權費”都賣到80億。其實,這是體育界將體育賽事轉播權與根據體育賽事創作作品的權利劃了等號。有文章明確指出,所謂體育賽事轉播權,是指賽事組織者授權媒體機構播送體育賽事以獲得經濟利益的權利。這種授權不是基于創作作品產生的權利,而是基于對賽事資源的把控。眾所周知體育場館受時空限制,只能滿足部分人到現場觀看體育賽事的需求,但對賽事有欣賞需求的人眾多,而且不受時空限制,要滿足眾多人對體育賽事的欣賞需求,只能通過現代媒體手段來實現。到現場觀看體育賽事要買門票,通過廣播電視網絡等媒體觀看體育賽事也不能成為免費的午餐。因此,體育賽事組織者憑借對賽事資源的把控,對媒體想借助其技術手段播送體育賽事的行為,要求其付出相應的對價。從這個角度上看,體育賽事轉播權與著作權保護本身沒有直接關系。
有人將“體育賽事”與“文藝表演”作類比,認為兩者都應受著作權法保護,其實這完全是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首先,“表演”屬著作權保護的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范疇,而“賽事”則不在這個范疇。關鍵在于,表演之前已經存在“音樂”和“舞蹈”等作品,演員只是通過其表演將作品演繹出來,前提、過程和結果都是確定的,完全符合著作權法保護的主客觀條件。而“賽事”是追求優勝、錦標,既沒有事先可操作的方案,也不會出現競技雙方都想要的過程,其結果完全取決于運動員的競技狀態和臨場表現,前提、過程和結果都存在不確定性,所以也不會產生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
(二)關于體育(廣播電視)節目
本文認為,廣播電視節目不是著作權意義上的概念。這一概念首見于我國1990年頒布的《著作權法》第40條的規定:廣播電臺、電視臺使用他人未發表的作品制作廣播、電視節目,應當取得著作權人的許可,并支付報酬。這一規定存在邏輯問題。在2010年第一次修改《著作權法》時將其調整為第42條: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他人未發表的作品,應當取得著作權人許可,并支付報酬。
之所以專門提出廣播電視節目這個概念,是因為這個概念攪亂了人們的思維邏輯。具體而言,在著作權法領域,它屬于著作權范疇還是屬于相關權范疇,是著作權人的權利還是廣播組織的權利?如果是著作權人的權利,但它是針對廣播組織的概念,若廣播組織處于著作權人的地位,那廣播組織的相關權怎么體現?如果是廣播組織的權利,能僅僅因為一件作品或者制品經廣播組織傳播就成其為廣播組織的權利了嗎?作者的權利何在?這顯然不合理。因此,本文認為,著作權法不應再沿用這一不確定的概念。對廣播組織而言,作品經其傳播,其能享有的權利是被傳播作品的信號,而不是作品本身。
為什么出現廣播電視節目這一定義,本文認為,這是我國對《羅馬公約》的不同翻譯所致。
《羅馬公約》第13條廣播組織應當有權授權或禁止有兩種翻譯 :
其一,廣播組織應當有權授權或禁止:
(甲)轉播他們的廣播節目;
(乙)錄制他們的廣播節目;
(丙)復制:略
其二,廣播組織享有權利授權或禁止:
a.轉播其節目廣播;
b.固定其節目廣播;
c.復制:略
前一種翻譯,把“權利”落腳到“節目”上,即廣播組織對其播放的作品或制品享有權利,他人的作品或者制品一經播放就成了廣播組織的權利。后一種翻譯,則把“權利”落腳到“廣播”上,即廣播組織只對其播放作品或制品的“廣播”享有權利,也就是說,其只對其播放內容的信號享有權利,而不是對播放的內容本身享有權利。本文認為,后一種翻譯更準確,更符合廣播組織權利的定義。
(三)關于體育賽事作品
競技體育和體育賽事不是體育賽事作品,但是,體育賽事作品的創作源于競技體育和體育賽事。
競技體育和體育賽事與文化、經貿會展、婚慶儀式,乃至江河山川一樣,都是人類社會活動或客觀世界的自然呈現。但是,當人們用文字來贊美江河山川,記錄展會盛況;用鏡頭來鎖定風光景色,拍攝婚慶過程等就會產生著作權意義上的作品,就會與著作權保護有關。同理,競技體育和體育賽事通過文字、鏡頭等創作活動同樣可以產生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或制品。
如果說競技體育是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那么其保護對象就不應該僅僅限于體育賽事用于廣播電視傳送的錄制品和攝制品,還應包括對賽事過程的文字報道和評論、對體育比賽的攝影圖片以及體育為題材的影視劇等。事實上,體育賽事組織者從來就沒有因為上述創作方式基于競技體育過程而向創作者主張權利。其原因就是競技體育不是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這一點體育賽事組織者是非常清楚的。
有人會進一步提出,廣播組織和網絡播送的體育賽事節目究竟是錄像制品還是影視作品。這個問題在我國是一個事實問題,因為,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存在“電影作品”與“錄像制品”兩個概念,判斷到一個體育賽事節目是制品還是作品應該由主張權利的人舉證。這一問題涉及到對賽事過程固定機位的機械錄制或者活動機位的選擇拍攝兩種情形,本文認為前者產生制品,后者產生作品。
(四)關于體育賽事轉播權與體育賽事作品著作權的區別
關于二者的區別,本文認為:
——前者是賽事組織者把控賽事資源產生的經濟權利;后者是作者基于體育賽事創作作品享有的著作權。
——前者是一次性使用的權利,即過期不候,針對特定的賽事活動不能反復使用的權利;后者是有期限的權利,即在法定范圍內可以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反復使用的權利。
三、體育賽事作品著作權保護的相關主體
本文認為,涉及體育賽事作品著作權保護的相關利益主體包括體育賽事組織者、體育賽事作品創作者、體育作品的傳播者。體育賽事作品組織者是體育賽事資源的控制者和權利人,但不是著作權意義上的權利人;體育賽事作品創作者是著作權意義上的權利人;體育賽事作品的傳播者是著作權意義上的相關權利(鄰接權)人。
以上三者的概念定位應該說是明確的,但在利益問題上是相互關聯的,而且體育賽事在廣播、電視、網絡狀態下播送,利益主體往往會產生競合,同一主體會同時扮演不同的角色。
比如,賽事組織者僅將某一項具體比賽活動的廣播、網絡播送權授予某一市場主體,而不向其提供任何錄制制品或攝制作品,那么,他則僅僅是通過掌控體育賽事資源獲得經濟利益的非著作權權利主體。而如果賽事組織者不僅將某一項具體比賽活動的廣播、網絡播送權授予某一市場主體,同時又向這一市場主體提供賽事活動的錄制制品或攝制品,他就同時扮演著資源控制利益主體和著作權人(相關權人)兩個角色。
按照上述邏輯推導,如果某一市場主體僅從賽事組織者獲得具體賽事的廣播、網絡的播送權,但是其到現場通過自己的設備錄制、攝制賽事過程,并向公眾傳播,他就是該錄制、攝制體育作品的著作權人和相關權(鄰接權)人。如果某一市場主體在獲得賽事組織者某項具體比賽活動的廣播、網絡播送授權的同時,又得到了賽事組織者提供的賽事活動錄制或攝制影像,在著作權意義上其僅為體育影像的傳播者(僅獲得專有或非專有使用權)。
澄清體育賽事著作權保護相關利益主體,對解決體育賽著作權保護問題非常必要。
結 語
本文認為,明晰了有關概念及其相互關系、主客體定位等問題,所謂的體育節目著作權保護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也就不存在困境或找出路的問題。
——評《休閑體育》